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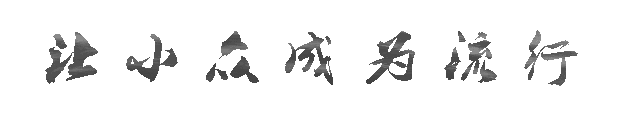
上个周末,小拇哥窝在家里看了两部片子,一部是电影《白日梦想家》,另一部就是今天要说的纪录片。
巧的是,《白日梦想家》里一句丧到极致的台词,刚好印证了这部纪录片的基调——
“再浓厚的血缘,也抵不过凉薄的亲情和巨大的隔膜。”
先不要被这句负能量话给吓跑,小拇哥后面还有话说。

这部丧丧的片子名叫《日常对话》,由侯孝贤监制。不足2000人给出豆瓣8.1,说实话,评分不算高。
但提名和获奖的履历却写得满满当当:
2016年,提名第53届
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
2017年,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评审团最佳纪录片。
2018年,
代表台湾
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的纪录片。
不过,以上都不是我安利它的理由。

故事的主角之一叫黄惠侦,同时她也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
但在拍下这部片子之前,她只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素人。
在黄惠侦的身上,有许许多多标签:
父亲家暴,10岁逃亡,单亲家庭,小学辍学...
最最不同的是,她有一个同性恋母亲。

母亲阿女22岁时一脚踏入形婚并生下了她,两年后又生下了妹妹。
之后因为父亲好赌不养家,黄惠侦从6岁开始便跟着母亲一起做牵亡(法事)讨生活;
10岁时,又因为受不了父亲的家暴,母亲带着姐妹俩逃了出去,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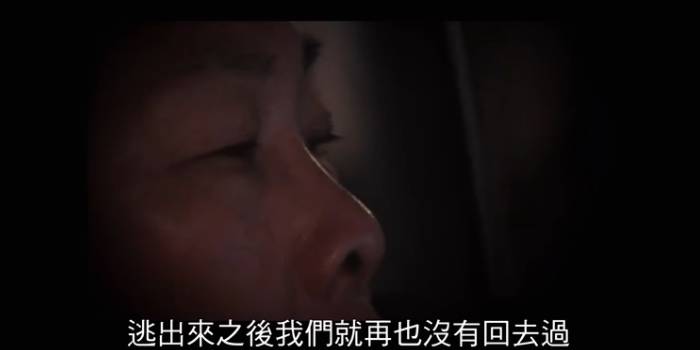

按理说,母女相依为命,本来应该彼此关爱,无话不谈才是,但
黄惠侦和母亲之间更像是两个陌生人。
虽然已经一起生活了30几年,
母亲每天出门前也都会为她准备好饭菜,
可是在黄惠侦看来,除了餐桌上的饭菜,她和母亲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交集。

早上阿女给惠侦准备好饭菜,不是为了坐下来一起吃的,比起和女儿同坐一张桌,她还是宁愿出门和朋友们一起吃;
晚上回到家,她也立马关上房门,无所事事地躺着,或是听收音机发呆。除了日常琐碎,母女俩几乎从来不交流。
就连二女儿也说“从小就是姐姐(黄惠侦)在照顾我,她就是放着我们姐妹俩,不理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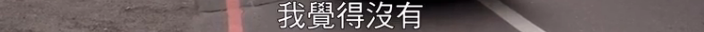
黄惠侦说:“
本来以为我心里的那些问题,等到长大之后我就可以不再去想。
”
比如母亲为什么明明喜欢女人,却选择结婚;为什么母女三人明明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之间的隔膜却可以这么大。
但是在她也成为妈妈之后,她却更想要知道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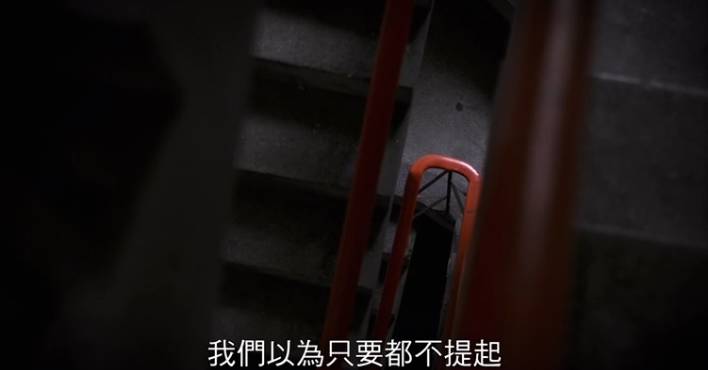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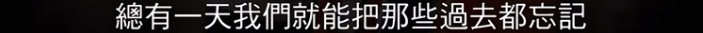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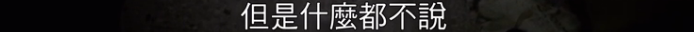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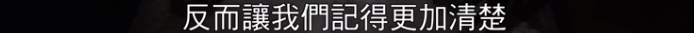
于是黄惠侦试图打破母女之间的僵局。
她问母亲:“你有没有什么话,是想对我跟妹妹说,但都没有说的?”
阿女扣玩着手指,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不喜欢说些有的没的。”
之后,又是一阵
沉默。

在女儿面前沉默寡言,但
在自己的女朋友面前,阿女却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交际高手。
女朋友爱看歌仔戏,她就随时关注着哪里会有演出,骑着摩托车载着对方一起去看;每一年生日,都会给对方送金饰手镯...
哪怕是当着对方家人的面,也会毫无顾忌地叫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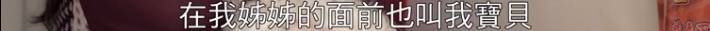
惠侦问母亲交过多少个女朋友,阿女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太多了,要怎么算。
”
但即便是如此,当被问起“你觉得这世上有了解你的人吗?”,阿女依然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反问:“不知道,谁要了解我?”
在阿女看来,女朋友们不会想要了解她,家人也从来没有了解过她。

惠侦没有从母亲的口中得到问题的答案,但跟着母亲一起回乡祭祖后,
一切没有办法解释的答案,却以常理的姿态浮现在了她的眼前。
在祭祖仪式上,阿女讲起了她小时候的故事。
在阿女小时候,父亲对母亲不断进行语言暴力,以至于母亲甚至想要喝农药自杀,最后被阿女偷偷倒掉。
长大后有人给阿女做媒,没想到嫁人只不过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坑,丈夫喝醉了就对他拳脚相加。
惠侦问阿女为什么不说出来,阿女回答,
因为丢人。

惠侦问舅舅们不觉得母亲可怜吗?舅舅反问“有什么可怜?”
在那一辈人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人之常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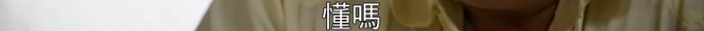
而当惠侦问起“你们知道我妈喜欢的是女生吗?
”
亲戚们却出乎意料地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我不知道,知道这也没用,庙会好像来了。”“我不知道,我要去洗衣服了。”
“(家里)没有人知道。”
惠侦问:“那你现在知道怎么这么冷静?完全不惊讶。”
“有什么好惊讶的?”

小拇哥突然想起王小波的一句话:“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
比如阿女讲起小时候和哥哥们逃学的事情时,总能滔滔不绝聊很多。
但被问到“想不想回老家看看”时,她又低下了头,不作回答。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惠侦终于和母亲坐下来,进行了一场长达10分钟的单独对话。
在对话中,惠侦对着母亲说出了一个在心里绕了30多年的心结。
原来小时候每次和父亲同睡一张床时,父亲都会对她进行骚扰。
惠侦以为因为这个原因,母亲才对她不理不睬。但事实是,直到惠侦说出来,母亲才知道这件事情。

在看这部纪录片之前,小拇哥是被“侯孝贤、金马奖、家暴、同性恋”等一系列夺人眼球的关键词所吸引。
但看完之后,我才明白影片取名为《日常对话》的真正用意——
这场对话,早已跳脱了个体的特殊性。
对于阿女的同志身份的看法,或许影片早已给了答案:

但家人之间这种介于熟悉和陌生之间的亚健康关系,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真正会痛会痒的地方。
也许我们家庭没有像黄惠侦的家庭那样极致,但沉默和隔膜却实实在在存在于每个人的身边。
然而沉默和隔膜就是不爱吗?
不是,
那只是不会爱。

记得《爱与孤独》有句话是这么写的:“你感觉到隔膜,前提应该是你有沟通的愿望,你对那些你不曾想到要与之沟通的人,是不会感觉到隔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