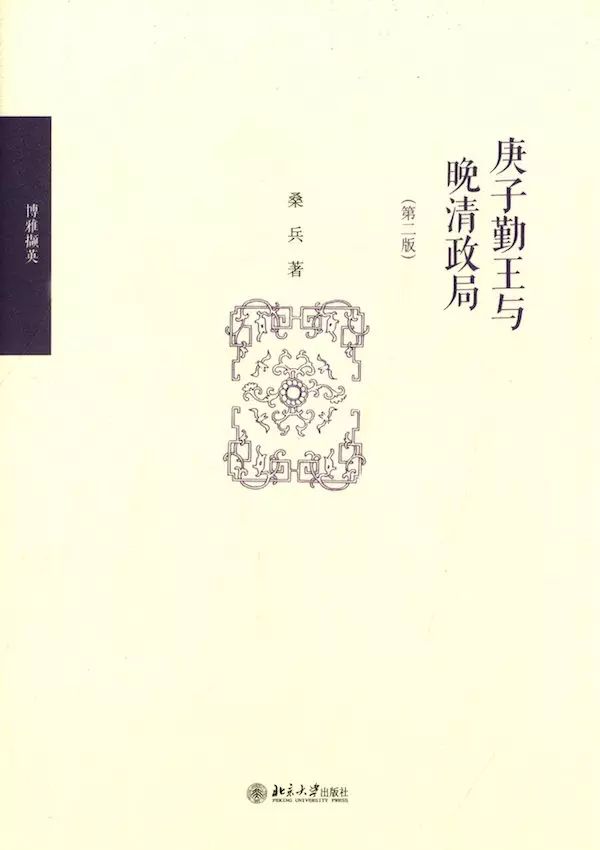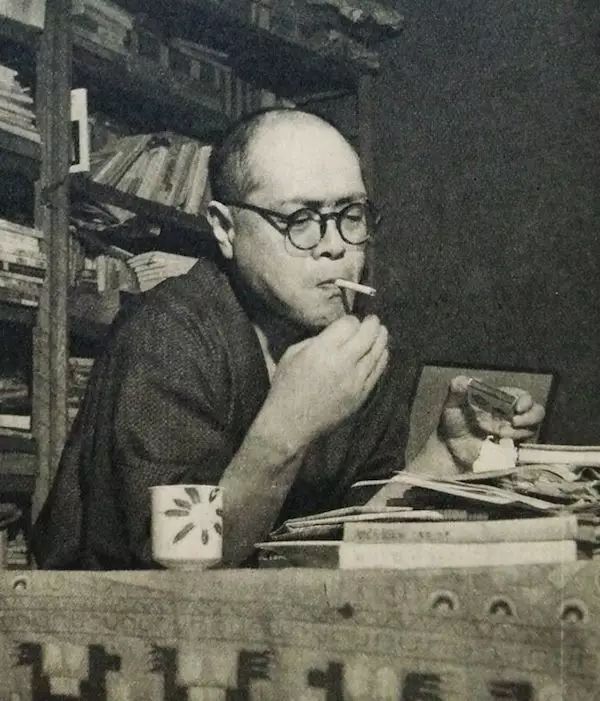
竹内好,1953年。
文︱汪力
━━━━━
狭间直树
从唯物史观到实证史学
━━━━━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接触现代日本人文学术时,曾发现对“亚洲”话题的关注是日本学界不同于中国学界的一个特征。经过二十多年的译介与讨论,今天中国的东亚近现代历史与思想的研究者,已经非常熟悉这一话题。特别是孙歌等学者译介的竹内好,引起了人们对鲁迅、中国革命与东亚、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等话题的兴趣,一度形成“竹内好热”。“亚细亚主义”也自然成为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话题。不过,熟知非真知,与各种广泛存在的“竹内好式”话语相比,实际中国学界对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的了解仍非常有限。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商务印书馆,2004年)
可能是少有的概观性著作。虽然通过这些有限的译介,我们能够得到对这一话题的一般印象,但是要进一步理解这一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课题,仍需要更多的翻译介绍的工作。如此,狭间直树的《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的翻译出版,也就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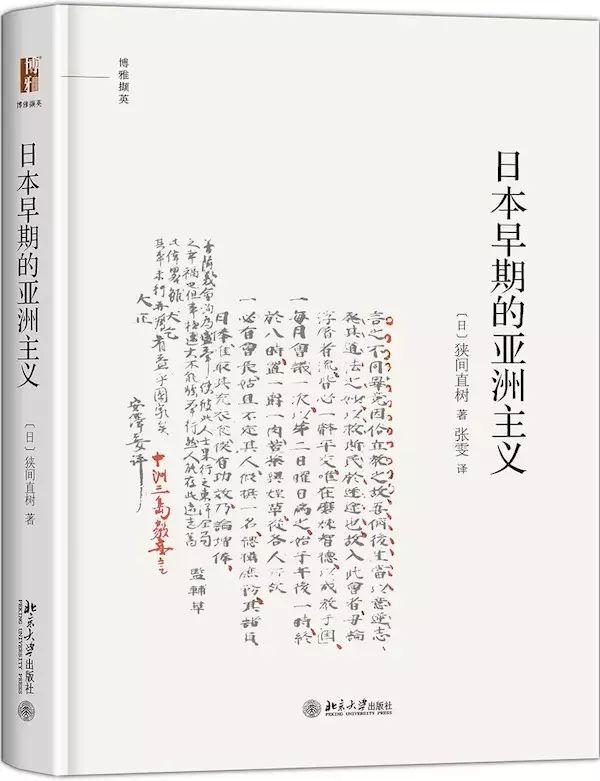
[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59元。
狭间直树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东亚近代史研究者,也是当今京大人文研代表的研究者之一。作为战后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与不少同时代的研究者一样,其研究起步时期的学问深受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特别在当年的京大人文研,有井上清和渡部彻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引导,学术气氛可想而知。狭间早年的一篇论文收入了历史科学协议会所编、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成绩集成《历史科学大系》的《亚细亚的变革》(下卷)中
(狭間直樹「中国近代史における「資本のための隷農」の創出およびそれをめぐる農民闘争」、歴史科学協議会編『歴史科学大系 14 アジアの変革』、校倉書房、一九八〇年)
,也可见他早年在这方面的成绩。此后他致力于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与日本的问题,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
(狭間直樹『中国社会主義の黎明』、岩波書店、一九七六年)
。

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
然而,不多久,中国革命的理想形象很快消逝,中国反而要向日本学习高度成长的经验,传统史观的问题意识自然难以维持。狭间的学术于是也有所转换。不过这种转换并非追随时流。一方面,战后京大的左翼史学并非不重视史料整理与分析等实证工作,在实证史学逐渐占据主流的形势下,这种传统自然得到发扬。另一方面,狭间积极与打开国门的中国学界交流,介绍、吸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成果,同时也影响中国学界。特别是他主持开展的一系列京大人文研的共同研究——涉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为中国研究者熟悉。这些研究除了严谨、实证的学风外,未始不依然包含着探索近代中日两国间的相互影响与非侵略的连带的可能性的问题关心。这本关于早期亚细亚主义的著作,显然是这种问题关心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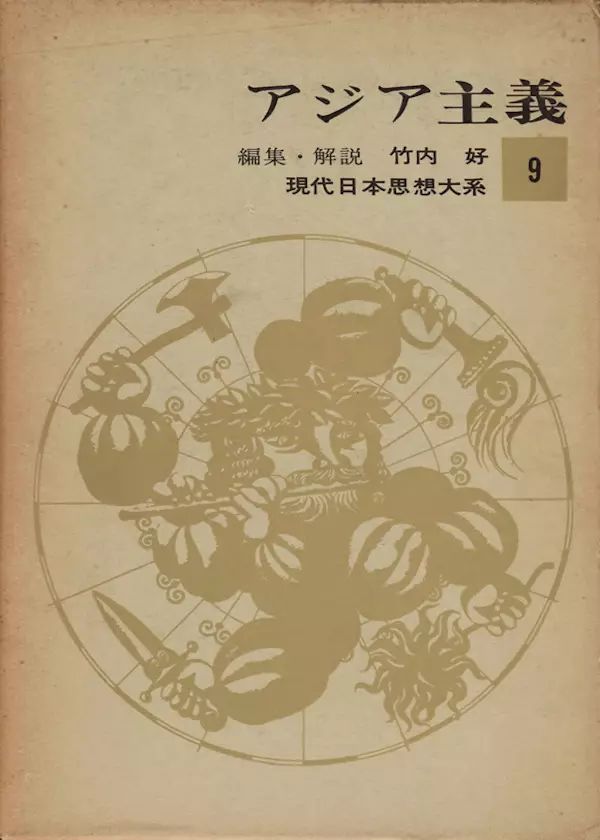
竹内好编:日本现代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卷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并非专门面向中国读者而写,而是由2001至2002年间发表在霞山会(东亚同文会的后继组织)杂志《东亚》上的系列论文组成(原文尚未结集成书,中文版先行出版)。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研究史来看,自从竹内好编纂日本现代思想大系中的《亚细亚主义》卷
(竹内好『現代日本思想大系 9 アジア主義』、筑摩書房、一九六三年)
,发表著名论文《亚细亚主义的展望》以来,亚细亚主义就成为广受近代思想史研究者与论坛论客关注的问题。不过,中国研究者容易忽略竹内好的日本浪漫主义背景,实际上他浪漫与暧昧的文字表达,往往包含了超出具体历史事实的“情念”的关心,旨在唤醒读者某种“日本”的文学教养与感情。在其影响下,具有影响力的亚细亚主义研究,如桥川文三、松本健一、渡边京二等人的业绩,学术意义固然重大,但都充满竹内式的浪漫主义色彩:文章逻辑不甚清楚,主角个人的思想感情经历被突出放大,而历史的实际情况有时却暧昧不明。相比之下,严谨的实证研究固然已经出现(如酒田正敏在“对外硬”概念下的研究),但还不是十分充分。此时狭间介入亚细亚主义研究,便有其学术史意义。此后,关于亚细亚主义的实证研究爆发式发展,近年来走向高潮——这个意义上,本书也可以说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
━━━━━
早期亚细亚主义
仅有的两国共有幸福幻想的时刻
━━━━━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从1870年代末曾根俊虎筹建“振亚社”写起,至1900年东亚同文会合并亚细亚协会,成为最主要的亚细亚主义团体为止,考察了二十年左右的早期亚细亚主义轨迹。其历史叙述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是1870年代末到1890年代初,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振亚社、兴亚会、亚细亚协会、东邦协会等团体,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有真诚的亚洲各国平等连带抵抗欧美的思想,特别是存在将汉语官话作为东亚共通语言的语言构想。然而随着中日围绕朝鲜问题的矛盾激化,亚细亚主义趋于沉寂。
第二个阶段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戊戌变法时期,出现了东亚会、同文会和善邻协会。这一时期虽然在战争中被日本击败,战后的中国却燃起了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同时变法派、革命派等反体制运动的参与者也来到日本,积极寻求支持。这些动向与亚细亚主义产生共鸣,从而产生了亚细亚主义团体活动的高潮期。作者高度评价这一时期包含的中日合作的可能性,也指出其间日本对中国优越意识的强化。
第三个阶段始于1898年,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成为东亚同文会,并整合其他亚细亚主义团体。作者指出由于国家力量的积极介入,早先从民间谋求中日联合的亚细亚主义运动,变得更加积极配合国策,从而逐渐丧失早期运动的亚细亚主义本质。作者将其视为整个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从早期向中期的过渡。

亚家
兴
曾根俊虎
叙述手法上,本书以各个亚细亚主义团体为经,从人物论与中日思想人物关联两个角度展开。前者论及各个团体的主要组织、参与者,后者考察与这些团体有关的中国人的思想行动,及其与日本人的互动。
在介绍1880年代“兴亚会”的活动时,狭间叙述了该会的缘起、组织、纲领所反映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后,就介绍了重野安绎、广部精等人与该会的关联。重野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为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他也关心“兴亚”问题,为访日的王韬提供很多帮助。广部主张学习中文官话,将其作为亚洲的通用语,他使用中文编辑《兴亚会》报告,体现了从语言上追求东亚共同性的努力。
接着,狭间又叙述了中国人对该会思想与活动的反应。驻日公使何如璋、知识人王韬等人都对兴亚会的思想予以积极评价,甚至还参与该会的活动,但同时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提出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时期围绕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的问题,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中方无论对日本“志士”提倡的团结起来抵御西方入侵的亚细亚主义命题有多少共鸣,面对日本强行吞并清朝的朝贡国的行为,都不能不感到疑虑。王韬尖锐地指出:“故兴亚第一义,无过于中日相和,而中日相和第一义,则在还琉球之故土。”
(55页)
对此,曾根俊虎等人均表示这只是小事,是中方人士的“杞人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