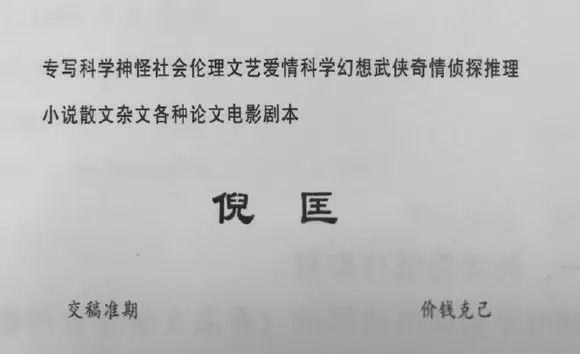本文原题目为《〈论出版自由
〉
》对历史的运用或滥用》,载于
《经典与解释(58):弥尔顿与现代政治》(娄林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年8月)
,
道林(Paul M. Dowling)撰,王涛译
。
注释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
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
虽然古代的历史学家描述的事实即使是错误的,但是他们有很多见解可以供我们采用。我们都不善于认真地利用历史;大家只注意那些引经据典的批评:好像要从一件事实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就一定要是真实的事情。明理的人应当把历史看作为一系列的寓言,它的寓意非常适合于人的心理。
——
卢梭
《爱弥儿》,第二卷
《论出版自由》这部反对书籍许可制或书籍出版事前审查的伟大著作,开篇首先考察了罗马天主教徒发明了许可制。更具体地说,在考察了古代雅典、斯巴达和罗马的审查活动后,弥尔顿揭示了罗马天主教徒如何不断增加他们的政治权力,最终,他们要求书籍必须在出版前接受审查,且必须在获得许可或正式批准后才能出版。对于弥尔顿时代以清教徒为主的伦敦来说,这个论点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清教徒对于没有改革的罗马教会没有任何好感。
但是我将提出,以这种
方式来打量所谓的《论出版自由》的
“许可制的历史”,忽视了弥尔顿的真正意图——至少是最深层的意图。弥尔顿的“历史”根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而是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史的一个典范。要想理解弥尔顿的历史,我们必须朝向希罗多德,而非
伯里
(
Bury
)、
兰克
(
Ranke
)或
伽德纳
(
Gardiner)。
我们需要做出一些界定。首先谈谈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较为容易,因为它就像我们的语言一样为我们熟知。它的目标是准确性。它的问题是:过去发生了什么?它的方法由历史系来传授,主要在于运用书籍、档案、信件、碑文、工艺品等等一些证据。我将现代的历史定义得如此宽泛,并非意图否认现代历史学家之间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差异。对于什么构成一个历史事实,比如,是否可以在重要的军事和政治精英或大众和非精英的行为那里发现历史事实这些问题,历史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也许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现代历史的古典对应物,我如此宽泛地刻画现代历史的原因会变得更为清楚。
如今,谈论古典意义或希罗多德意义上的历史非常困难,就像谈及现代历史是如此容易一样。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古典意义上的历史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思维方式,而且还因为直到最近,历史学家都还没有完全理解希罗多德所研究
的
“历史”的所有特征。对此我将利用一小批晚近学者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
伯纳德特
(
Seth Benardete
)的《希罗多德的〈原史〉》。伯
纳德特的书名
“探原”是对希罗多德原书希腊文标题的直译,伯纳德特指出,希罗多德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准确地回答过去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以现代史学的框架内来理解希罗多德的著作是一种错误。
当然,希罗多德确实讲述了希波战争的一些事情,他确实使用了一些书面或其他档案。但是,希罗多德整理了这场战役的具体资料,他也承认其中有些是错误的,或者不准确,但他整理的目的是为了使那些更具洞察力的读者能够反思这些具体资料蕴含的某些普遍问题。希罗多德的普遍理性(
logos
)包含于这些他讲述的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的具体材料中。
举个例子也许有助于澄清希罗多德的
“历史”写法
。希罗多德在第八卷(节
118-119
)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个故事“在我看来根本不值得相信”。故事讲述了波斯国王薛西斯(
Xerxes
)的一段航行。当风暴来临时,舵手要求船上的波斯人为了国王的安全跳海。据说,波斯人确实都跳海了,船也安全抵达港口。接着,薛西斯马上做了两件事:
他因舵手的救命之恩而赐给他一顶黄金冠,但同时割下了这个舵手的头,因为他使许多波斯人丧了命。
伯纳德特指出,由于这个故事并不真实,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思考希罗多德所谓的故事的
“意涵”(
meaning
)来解释,这种意涵就是希罗多德试图通过这个故事传达的教诲。伯纳德特认为,希罗多德使用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
薛西斯的做法表现了对正义的完美反讽。他的两个行为本身都是正义的,但是将它们合在一起,一个正义的行为抵消了另一个正义的行为,便导致一种荒谬。因此,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说明了有关正义的一个事实:严格执行一项正义规范,偿还所欠之物,会导致自相矛盾。波斯人尤其具有这种对正义的误解,后文会将这种误解显现得更为清楚,因此我们会看到,即使虚假的故事也能够说明有关波斯人的真相。(《希罗多德的》,前揭,页4-5)
如伯纳德特所言,阅读古典史与阅读文学相差无几:读者通过解读书中的诸多具体资料来发现作者的意涵。那么
,我们需要牢记现代
“史”(
history
)
与古典
“史”(
historia
)的差异,还需要牢记,现代史注重事实准确,而古典“史”的作者不拘泥于其事实准确性,但其意图传达的意涵却非常重要。
▲
伯纳德特《希罗多德的〈原史〉》,圣奥古斯丁出版社2008年英文版
现在让我们来看弥尔顿的
“许可制的历史”。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编者和批评家在将这份“历史”纳入现代范畴时碰到的三个问题。在指出这种做法面临的困难后,我将说明,通过将弥尔顿所写内容理解为古典史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弥尔顿的
“许可制的历史”免除了古代雅典、斯巴达和罗马与早期基督教在发明许可制或书籍事前审查方面的责任。但是,为什么弥尔顿要劳烦做出这种免责呢?在钞本时代,书籍的钞本非常少见,书籍副本都出自抄写员之手而且读者人数极少,这个时期的政府当局实施书籍事前审查既不可能也不是一个急迫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只有当印刷机发明后,印刷书籍迅速增多,阅读人群扩大,还应当加上
的是,像伦敦文具公司(
London Company of Stationers
)这样的协会在印刷机发明后垄断这项技术一
个世纪之后,政府当局的书籍许可制才有可能实施,才会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莱斯(Warner G. Rice)
针对弥尔顿所述历史中的这个异常现象指出,
“弥尔顿这里采用的历史方法完全错误”。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根据现代史学的标准来衡量。
另外,在处理古代雅典
的时候,弥尔顿还说,在雅典,
“书籍和哲人比希腊任何其他地方
都要多
”,弥尔顿还宣称,雅典的“长官只注意两种文字,渎神(
blasphemous
)和无神论的,或诽谤中伤的
”(卷二,页
494
)。就苏格拉底时代的古代雅典对书籍和哲人的政治迫害而言,这个说法显然是有选择的,也不全面。《论出版自由》的十九世纪编者
黑尔斯
(
John Hales
)第一个注意到,弥尔顿
并不想做到详尽全面,否则,他肯定会提到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和阿斯帕齐娅(Aspasia)因“不敬神(impiety)”而被控告。
有关这些控告的历史事实文献,他建议读者阅读
格罗特
(
Grote
)的《希腊史》。
但是,当弥尔顿说
“长官只注意两种文字”时,他其实宣称自己已经做到详尽全面了,只是
黑尔斯提到的
“不敬神”并没有包含在内。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进黑尔斯的观察。弥尔顿在对雅典长官如何对待“书籍和哲人”做出历史描述时,并没有提到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这看上去确实有些奇怪。毕竟,虽然苏格拉底没有写书,但是他的哲学智慧肯定非常令控告者厌恶,所以
控告他
“败坏青年,不信城邦信的神,而是信新的精灵之事。”
最后,我们来看弥尔顿的历史叙述得出的明确结论:无论如何,许可制就是罗马天主教徒的发明,而正直的英国清教徒不会采用。弥尔顿的另一位编者
西拉克
(
Ernest Sirluck
)反对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竟然
得到这样普遍的接受,真令人吃惊,因为这个结论完全背离事实
”。他补充说:
不仅是查理一世和劳德大主教,而且弥尔顿眼中真正清教改教者国王和改教者,都采取许可制政策……(卷二,页158)。
萨拜因(George Sabine)在他编辑的《论出版自由》中也要面对这个问题,他提到弥尔顿“高度偏颇的历史”,并建议读者去看《大英百科全书》和《社会科学百科》有关宗教法庭和审查的内容,以了解实际情况。
关于这三个问题,弥尔顿的编者和批评家都假定,弥尔顿是在书写某种有关许可制的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但他有时候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假定本身正是问题所在。原因在于,弥尔顿之书写历史,并不是在现代史学传统之中,而是在某种近似希罗多德的传统之中。解读在这种传统中写成
的
“历史”,仅仅确定史家是否准确书写事实并不够。相反,我们必须认为,无论其真假,那些具体资料都
在表达某种
“意涵”。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我们发现的那些问题。比如“许可制的历史”问题,这种制度始于古代雅典、斯巴达和罗马,远在印刷机的发明使得许可制得以操作和显得
急迫之前。在这里,编辑者和批评家使用的
“许可制的历史”这个标题就过分简化了弥尔顿所做的工作。要想理解弥尔顿的“历史”的复杂性,读者必须密切留意弥尔顿对自己目的和结论的几次重述。第一次说明自己书写“历史”的目的时,弥尔顿仅仅说,他将证明“这项许可制的订立者是诸位不屑于承认的”。但是,在下一段岔开去说了说书籍本身后,弥尔顿再次陈述他的目的,包括两方面的意图:
尽管我反对许可制(licensing),但我还是要引入许可(license)[概念];我将不厌其烦地从历史上引证古代的著名国家制止此种混乱[即书籍写作自由导致的混乱]的办法,然后追溯这种许可制怎样在宗教法庭中产生,为我们的主教们拿来利用,并吸引了许多长老会的长老。
弥尔顿的叙述有两方面的目的:表明古代国家在制止书籍写作的自由或混乱方面的做法;说明谁发明了许可制;出于这两个目的,弥尔顿从古代雅典开始书写这一历史看起来就
合理了。但是,弥尔顿对自己意图的重述没有至此结束。在这一
“历史”的结尾,弥尔顿声称,信奉异教的雅典、斯巴达和罗马这些“古代著名的国家”为“古往今来最好、最明智的国家”(卷二,页
507
)。这个细节反映了弥尔顿在清教徒主导的伦敦可能不想大声说出的“意涵”:在处理书籍写作自由导致混乱这个问题上,不是耶路撒冷、日内瓦或爱丁堡,而是古代异教政权才是“古往今来最好、最明智的国家”。
第二个问题是,弥尔顿笔下的雅典比实际情况更为自由、更为宽容。相较于前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多分析,部分原因在于,这个问题的涉及面要比编辑者所指出的更加广泛。在关于最佳且最明智的异教政制的历史的思考当中,弥尔顿将雅典描述为自由化的城邦成为一种模式,这样,自始至终对不妥协地追求真理或哲学思考的个体与政治社会的实践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弥尔顿就可以轻描淡写了。
至于
斯巴达,弥尔顿认为这个城邦极度军事化,毫无书卷气,所以无需许可制。但是,斯巴达确实找了一个
“很小的借口”(弥尔顿如是说),就把
阿基洛库斯
(
Archilochus
)
赶出城邦。弥尔顿没有说明这个
“很小的借口”是什么,但他的资料来源是普鲁塔克的《斯巴达政制》(
Instituta Laconica
)
293B
:阿基洛库斯被赶出城邦是因为他主张,与其放弃生命,不如放弃盾牌。在一个军事对于其生活方式来说至关重要的城邦里,这显然是不审慎的言辞。但是,弥尔顿这是将言说真理的欲望和政治社会要求之间的张力做了轻描淡写的处理。
至于罗马,哲学如何进入到之前军事化的、无知的早期共和国中这个问题,弥尔顿也是轻描淡写。在弥尔顿看来,哲学这样进入罗马:
当卡尼亚德斯(Carneades)、克利托劳斯(Critolaus)、廊下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出使罗马时,趁机使这个城尝试了他们的哲学,当时竟连监察官加图这样的人都怀疑他们是煽动者,于是便在元老院中提议将他们立即赶走。
加图对这些希腊人的言论的反对,弥尔顿视之为老年人一时的过度警惕。但是,这个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普鲁塔克的《加图传》和西塞罗的《论共和国》
3.6
)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首先,克利托劳斯这位亚里士多德逍遥派的领袖人物并不在场。其次,另外两个人是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怀疑派和廊下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只是不够审慎。卡尼亚德斯做了两场演说:一场演说论证正义,另一方演说则反驳正义。在罗马这个如此需要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的地方,公开诋毁正义显然不是一件小事。但是,弥尔顿并没有反思早期罗马与哲学的这场遭遇呈现的问题。他隐藏了不妥协地追求真理与政治社会的要求之间的张力。
有人会反对我对哲人和古代城邦之间冲突的解读。也许弥尔顿根本没有捏造关于罗马的事例。也许,他仅仅是转述了普鲁塔克和西塞罗之外的其他资料。当然,我无法证明不存在其他资料,但是我可以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论出版自由》的编者们并没有发现这种资料。也许更重要的是,鉴于晚近对这种古典历史的重新发现,我们为什么要将精力和关注只放在那些事实准确的历史上?如果弥尔顿已知的材
料对相关事件有一个说法,而弥尔顿本人却多次偏离这个说法,甚至成为一个模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尝试确定弥尔顿的偏离如何符合他的历史书写的
“意涵”?
我们可举一例,弥尔顿在谈及哲学进入罗马时,加入了克利托劳斯这个普鲁塔克和西塞罗都没有提到的人物。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哲学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应当因一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代表的在场而有所节制,这对弥尔顿的故事版本不是很恰当吗?因为后者对政治和道德事务感兴趣,而且理解审慎这项德性。如果这就是克利托劳斯在场的原因,那么,弥尔顿将他置于两位激进哲学同伴
中间(
“卡尼亚德斯、克利托劳斯、廊下
派的第欧根尼
”)以表明他的节制意义,这不是很恰当吗?
但是,即使我们假定弥尔顿以希罗多德方式写作,为什么他自始至终对哲学和古代城邦的张力轻描淡写?我认为,弥尔顿是想表明,他讲述的这些异教政制应当成为现代基督教英国的典范。它们的自由化和宽容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可堪学习的榜样。即使这个事例在历史层面上不够准确,但是它能够激励英国走向宽容,而这正是英国可以也应当做到的。
为了了解弥尔顿有关古代城邦的事例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将其与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后文对英国提出的建议加以比较。正
如雅典和罗马惩罚两种书籍和哲人,弥尔顿也建议英国惩罚两种书籍和哲人。英国的书籍事后审查应限于那些被弥尔顿称为
“恶意的”或“诽谤中伤的”书籍(卷二,页
569
)
。这两个类别与雅典和罗马的
“渎神和无神论的,或诽谤中伤的”类似(卷二,页
494
、
498
)。
“智者”(
wits
)参与教学和宣讲活动及没有见诸书籍的其他活动,关于他们,弥尔顿建议普遍宽容新教教派。他拒绝宽容两类人,罗马天主教徒和做出
“违背信仰和破坏风俗习惯的,不敬虔甚至绝对邪恶的行为”的人(卷二,页
565
)。
弥尔顿的这种不宽容基于完全世俗和政治的理由,而非彼世的、神学的理由。在弥尔顿看来,罗马天主教
“要消灭一切宗教和世俗的最高权力”,坚决不能予以宽容(卷二,页
565
)。
20
世纪一位作家的下述说法表达了弥尔顿这里的意思,即
“有可能的情形是,普遍宽容必然受到了不宽容那些不宽容的人的启发。”在
17
世纪,罗马天主教就是不宽容的人。另一方面,弥尔顿来提到不敬虔的、绝对的邪恶时,并没有说它们是对神的冒犯,而是说它们会造成混乱,
“使得(法律)自身非法化”(卷二,页
565
)。
弥尔顿这里是在援用政治哲人的下述教诲,即政治社会的法律需要公民的某些态度和道德倾向的支持。比如说,信奉一位在死后审判人的罪行和信仰的神,这种信仰似乎支持人们服从法律规定。诸如不敬虔和绝对邪恶这样的混乱,会削弱对法律的这些支持。但是,这种哲学推理未必属于某个宗派,更不见得是一般信徒在思考宗教信仰的好处时会出现的想法。许多宗教都会有一些最低限度的信条,鼓励教徒守法。无论如何,弥尔顿认为,如果英国以雅典和罗马的那种世俗的、政治的角度来考虑书籍和哲人问题,英国就会变得更为人道、更为理性。
最后一个问题。萨拜因说弥尔顿写的历史是
“高度偏颇的历史”,西拉克也指摘弥尔顿没有提那些免于许可或参与实施事前审查的新教徒。似乎在这些编辑者眼中,弥尔顿与他的大部分新教读者一样心怀偏见,将许可制与遭到强烈厌恶的罗马天主教徒视为一路货色。这个问题过于庞大,无法在这篇论文的有限篇幅内予以完全的回答。若要提供一个全面的回答,就需要考察弥尔顿的整篇演说,而不仅仅是
5
页篇幅
的
“许可制的历史”。拙文先开其端绪。
让我们首先关注一个问题,藉此检测一下弥尔顿与他的清教读者的偏见之间的关系。这就是
弥尔顿如何处理罗马皇帝刚刚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罗马。这个问题与那些希望按照早期教会模式改革基督教的清教徒休戚相关。如果弥尔顿认为纯洁和原始时期的基督教存在真正的缺陷,他们肯定会感到不安。弥尔顿首先说了一些令人安慰的话,虽然说的有些模糊。他说,早期基督教的控制
“并不比以前的做法更严厉”(卷二,页
500
)。问题在于,不比哪些做法
“更严厉”?它指的是前面段落的哪个地方?弥尔顿是指相对自由的雅典政制和罗马共和国晚期吗?还是说,他是指前两句中提到的罗马帝国的暴政?
从那时以后,罗马帝国除了暴政,几乎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看到坏书被禁得少,好书被禁得多,那也一点不稀奇。(卷二,页499-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