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技术环境下知识形态会带来一些改变,渐渐模糊原有知识的界限,甚至逐渐修改知识在汉语中的意义。
在上一篇崔老师的专访中,崔老师和我们讲述了自身的学术经历,以及对学术生活的看法。在本篇推送中,我们则继续与崔老师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知识与媒介的关联以及相关问题。
采写︱刘浏 梁方圆

引擎:老师最近的研究成果都比较偏向于“媒介”与“知识”的关联,老师如何看待“作为知识的媒介”?这一视角为何在先前的学术领域中被忽视?
首先知识社会学对新闻研究是有比较明确的影响的。但这部分讨论比较集中,主要涉及新闻生产和对新闻的功能主义的理解。其次,知识作为一种媒介效果研究在英文的文献里是非常多的。在国外研究中,获取知识是政治传播中的一个环节。比如,美国公民会投票给希拉里还是特朗普?投票的前提是你要知道候选人有什么样的政策。这些知识如果都不知道,这一票投出去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它可以看成是一种美国的“本土研究”。
我也做一些测量知识效果的简单研究。我很多时候都关心“公共事务知识”。在中国,我们从小就要了解国家大事。此外,我们也有很多政治类课程,帮助我们理解本土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我们也提倡“知情社会”、“信息公开”,希望官方和民间的沟通可以顺畅,一些宏观政策需要“上情下达”。
尽管政治传播模式差别很大,但是在认知层面上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有一定的对应性
。此外,在国内很少有学者去做知识这一块的研究,西方虽然做的很透了,但中文文献里出现得很少。
引擎:老师最新的论文中指出了“今日头条在信息分发方面并未出现明显的结构失衡,同时它作为一款新闻产品在告知信息方面的表现较为理想”。这个打破了以往我们对于今日头条的观点。但我们以前所说的“信息茧房”是不是一个悖论?即便没有算法推送,我们似乎也是在不断寻找自己喜欢的文章与观点。进一步说,这个理论是否能被用于形容“今日头条”?毕竟在桑斯坦的语境中,信息茧房是用于形容搜索引擎的,但搜索引擎是基于用户主动输入内容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收算法推送的新闻。
首先,我这篇文章并没有讨论今日头条和“信息茧房”的问题。它回答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今日头条作为一款新闻产品,表现还不错,看上去确实可以让人们获取知识。信息茧房有很多类似的说法,例如“过滤气泡”、“回音壁”等等。它的根本机制有两个,
一个就是选择性接收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人会看自己喜欢以及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东西,因为“异己”的信息或观念会让人很难受。这背后的机制很简单,因为人的认知是有惰性的,大脑是很耗能的,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要就是偷懒,因为你要储藏热量。当一个人处理和自己之前理解不一样的信息就很消耗能量,所以人基本上就非常愿意去接受那种已经掌握的信息和观点。

另外一个机制就是
媒介选择
,当我们不止有一份报纸,不止有一个电视台频道,当我们能在不同的频道和内容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们的媒介选择性就增强了。互联网也好,社交媒体也好,无疑是让媒介选择更加丰富了。
有学者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高选择的媒介环境(high-choice media)
。
所以,选择性接触和媒介选择这两个条件,肯定不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情。大众传媒时代很早就已经开始,当美国战后电视台开始增多时,观众便已经可以选择了。这些电视台每个都有自己的内容策略,这就肯定涉及到媒介选择问题。所以说,它是一个很老的现象。
算法推送技术让我们更加关心“信息茧房”这类问题。当然新技术会加深一些长久的担忧。在我看来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恐慌——因为从规范性的角度出发,人们总害怕观点的极化。我们总希望公共是一个整体,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公共生态。选择性观看的背面其实还有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回避,有人说社交媒体会让人这种不经意间的接触变少了,比如说你以前看新闻联播,你可能只爱看里面15分钟的内容,但是那15分钟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也会看到,然而社交媒体或者算法就可以帮你把这15分钟不喜欢的东西去掉。仿佛你是一个骄纵挑食的小朋友,算法或者什么就是一个宠溺的父母。
但实际并不一定就如此,算法会推荐给你一些很杂的东西,它
除了给你个性化的东西,也会推一些整体热度(global popularity)和在你同辈群体里很流行的东西(peer filtering)
。此外,虽然人会选择性接触,但不见得会完全回避掉不一样的东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很多年轻人都是粉丝,用爱发电支持自己的偶像,生活在彩虹屁里,但是不是也会定期去看看黑粉或者喷子们说什么呀?我想是会的。这很正常,人没有那么简单的。关于算法对人的认知效果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糟糕。最近有不少重量级的研究,也试图在建立一些平衡的视角。所以我倾向认为,
批评算法推送或者任何一种新传播技术形态前,我们先要在实证的层面去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
。
引擎:在互联网这个延森所说的“元媒介”语境下,知识所依托的载体已经非常的多元化。老师觉得在这一环境下,知识原有的含义会被消解吗?例如,如果我们把游戏视为一种知识,那王者荣耀中把历史人物变相化地处理是否会产生知识的误导?
我现在主要研究的两个东西非常割裂,一个是知识,另一个是娱乐。但是你如果退一步看这两个东西,事实上他们是关于
公共空间的理想的两个面
。直觉上,我们希望公共空间里是以严肃的和有质量信息为主,同时减少娱乐的、琐碎的、情感的信息的干扰。但在这个时代,娱乐的东西特别多,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当有媒介选择的时候,泛娱乐就不可避免了。算法这时就能迎合人喜好,同时算法又是挣钱的东西,所以娱乐的内容就会变多。

我觉得在这种技术条件下,那种古老的那种关于一个纯净的公共空间的理想,已经难以实现了。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截然二分
,娱乐
和知识或者严肃的信息这两个东西会融合或者并置
。这二者同时以相同的显现度出现在你的页面上会是一个常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坚持说一方消解了另一方,一方破坏了另一方的严肃性,可能是有点一厢情愿。我可能会更看重如何用轻松的方式去传递所谓的严肃信息,这会变成未来更加重要的一个趋势
。参照后真相的说法,你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有一个所谓“后知识”的时代正在来临。
引擎:老师如何看待当下盛行的“知识付费”?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使用“知识付费”?先前有许多自媒体帐号抨击罗振宇的“得到APP”,认为人们从中获得的只是被人嚼烂的二手知识,并将其视为一种观点的灌输。但这类观点似乎过度打压了新萌芽的知识传播创新机制,毕竟碎片化的时间本身就可以利用起来,在这些时间听一些知识似乎比不听总归是会好一些?
我觉得“得到”这类APP是很好的互联网产品,知识只是他们的一个名号而已。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传播力和市场导向的东西。
对这类产品的批评,很大程度都是布迪厄意义上品位和区隔造成的
。
对于“得到”的读者而言,他们真的在意原汁原味吗?他们或许就不需要。书就在那里呀。他需要的就是这个新的产品。比如“得到”会讲解《娱乐至死》、《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等,这类书如果你不讲解,在学术群体外,有多少人会去读?那些学术类的书反而以通俗化的方式能够进行传播。但批判者往往是在用一种传统的知识观在打量这类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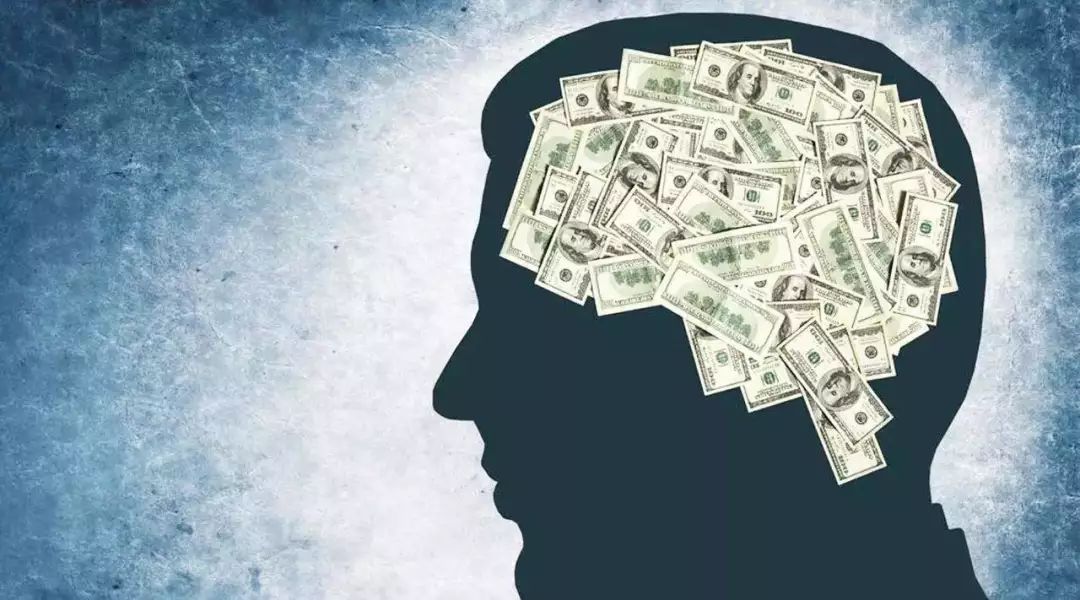
我觉得互联网知识产品,他只不过是用了“知识”这个词,其实最根本的是内容。因为在日常生活话语中知识这个词,尤其在中文的语境里面,知识有比较高大上的意涵,知识为一部分人所有,因而似乎知识的界限就比较固化,排斥其它的内容成为知识。也许新的技术环境下知识形态会带来一些改变,渐渐模糊原有知识的界限,甚至逐渐修改知识在汉语中的意义。那也意味着原有的知识精英群体受到了一些冲击。
引擎:最后,能不能请您为引擎的读者推荐几本您认为值得一读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