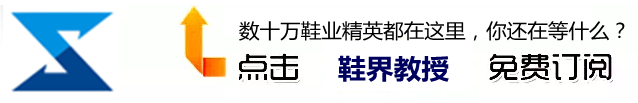
鞋界教授
微信号:
live555888
鞋业界最专业
有价值,有趣,有爱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鞋业圈子!
鞋界教授个人微信号:
aiwangyongjun
直面行业真相,洞见鞋业未来
【前言
】
随着近几年温州大规模拆改违建、原料人工等成本一起飙升、个体户转企业等政策来回“折腾”,温州中小民营企业利润已经“薄如刀片”,甚至有老板表示企业已经是在零利润“空转”。
王勇均

来源:中国经营报(图片来自网络)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倒闭了,老板吃喝嫖赌欠下3.5个亿,带着小姨子跑了……”几年前,神曲《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洗脑般传遍大江南北,而让人惊讶的是,原本以为这只是小商贩博出位的营销噱头,没想到却是浙江温州多年前真实上演的一幕。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近期的调研中了解到,在历经了大起与大落之后,号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老板们近几年也已经是“曾经沧海”,不求大富大贵也成为部分人的口头禅。但商海沉浮,岂是凭一己之力又可左右。“即便企业想关张也不容易,毕竟还有一堆债务和应收、应付在。”
而随着近几年温州大规模拆改违建、原料人工等成本一起飙升、个体户转企业(以下简称“个转企”)等政策来回“折腾”,温州中小民营企业利润已经“薄如刀片”,甚至有老板表示企业已经是在零利润“空转”。
成本飙升利润薄如刀片

35岁的郝伟(化名)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经营20多年的锁具生意,除了公司老板的身份,他还是一名滴滴司机。每逢周六日的两天里,他开着自己的宝马X1穿行于温州大街小巷,接单跑活。“现在老婆快生二胎了,多赚点奶粉钱。”他自嘲道。
郝伟说,之所以他能当“甩手掌柜”,一来是他父亲为他留下了好的管理层,公司经营很少用他操心,二来是锁具生意近几年不景气,也确实不用投注太多精力。
“一把锁成本二三十元,扣除各类成本到手利润也就是3%,而且还不算报废率。现在锁具行业都是白菜价,赚不了钱也饿不死,在夏天甚至还不如我老婆的3家奶茶店赚的多。”郝伟说,“在夏天,一家奶茶店营业额都在5000元/天左右,而锁具在夏天一天也卖不出去500把。”
与郝伟同样深感经营之难的还有秦正伟(化名)和李海超(化名)。
浸淫鞋服行业20多年的秦正伟白手起家,目前公司年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但同样扛不住飙升的成本。“近几年成本涨得太厉害了,现在工人工资已经达到7000元左右/月(不含社保等福利)了,而且平均每年还在以10%左右递增。”秦正伟说,“我们现在的净利润率只有1%~3%,甚至是零利润。”
而公司年产值1700万元左右、深耕汽摩配行业的李海超也坦言,员工工资现在人均4500元左右/月(不含社保等福利),而且还在以每年15%~20%的比例递增,而除了人工越来越贵,原材料节节攀升也已经越来越挤压利润空间。
事实上,企业的感受也集体反映在统计数据上。
温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2017年的13年间,温州对外出口数据也是经历过山车。其中2005年~2008年的4年间,出口总额分别从61.84亿美元上涨至119.04亿美元,年均增幅在35.2%~17.3%之间,可谓高歌猛进。但自2009年开始至今,则呈现负增长或疲软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服装、鞋类等作为温州传统支柱性产业则下降或疲软更为明显。
记者粗略统计,2005年~2013年,鞋类出口额从15.84亿美元上升至51.56亿美元,除2009年下降,其他年份均保持较高增长;但2014年~2016年,则分别下滑至48.13亿美元、42.80亿美元、253.7亿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6.6%、-11.11%、-4.3%;唯有2017年有所上升,至267.7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5.5%。
“2008年金融危机时,制造业在最困难的时候净利润还在12%~15%左右,但这几年净利润却只有1%~3%,可以说薄如刀片。”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市工商联副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道。
“现在是资质好的企业我们追着给贷款,但人家不需要,而想要贷款来补窟窿的我们则拒绝。”上述银行人士感慨道。
“温州的老板现在都看透了,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而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向企业倡导,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尽量避免动用杠杆。”温州中小企业协会执行会长许剑翩说。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7年温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多年来,温州市坚持把化解“两链三险”作为首要任务,累计帮扶风险企业1600多家、处置不良贷款1590亿元,不良率从最高时的4.68%下降到2.69%。
拆走“中小微”

事实上,中小民营企业除了因此前深受民间借贷危机打击士气外,近年来温州因棚改也让不少中小微企业元气大伤,而正如郝伟所言,净利润低至尘埃,甚至是零利润空转的也不无可能。
“我们企业在2016年还是规模以上企业,不得已从瑞安搬到平阳县的工业园内,而之所以搬迁是因为此前当地政府把本该给予我们的土地指标卖掉了,导致我们的企业一直处于违章建筑状态中,随着温州大拆大改,企业只能被迫搬迁,现在入驻同一个园区的企业60%都是来自瑞安。”郝伟说。
企业的搬迁并不是简单地挪个地方,而更多的是背后的一本经济账。“我们每年光在路上的损耗就高达50万元以上。”郝伟说。
何为路上损耗?
据其介绍,因为公司并非普通制造业企业,所用工人必须是熟练工,而从瑞安搬迁至平阳后,因为园区配套尚未完善,招工难等持续困扰着企业,为了使企业正常生产,只能高价聘用既往的瑞安工人,但其代价是企业将为此支付员工住宿费、伙食补贴费,甚至向园区购买员工夫妻房。“如果从企业单纯经营角度来说,企业的毛利润在20%以上,但因为其他不必要的成本等导致,公司现在基本零利润运行。”郝伟说。
温州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也坦言,之前温州的中小企业基本都属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场地就是自己家或租别人家的房子,虽然大部分属于违建,但毕竟是零租金或低租金,但随着棚改的拆除,中小企业也就失去了很大的成本优势。虽然温州的各个区县都在推广小微园对其招商,但他们并不愿意入驻。“因为重新购买或租赁厂房会把成本抬高,而且要搬到偏远的工业园里,毕竟不如在自己家方便。”
“一刀切的拆迁对小企业来说是灾难,拆10个死7个。”许剑翩惋惜道。
万洋集团总经理吴建民表示,很多中小企业被拆掉后,除了部分进入到工业园区,更多去了江西、安徽和江苏徐州等地。“城市建设是有周期的,要处理好拆和建的关系,对中小企业而言要先搭建好工业园区后再拆,这样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而事实上,被拆掉的中小微企业并非能轻易入驻所谓的小微园区。记者在走访某小微园招商中心了解到,凡是入驻的企业不仅要符合政府产业导向,每年还要达到亩产税收的标准才能购买厂房进驻园区。“温州的小微园基本都是如此,而我们这里的标准是2000元/年·平方米,并且企业5年内转让,如果企业破产只能由开发商或政府回购。”
不过,郝伟在采访中也表示,虽然此前家庭作坊式的成本很低,但也时时刻刻面临着电线老化等火灾隐患,现在入驻园区后,环境确实不一样了,不用再像过去那样提心吊胆。
“个转企”来回折腾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不仅是温州的中小企业被折腾,甚至连个体户也受到牵连,随着城市的拆迁改造,不少靠租赁沿街铺面的个体工商户也被连带拆除。不仅如此,几年前盛行于温州的“个转企”运动也让老板们叫苦不迭。
“现在温州大街小巷连卖包子的早点摊贩都可以说是老总。”温州当地人说。
河南人张晨(化名)和朋友来温州已经多年,做个体户的他靠开按摩店为生,年收入基本在三四十万元左右,而就在前年,辖区政府部门上门要求他将个体工商户转变为公司来运营。“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只是政府说改也就改了,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变成企业后平均每年要多缴3万~5万元的税,所以后来我又托关系变更回个体户了。”
上述温州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个转企”是2012年省里说浙江的个体户占比过大,而企业占比小,而且部分个体户已经体量很大了,所以就要求把符合条件的个体户转变为企业,当时有个说法是“要把老板变成老总”,所以省、市相继成立了转企办,虽然并非强制,但也是有指标考核的。
“当时个体户转企业是有很多优惠政策的,例如转型后三年内免税收,温州为此也掀起了宣传热潮,工商部门还推出了全程无偿代办服务。”上述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说。不过因为后期地方政府承诺的优惠政策无法兑现和落实,所以在2013年就已经大批出现企业又转回个体户的情况。
据记者获得的一份此前温州市工商局内部“个转企”专题汇报内容显示,截至当年10月底,温州市已累计完成“个转企”21910家。对照彼时省政府下达的全年完成5100家的任务目标已超额完成,完成率为429.61%。对照省政府给温州市三年完成“个转企”12700家的任务目标,完成率为172.99%。同时,对照温州市定出的2万家任务目标,完成率为109.55%。
记者注意到,该汇报内容也提到,随着“个转企”活动的推进,已发现12个方面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反映转后税额等负担增加,甚至出现政府部门强制变更办理“个转企”的现象。汇报内容举例称,某农家乐饭店在转前每月地税50元,转后每月缴税近1000元,增加近20倍;而原本转前不用纳税的,转后则国税部门上门催缴。据现有数据可查,仅在2014年~2015年间,温州市“个转企”数量分别为2.3万家和1.8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