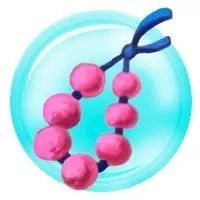本文选自另维新书《每一天梦想练习》。
图/阿宗
尊重摄影师版权,图片请勿盗用,如需转载请联系摄影师本人。
阿宗是我最无法忍受的朋友。
但我还是忍受他,因为他也是我最酷的朋友。
我见到阿宗的开场白永远一句话。
“把你的故事写出来吧,不然太暴殄天物了!”
他操一口襄樊话:“么(没)文化,不会写。”
用我们湖北土话讲,他小时候成绩差得很。就上了个省内三本分校,还是艺术生。
没想到毕业两三年摇身一变,足迹遍布全世界,旅游部门抢着邀请。妥妥的环球摄影师,年入百万,绰号人赢。
人生赢家。
他变身人赢阿宗之后,我妈依然说:“找另一半一定要擦亮眼睛,有些男人再好也不能嫁,比如阿宗那样的。”
01.
阿宗向来神出鬼没。
暑假,我在普华永道做审计师,忽然收到阿宗的微信。
“我在北京,明早飞玻利维亚,吃个晚饭?”
年初,邮轮开辟四十六天环行南太平洋航线,我是百来个受邀旅游博主之一。
阿宗是唯一受邀摄影师,我们一起漂在船上干活儿,陪阿宗妈卡五星[襄樊特有的一种三人麻将]。
下船至今,我闭关写新书,回西雅图继续攻心理学和会计学位,申请四大,做旅游博主。
他去芬兰拍极光,去印度尼西亚拍星星,去美国拍日食,去四川拍熊猫。
我们又已经小半年不曾碰面。
我说:“好啊,我赶紧把手头的活儿弄完,我们公司楼下见?就是央视大裤衩正对面那栋。”
三十分钟后。
“到了。”
我急忙收电脑,进电梯。
在大堂里三层找外三层找,不见人影。
我说:“你人呢?”
他不吭声消失就算了,还大半天才回消息,留我踩着高跟鞋在人流里干着急。
“我刚刚等你的时候看到大裤衩旁边有四栋没竣工的楼,距离刚好,感觉能拍地标,就爬上来了。”
我一脸黑线,说:“好拍吗?那我也上去。”
“你别来。”
他连忙阻止:“这楼还没盖好,地也没铺,也没墙,还巨高,贼危险。我刚刚开门,门把手连门一起给人家拧掉了。我怕一会儿有人找事,我带着你不好逃……”
我勾勒了一下场景:一个小眼胖子一把拧掉一扇门,贼头贼脑溜进建筑工地,在没墙没地板的高空之上时刻准备拔腿逃命……
成龙的电影才敢这么拍,我打消入伙的念头,改做知心姐姐。
回复:“哦哦哦,那我去7-11买点吃的,你拍好了下来给你充饥。注意安全。”
阿宗出现的时候,左右手各拎一个三脚架,身宽体胖,气喘吁吁面红耳赤一阵小跑。
越过我也不停步。
我小跑追上去。
“怎么了怎么了!真追上来找你赔门了吗!”
晚高峰在身旁,马路上,汽车们亮成一条红红黄黄的霓虹小溪,北京城变成一座巨大的停车场。
我和阿宗一前一后逆流小跑。
有人侧目,奔跑的阿宗也不管。
他一边跑一边回答。
“今天撞大运,肯定要出牛×日落!我刚刚构思了一哈(下)子,要是能在对面那栋大楼上取个大裤衩日落,加上这条街上慢慢亮起车灯的车流、路灯、店儿,弄个延时出来绝对牛×!”
他在说十几个街口外的阿诺药业。
我被他带出了襄樊话,在东三环北路上边跑边喊。
“现在克(去)爬那栋楼?你莫(别)光看到近,实际上远滴狠(远得很)!”
他倒比我清楚,回喊。
“日落还有二十分钟开始,跑跑锻炼身体,赶不上去球(算了),赶不上吃饭克!”
还真给他赶上了。
大楼戒备森严。
他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詹姆斯·邦德,因为常年不修边幅,冬天冲锋衣夏天破T恤,很不时尚,只能当乡村版007。
他熟练地收好器材,蒙混过保安,研究了一下大楼布局图,继续狂奔。
转眼之间,阿宗已经找到两个完美的架相机制高点。
只见他从背上的超大黑书包里抖出一堆工具,全部装好,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喘气。
我喘得直不起身,按住膝盖。
我问:“你要拍多久?我怕再晚餐厅就取消我们的订位了。”
“十五秒一张,960张。”
我:“…………”
夕阳开始了,果然是北京城难得一见的红霞漫天。
我忍了三秒,咽下一句“你知道我中午饭都没跟同事吃!坐在办公室里一边啃早餐剩的半张煎饼一边在大众点评北京餐厅早早订位!觉得你难得来北京我不能亏待你!然后一下午一边饿肚子一边安慰自己没事晚上吃好的补回来……吗!”
怀着内伤,我说:“那我先走了啊,本网红晚上要一直播健身,等不到你拍完。”
阿宗背对着我捣弄相机,好像没有听见。
我知道又到了我说一句话,平均问三遍等十秒,才能等到他“嗯哼”之类的敷衍的时候了。
我在翻脸之前果断地走了。
深夜两点半。
我在被窝里,刷到阿宗一分钟前更新的朋友圈。
一张相机照片,相机屏幕是漫天橙红里的大裤衩,定位药业大厦。
“收工!今天运气不错,撞大运撞上北京这种夕阳!”
我回了一个微笑挥手再见的表情。
阿宗私信我。
“另维,我今天绝对是专门找你吃饭的!”
我回复:“滚。”
我没有生气,我早已历劫成仙。
在船上和这个人朝夕相处了四十六天之后,无论他怎么出幺蛾子,我都已经波澜不惊。
02.
那时候船过赤道无风带,水天一色,湛蓝得漫漫无垠。
天上无云,海上无波。
我们背上相机拍船头。
船头风最凛冽,人只消靠近那一带,立刻被吹得说不出话,一张口风就灌满嘴巴。衣角和发丝纷飞,摇摇欲飞。
游轮大约出于安全考虑,整个船头都围上了巨大的塑料挡板。
塑料挡板斑驳,船客们镜头伸不出去,放在它后面,一片模糊。
船客们兴致勃勃来,败兴而归。船头很快人烟稀少了。
阿宗说:“我要一个船头景。”
他上上下下打量,观察地形,一丝不苟。
突然一下子,他胳膊一伸腿一蹬,翻身站上栏杆。
如此,人刚好比塑料挡板高出一个头,相机架在挡板沿上,问题完美解决。
我连忙学样。
调试相机,站上栏杆。
——好一张太平洋上的乘风破浪!
马上我又十分可惜。
“……构图不够完美哎,镜头要是能再多框进1/6的船头就好了,可惜我们已经爬到最高处了。”
我说完,没听见阿宗的回音,扭头看他。
瞬间吓出一身冷汗。
——人呢?!
我吓得差点摔下去。
抬头,阿宗正又胳膊一伸腿一蹬,屁股坐上了挡板,整个身子落在安全罩之外。
船本来就晃,他迎着风,身体都没办法固定,再赤手举相机,根本什么也拍不了。
我想喊:“下来吧,太危险了!”
不敢喊,怕一惊着他,真把他惊得掉下去了。
只能屏住呼吸,见证他收起相机,挎在脖子上,然后挪动屁股,小心翼翼探出一只手,抓不远处的桅杆。
那桅杆在狂风中呼啸。
一个没抓稳,掉下去被吸进船底四分五裂,绝对是一瞬间的事。
阿宗抓紧桅杆,灵活一哧溜,手脚并用,像树袋熊一样绕上桅杆。
固定住了!
他麻利架好相机。
我这才敢大口呼吸,大声叫喊:“你不要命了!”
阿宗拍完照片,低头俯视我,还是那口懒洋洋的襄樊话:
“这儿角度好。”
阿宗的照片拿出来,正是我想要的多1/6的船头。
怎么拍出别人拍不出的风景大片?
王安石在963年前就教过世人秘诀了。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道理我懂,志我有,也不算胆小,可是面对根本没有可能到达的地方,我自然而然的想法是:“好可惜呀!”
而阿宗想方设法,创造可能性。
后来我渐渐发现,阿宗没有想方设法,不是在挑战自己,也根本没有“加油哦,你可以的!”的下决心过程。
他是本能。
前方有瑰丽,他本能地,哧溜一下就上去了,像有神明或者魔鬼在拉他的手。
03.
阿宗环航南太平洋的时候,二十六岁,已经是中国最好的星空摄影师之一。
客户爱极了他拍的视频,13万的船票赞助他两张,叫他带上助手,工作任务是用四十六天拍一段几分钟的视频,而客户只要使用权,并且另行支付使用费。这待遇有且仅有阿宗一个。
画画班上的发小谢毛毛,大学毕业后,在新加坡做铁路工人。
阿宗把他招回来,倾囊相授,组成阿宗团队,一起上船。
于是,我们三个襄樊娃子,在阿宗的带领下,满船上蹿下跳,不分昼夜。
我们一边找地方架相机,一边见识更多阿宗神奇的本能。
夜里一点拍星星。
阿宗要穿过一条不起眼的甬道,去一条人迹罕至的小楼梯,躲避光污染。
他拧开门把手。
只见地板上布满凌乱衣衫,顺着往上望,乖乖,偷情的意大利人和中国大妈正一丝不挂、纹丝不动、惊慌失措看着我们。
阿宗说了一句襄樊话,面不改色走了。
他说:“借过。”
我和谢毛毛捂着脸跟在后面。
我又渐渐发现,
阿宗的横冲直撞不是莽撞。他脑子相当有数。
所有客房的布局、发动机和排污口在哪儿,他上船前就搞得一清二楚。
他脑子里有个亚特兰大号3D全景图,里里外外360度无死角旋转剖析。他说船上没有更好的角度,就没有更好的角度。
阿宗飞无人机,一样的风格。
船上的乘客,都是有四十六天的闲,还有13万的钱的人。富爷爷阔奶奶站在甲板上拍日落,简直是一场奢华摄影设备展。
他们什么刁钻新奇的设备都有,加上近百家旅游媒体和摄影博主,甲板上简直天天有人在飞无人机。
很快结论就出来了:船上飞不了无人机,一飞就炸机,葬身大海,没有例外!
阿宗背了四个无人机上船,不着急飞,每天敞开落地窗在房间打游戏,冻得访客们直流鼻涕。
忽然他游戏不打了,站起来:“走,飞飞机克。”
我说:“你游戏里的人想打死你。”
他说:“这天气飞无人机牛×得很,赶紧赶紧!”
话音未落,已经连人带设备没影了。
阿宗飞无人机,掏出一面小红旗,一看旗帜飘扬的方向和强度,就知道能不能飞。
他观察完风向和风速,还结合船速做算术。
他教我:“船上风大,无人机一上天就会跟着风往后跑,船又在往前开,加上信号干扰,只能全手动操作。你要观察,现在船在往南半球开,风向西北,船速××,风速××,只要这三项数据在这个范围里,都可以试试起飞。要抓紧时间,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图/阿宗 太平洋上的邮轮,阿宗航拍作品,另维同学见证了拍摄全过程呦~
我说:“大哥,你不是成绩巨差还是美术生吗,怎么会物理?”
无人机在他的解释声中“唰”一下飞上天空,转眼消失在视线里。
他说:“网上看的。”
阿宗不仅上网看,他还善于抓住一切机遇学习。
后来我参加无人机的品牌活动,阿宗叮嘱我他们的专业飞手不少是工程师出身,对机器性能和极限极其了解,要我抓紧机会多问,那些比他们给的钱值钱。
好多人混到阿宗这份儿上,出席商业活动露个脸就走了,阿宗赖在工程师身边研究机器。
海上航拍果然意外重重,阿宗幸运了几回,无人机终于失控。
大家都在惋惜大师的机器也要葬身太平洋了,阿宗没放弃也不着急,他一边追飞机一边大喊谢毛毛。
一早守在船尾的谢毛毛闻声,手里的毛毯一甩,就把无人机扑了下来。
我越了解阿宗越发现,他应对意外的办法比意外还多,都是安排好了再出手冒险。
他坐在甲板上检查无人机,报了几个确认损毁的零件,叫谢毛毛去取工具箱。
我们拉他吃晚饭,他坐上餐桌旁若无人地换零件、修机器。
那股子钻研又专业的劲儿,我如果不是一早认识他,一定会误以为他是个学霸。
04.
旅行体验师们抱怨这行苦,常说别的工作都是越老越值钱,新媒体却日日面临淘汰:
一月份会拍照修图写攻略还能混,三月客户就想要视频了,视频还没太学会,又有新玩意儿先出来了,“这回活动我们只要航拍博主”……搞得大家纷纷活在一觉醒来,营生手段已经被淘汰的恐惧中。
阿宗不恐惧。
甭管什么新玩意儿,市面上流不流行,但凡是拍摄工具,阿宗都能想方设法搞到手,整日把玩。
上船时,我们一人得了个全景相机,我见镜头太鱼眼把人拍丑了,马上失去兴趣。
阿宗那个像粘在他手上一样,被他双眼放光捧着赞美:“这视角牛啊!”
阿宗头衔不少——中国最早一批延时摄影师,中国最早一批航拍摄影师。
你认识他之后就会明白,他不是故意的。
只要是能帮助他拍出好照片的,别说是摄影器材了,什么刁钻诡怪的十八般武艺,他都不放过。
比如潜水。
我们在塞班潜水。
当地教练说:“这一带除了蓝洞都安全,蓝洞尽量算了。那儿虽然景观特别,洞口洋流太复杂,好多人游到那儿就被冲走了,死亡率最高。”
不出所料,阿宗只问一句。
他问:“好拍吗?”
教练说:“美极了,天上的光打在水面上,从洞里往上看,简直是一块巨大的天然的深蓝色宝石,妥妥的世界级奇观,大自然的瑰宝!”
阿宗和徒弟谢毛毛检查好潜水服,纵身一跃。
教练跟了一圈回来,赞不绝口:“两个都是好手,都欢迎留下来跟我一起当教练!”
比如登山。
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看见了计划之外的活火山。
阿宗原计划潜水,穿的是拖鞋。
火山不久前才小喷过一次,山下的湖泊还冒着烟兼滚泡泡,脚下的火山灰很烫。
同行的都叫拖鞋阿宗别作死,阿宗望了望心心念念的火山口,背好无人机,耳朵一闭:爬!
阿宗踩着烫坏的拖鞋在活火山顶飞无人机。
我爬不动了,拉着土著导游在半山腰气喘吁吁,想着就搁这儿架相机得了。
阿宗在火山口大声喊我,很兴奋,还是那口襄樊话:
“这儿角度好!”
我对导游说:“见笑了,那是我最不珍惜生命的朋友。”
导游咧开嘴,露出鲜红的牙齿笑了。
“那孩儿虽然鞋没穿合适,但他找来的登山棍,身上背的水源,登山的动作、节奏,储存体力的方法,都堪比专业选手。我更担心你。”
好吧,
就算阿宗不瞎玩,也有处理严峻的能力,
但他那面对生死的态度,实在太不端正了。
阿宗随身携带很多纪录片,如果你看过他那个超大硬盘,也会觉得,他已经收集了全世界所有的好纪录片,并已然如数家珍了。
去世界三大活火山岛国——瓦努阿图之前,阿宗带领我和谢毛毛在房间狂看火山纪录片,一边看一边手舞足蹈讲解,用襄樊话:
“斗(就)是这两个人,专门拍火山纪录片滴(的),他们拍完老地球上所有的著名火山!——看到没有?火山星子蹦出来,蹦到跟前这两个人退都不带退一步,牛——×得很!后来有一回他们拍到火山爆发,没来得及跑,直接被岩浆吞老!那一部片子我也有!”
我说:“好惨啊……”
他说:“惨什么!多牛!”
“…………”
这就是为什么我妈强调,阿宗这种人再好玩,也绝对不能当丈夫。
偏生阿宗拥有最完美的爱情。
05.
阿宗早婚,媳妇叫尔秋。
阿宗怕媳妇。
那时候在船上。
有一天,阿宗一个人坐在餐桌边发呆。
他在起航仪式上上过台,客户特意邀请的著名摄影师,大约不少船客有印象。
他往餐桌一座,不一会儿就来了个妆容精致的妙龄女郎,大大方方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来,支着下巴笑盈盈打招呼。
电光石火间,阿宗像是屁股上长了弹簧,整个人“噌”地弹起来。
还摔了一跤,摔了跤也不停,就那么一崴一崴,急急忙忙走了。
太没礼貌了吧。
女生一个人坐那儿好尴尬。
我赶紧装没看见,绕过去嘲笑阿宗。
我说:“你至于吗?”
阿宗说:“船上这么多人拍照,万一拍到传到秋儿那儿去了,麻烦。”
我说:“这么小概率的事件你都能怕成这样?而且你多大的人了,成年人在餐厅里吃一顿饭,又不是从你房间里出来,从房间里出来还能是聊工作呢,几句话解释清楚的事。”
“麻烦。”
阿宗觉得那也麻烦。
我难得逮到机会损他,绝不放过:“你晓得你刚才多吗?哎哟,没拍下来给大家看简直要成我人生一大遗憾了!”
要面子的阿宗想甩掉我,一路小跑去甲板,边跑边冒襄樊话:
“拍星星拍星星。”
我跟在后面喊:“晚上八点你拍个啥星星!”
阿宗至今住在襄樊。
襄樊节奏慢,成年人聚在一起,习俗是吃晚饭卡五星到九十点钟,然后要么继续奋战到凌晨,要么换个地方唱K喝酒。
尔秋规定阿宗十二点前到家。
阿宗每回出门,不管在哪儿,玩得多嗨,十一点半准时屁股疼,干啥都坐不住,直摸车钥匙。
新来的教育阿宗:“媳妇你要教育她听话,不能叫她骑到你头上,搞习惯了那还得了?大老爷们,还是成功人士,不能搞得没有家庭地位!”
发小们会拦住新来的:“莫为难他,阿宗怕媳妇。”
阿宗怕媳妇,在襄樊这堆发小里尽人皆知。
尽人皆知的还有阿宗的爱情故事。
阿宗刚上高一的时候,学校的街舞社招新,阿宗排队报名,一眼看上排在他后面的尔秋。
阿宗急忙表白,尔秋急忙说No。
尔秋漂亮,成绩年级前三十,还从小弹钢琴。传说中的书呆子女神,连拒绝阿宗的理由都是“我不想影响学习”。
阿宗不知是哪根筋还没发育好,听不懂拒绝,照追不误。
早上给人家送早餐,晚上给人家打开水,一下课就跑去人家教室门口晃。
尔秋一说:“同学,你能不能别这样对我了?”
阿宗就很兴奋,女神跟我说话了!
连忙扑上去回答:“同学,我真的特别喜欢你,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一天接一天。
十六岁阿宗为追尔秋干过的傻事,写出来比家乡那条汉江还长。
听说尔秋报了艺术班学音乐,阿宗连忙变成美术生报同班。
两个人都在街舞社跳breaking,阿宗就进步神速,积极竞选社长。
当上社长之后,主要心思是研究如何给尔秋行便利,给尔秋开小灶。
尔秋不见他,不要他的东西。
他就趁尔秋不在,偷偷把早饭放在她课桌抽屉里,晚饭点跑去偷人家开水瓶,打满水再给放回去。
十六岁的尔秋全年最大的困扰,应该就是如何甩掉这条黏屁虫了。
可惜那个时候没有知乎,尔秋无法集结万千网友的智慧科学有效地甩黏屁虫。
阿宗也无法集结万千网友的智慧科学有效地追女神。
所以整整一年后,阿宗还在锲而不舍地用傻瓜的方式表白。
他跑到江边喝得酩酊大醉,喝醉了就有胆子给尔秋打电话。
他在电话里对着汉江大声喊:“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啊!你为什么永远不给我一次机会呢?”
喊着喊着就号啕大哭。
尔秋大半夜在电话那头听他哭,觉得好可怜啊,追了那么久还追不到,太可怜了,也跟着哭。
哭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挂电话的。
第二天尔秋看到他,胳膊上有伤,想起昨晚,突然心很痛。
阿宗走过来,认真看着她。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别哭,我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问你,你拒绝我之后,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缠你!求你别哭了!”
尔秋还在心疼他的伤呢,听他这么前所未有地严肃,直接心碎了。
这就是两因素情绪理论里典型的错误归因啊!
尔秋把她的同情当爱情了。
这不对!
可惜这时候我也还是中学生,还不能用大学学到的心理学知识,科学有效地帮助尔秋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高一暑假,尔秋就这样误入歧途。
她用收件箱只有三十条容量的诺基亚手机发了一条至今还在的短信。
“我答应你。”
2007年8月26日,5点20分。
这个魔法般闪着光的时刻,这条短信,改变了两个人的一辈子。
很多年后,当阿宗成了神秘的著名职业摄影师,还发了福,整个人圆圆墩墩,表情不多话也不多。
你一定已经想象不到,在2007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夏天,那个瘦瘦的街舞团杀马特,第一次蹦向他的小女朋友的样子。
那笑容,脸上的每一根筋都开花了。
图/阿宗 阿宗自拍,breaking 是阿宗和尔秋相遇的缘分
06.
高二开学。
阿宗搞了个本子,用他那手鸡爪子爬出来一般的字,写恋爱日记。
写得歪歪扭扭,但坚持写,日日写:第一节课尔秋笑了,第二节课老师叫尔秋回答问题了,第三节课阳光洒进教室了,有一缕刚好散在尔秋的头发上,美极了……什么芝麻绿豆大的事都不放过。
还非叫尔秋给他回信。
睡一觉起来,又不准尔秋回信了,不可以影响她学习。
尔秋成绩好,班主任盯得很紧。
为了不让班主任拆散他们,尔秋比任何时刻都用功学习,一边学一边鼓励贪玩阿宗,在一起就要共同进步。
一会儿哄他,考试进步十名,周末就一起逛街买文具;一会儿又说,考进全班前二十,放学就跟他切磋breaking。
高二一年,被迷得晕头转向的阿宗成绩突飞猛进,进步奖品本拿到手软,一度变成优等生。
艺术生的高三是最苦的。
冬天,艺术班“倾巢”搬去武汉,在一所破旧的废弃学校全封闭集训。
尔秋被关了起来。
阿宗跑到外面报小课,每天早出晚归,每次归来必定捧着热腾腾的武汉小吃——豆皮、热干面、麻辣烫,塞到尔秋手里,日日不重样。亮瞎全体其他考生的眼。
可是,被关起来的尔秋没办法知道一件事。
她不知道,贪玩阿宗每天出去上课,除了带小吃之外,还泡网吧打游戏。
高三打游戏,这让画画成绩很好的阿宗因为文化课,被很多好大学关在了门外。
尔秋考得好,阿宗追随她,去了离她不远的三本。
打游戏的后遗症依然在。
阿宗太贪玩,上大学后,游戏打得越发没有节制,还因为游戏语音,认识了女的,跑去跟人家网友见面。
尔秋哭了,哭着说再也不要在一起了。
如果你看过阿宗后来在沼泽上探路,在冰川上爆胎,在雪山顶上挨饿受冻十几天,一律不紧不慢,会觉得阿宗这辈子什么也不怕。
我知道他怕什么,他怕尔秋哭。
尔秋一哭,他的世界就塌了。
二十岁的阿宗什么也不要了,他下跪。
哭着求尔秋回来。
尔秋擦干眼泪,原谅了他。
阿宗再也没有不眠不休地打游戏。
这事过去六七年了。
现在的阿宗,在襄樊买了一套大公寓,超级大,主卧室里的Kingsize(超大号)床、婴儿床和婴儿玩具区加起来,才刚刚占到一半面积。
房间还很多,阿宗有个专门的书房,各种器材摆了一屋子。
所有的屋子,墙上都挂了许多阿宗的作品。
世界屋脊的风光照,环球旅行婚纱照,大小错落有致。品位很好。
可是进门处有半面墙,画风突变,像是穿粉红色裙子的樱木花道乱入《蒙娜丽莎》一样不和谐。
那墙上扎满了红色气球和彩带,还拿大红色充气条在中间弯出一道丑陋的“happy marriage”,特别诡异。
我看不下去,对他说:“你身为一个摄影师,怎么能容忍自己的新房有如此不和谐之画面?”
阿宗在削苹果,一块一块切下来放进碗里。
阿宗说:“我跟我媳妇保证过要弄滴。”
我说:“啥时候?”
“高二,高三,不对,高二,忘见老(忘记了),反正斗那时候。”
苹果削好了,阿宗端起碗,屁颠屁颠跑去找正在喂奶的尔秋。我跟谢毛毛被他扔在客厅里。
现在,尔秋生了个儿子,相机镜头一对着他就笑。
我每回回家乡都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