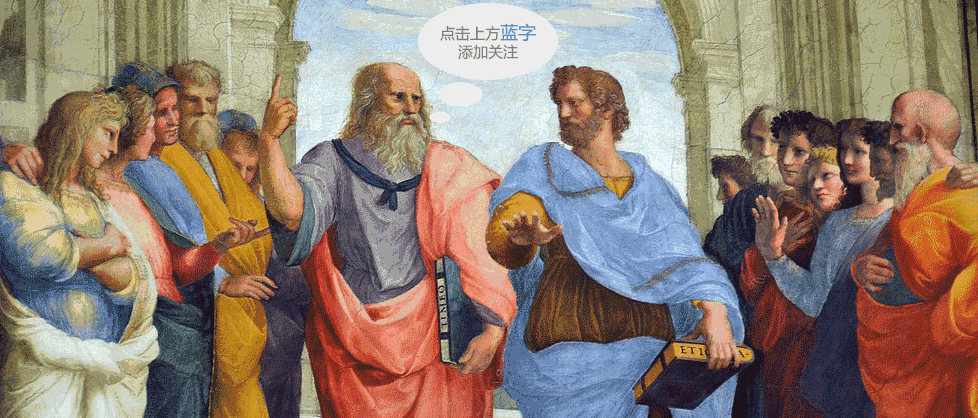
真相就是真理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百年
张旺山,
台湾《思想》杂志第一期
真相就是真理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百年,张旺山,台湾《思想》杂志第一期
1903
年夏,韋伯(
Max Weber
,
1864-1920
)這位以學術爲職業的學者,在進入不惑之年時,一方面由長期的病痛憂鬱中甦醒了過來,發表了延宕多時的一篇棘手的方法學論文的第一個部分
`
,展開了另一階段多產的學術生命;但也在這一年,韋伯正式辭去了海德堡大學的教職
——
用韋伯的太太瑪莉安娜(
Marianne Weber
,
1870-1954
)的話說:正値盛年的韋伯被逐出了他的王國
2
。辭去教職後,韋伯決定與宋巴特(
Werner Sombart
,
1863-1941
)和雅飛(
Edgar Jaffe
,
1866-1921
)接手主編《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以下簡稱《文庫》)
3
。這份刊物,給韋伯的學術生命提供了廣闊的園地
4
。光是
1904
年這一年裡,韋伯不僅爲新系列的《文庫》寫了一篇簡短的
<
編者弁言
>
(
Geleitwort
)、一篇反省刊物的性質與方向並藉此論述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問題的重要文章
<
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
>
(以下簡稱
<
客觀性
>
)、一篇探討普魯士財產權問題的文章,更在
1904
年
11
月在《文庫》中發表了
<
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
>
(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des Kapitalismus
,以下簡稱《新教倫理》)的第一個部分,並在翌年
6
月(美國之行返德後)發表了第二個部分。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學界熱烈的討論:首先是費雪(
H.Karl Fischer
,
1879-1975
)於
1907
年在《文庫》
25
卷中發表評論,韋伯在文末附上了回應
5
;
1908
年費雪在《文庫》
26
卷中又對韋伯的回應做了簡短的答覆,韋伯也再度在文末對該答覆做了一些說明;接著是
1909
年歷史學者拉賀發爾(
Felix Rachfahl
,
1867-1925
) 在《科學、藝術與技術國際週刊》(
Internationale
Wochenschrift fur Wissenschaft
,
Kunst und Technik
)連載長文
<
喀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
>
(
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
),不但批評韋伯的《新教倫理》,還要求韋伯的好友神學家特洛爾奇
(Ernst
Troeltsch,1865-1923)
對韋伯的觀點表態;
1910
年,韋伯在自己的《文庫》第
30
卷中作出了答覆,而特洛爾奇則在該週刊中作出了回應;拉賀發爾意猶未竟,立即又在該週刊中發表
<
再論喀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
>(Nochmals 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
這下子韋伯火大了,同年在自己的《文庫》第
31
卷中發表了一篇
<
針對「資本主義精神」之反批判的結束語》
(Antikritisches
SchluBwort zum “Geist des Kapitalismus"),
主動結束了這場論爭
⑥
。
1920
年
4-5
月間,韋伯完成了《宗教社會學論文集》
(Gesammelte Aufsi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第一卷的定稿與校樣,《新教倫理》的最後定稿就收錄其中作爲整部論文集的第一篇論文。就在韋伯於
6
月
7
日決定將這一卷題獻給妻子之後的一個星期,也就是在
1920
年
6
月
14
日,韋伯就因爲所患的流行性感冒引發深度的肺炎而過世了,享年
56
歲。
由於《新教倫理》有這二個版本,因此在今日談《新教倫理》就首先必須注意《新教倫理》的「版本問題」。雖然韋伯在
1920
年版所加的第一個註腳中強調:他在這個版本中「並未刪除這篇文章中任何一個具有實質重要主張的句子,也未對任何這樣的句子作出新的解釋、使其減弱、或加上實質上有所背離的主張」;因爲他覺得完全沒有這個必要,並相信「論述的進展」
(Fortgang der Darlegung)
終將使得「始終還有所懷疑的人」不得不信服這一點。
(RSI:18)
然而,在經過「批判與反批判」的論爭之後、在韋伯將自己的研究計畫大幅更動之後,韋伯在
1920
年的版本中爲避免已發生或可能會發生的誤解並針對各種批評意見而對
1904/05
版本所作的修改與補充,還是値得我們注意的:這二個版本的對照閱讀、尤其是
1904/05
年版與韋伯的幾篇「反批判」的對照閱讀,對於釐清韋伯的「問題」將有很大的幫助。
《新教倫理》發表到今天,已經整整
100
年了,韋伯辭世也已經有
85
年了。「時間的力量」(
Macht der Zeit
)業已確立了《新教倫理》的「經典」地位。這是無庸置疑的。但任何對《新教倫理》稍有涉獵、對《新教倫理》出版後、乃至韋伯過世後直到今日關於《新教倫理》的種種詮釋與爭議稍有所知的讀者,應該都會感到困惑:爲什麼這篇韋伯發表在自己主編的、一再強調其「學術性」的刊物中並且自認爲是「純歷史性陳述」(
RSI:204
)的論文,卻不僅在其生前、更在其死後,不論在文章的「問題」、對該問題的「探討方式」與獲致的「結論」等方面,都產生爭議、產生如此多的「誤解」甚至「不解」?也許更有趣的一個問題是,韋伯雖然在
1917
年
11
月所發表的著名演講(學術作爲一種職業
>
(
Wissenschaft als Beruf
)中強調:學術的研究無所逃於一種「進步」的過程,任何學術研究的成果都將在
10
,
20
,
50
年內「過時」,並認爲這就是學術研究必須臣服其下的命運、甚至是必須獻身追求的意義
——
任何學術上的「完成」(
Erfullung
)都意味著一些新的「問題」,並且想要被「超越」與過時。然而,不但韋伯在《新教倫理》發表
15
年之後強調
1920
年版對
1904/05
年版中所有具有實質重要性的句子「一句不改」,甚至在《新教倫理》發表了
100
年的今日,我們不但不覺得《新教倫理》已經「被超越」或「過時」了,甚至覺得他所提出的問題正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爲什麼會這樣呢?韋伯在《新教倫理》中問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問題」?他所做的又是什麼樣的「學術的」研究?
韋伯在
1920
年爲《宗教社會學論文集》所寫的總序〈文前說明
>
(
Vorbemerkung
)中說,他置於《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卷首的《新教偷理》和發表於
1906
年的
<
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的精神)
(Die protestantischen Sekten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這二篇舊作,乃是試圖:
就一個重要的個別之點去更接近問題之通常最難以掌握的那個側面:某種經濟形式
(Wirtschaftsform)
的某種「經濟信念」
(“Wirtschaftsgesinnung”):
「倫理」
(“Ethos”)
之受到某些特定的宗教上的信仰内容(制約)的制約性,並且是以現代的經濟倫理
(Wirtschaftsethos)
與禁欲的新教之理性的倫理
(rationale
Ethik)
的關聯爲例子的
(RSI:12)7
。
這句話可以說是韋伯自己對《新教倫理》所要作的研究工作之最後、並且是最簡潔扼要的說明,特別値得我們重視;因此,在這篇短文裡,我想以這段引文爲中心展開論述,試著去回應前面所提到的疑惑與問題,並就教於方家。
首先,這段引文中所說的「問題」,指的是
1920
年韋伯爲整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定調的問題:爲什麼全世界其他的地方無論在科學、藝術、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上,都沒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那些理性化的軌道?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理性主義」是什麼樣的一種理性主義?韋伯想要透過這些「宗教社會學」的著作去認識西方、尤其是現代西方的理性主義的獨特特徵,並說明這種特徵是如何產生的。然而,爲什麼韋伯會想要透過「宗教社會學」的研究
——
而不是像馬克思(
Karl Marx
,
1818-1883
)的歷史唯物論那樣,透過對「經濟生活」的發展的研究
——
去認識並說明西方文化所特有的那種「理性主義」的產生呢?韋伯自然非常清楚,經濟生活對於任何一個文化的發展都具有根本的意義(
fundamentale Bedeutung
),任何這類的說明,都不能忽視經濟條件的重要性。換言之,韋伯是承認西方文化所特有的那種「理性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經濟的發展制約的。關於這一點,自馬克思以來,已有不少的著作做了深入的探討
——
他的好友宋巴特就在
1902
年出版了他的六大卷鉅著《現代資本主義》(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韋伯的太太瑪莉安娜多次提及韋伯常說:「我沒做的,別人會做」。我們大概也可以想見,韋伯會說:「别人做過的,我就不必再做了」。而韋伯會想要做的,自然是韋伯認爲重要、但卻還沒有人做或至少沒做好的。
在韋伯看來,經濟條件對西方所特有的理性主義的產生所具有的制約性(
Bedingtheit
),畢竟只是因果關聯的一個側面;整個因果關聯還有另外一個相反的側面,不能忽視:韋伯所要探討的,就是這個側面。韋伯強調:「經濟的理性主義」的產生,不僅有賴於理性的技術與理性的法律等等外在條件,也有賴於「人之探取某些特定種類的實踐上理性的生活經營(
praktisch- rationale Lebensfuhrung
)的能力與傾向」(
RSI:12
)。換言之,「經濟的理性主義」不僅受到客觀的經濟條件的制約,也受到某種主觀的「能力與傾向」的制約。要「發展出」經濟的理性主義,是需要有特定的「主觀的條件」的。當這種主觀條件受到抑制(當然,這種「抑制」也是一種來自靈魂深處的抑制)時,某種「經濟上理性的生活經營」的發展就會遭遇到頑強的抵抗。而韋伯之所以特別重視「宗教」對這種「理性的生活經營」的影響,乃是因爲他認爲:在過去,「巫術的與宗教的力量」以及「建立在對這些力量的信仰上的種種倫理上的義務想法(
Pflichtvorstellungen
)」,毫無例外都是「生活經營之最重要的形構性元素」
8
。在這種想法下,韋伯將「問題」的這另一個側面以一般的方式描述爲:「某種經濟形式的某種『經濟信念』(『倫理』)之受到某些特定的宗教上的信仰内容(制約)的制約性」。《新教倫理》所要探討的,只是這種一般的制約關係的一個例子:現代資本主義這種「經濟形式」的「精神」(信念、倫理)之受到禁欲的新教的「理性的倫理」(精神)制約的制約性。簡單地說,《新教倫理》所要探討的,乃是宗教與經濟這二個實質的生活領域之間的某種「精神與精神」或「倫理與倫理」之間的制約關係。
事實上,這種制約關係,亦即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與基督新教的信仰內容相關」的想法,並不是韋伯的新發現。問題是,當人們想到這種制約關係時,浮現在心頭的,都只是一些模糊的一般想法,恰似「滿天金條,要抓沒半條」,很難說出個所以然。因此,韋伯認爲這個側面是問題之「通常最難以掌握的」
(
meist am schwierigsten zu fassende
)側面。而韋伯嘗試要做的,就是要去「更接近」(
nāher zu kommen
)這個側面,將心頭浮現的那不清楚的東西「盡可能清楚地表述出來」(
RSI:29
)。用視覺的比喻說,就是要將問題的這個側面「看得更清楚些」。問題是:要怎麼「看」才能「看得更清楚些」呢?「看」得越清楚,意味著能夠越清楚地將所看到的說出來、用語言表述出來。
問題是,韋伯所要「看」的,無論是新教的「倫理」或資本主義的「精神」,都是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而每一個「歷史現象」都具有「無法窮盡的多樣性」(
unausschopfbare Mannigfaltig-keit
),具體地說,無論是新教的「倫理」或資本主義的「精神」,事實上都指涉著在歷史上的無數多的人的腦袋中、以無數多樣的型態與深淺層次存在著的精神性的東西,絕非現成的完整可認識的對象。對於這樣的對象,是不可能依照傅統的定義方式
9
加以定義的。韋伯在《新教倫理》第二章一開頭,就對《新教倫理》標題中的研究對象「資本主義的『精神』」的概念掌握問題,進行了簡略的方法論反省,並借用好友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李凱爾特
(Heinrich Rickert,1863-1936)
的說法,將「資本主義的精神」這樣的對象稱爲一個「歷史性的個體」
(ein historischesIndividuum)
。所謂「歷史性的個體」是一種邏輯意義上的個體,亦即是某種可以作爲言說的對象或陳述的主詞的東西,並且這東西還是以某種方式「存在於」歷史之中的。但是,這並不是說:歷史上眞的有個現成的東西叫做「資本主義的精神」,而是我們
(
研究者
)
就文化意義
(Kulturbedeutung)
的觀點而將歷史實在
(geschichtliche Wirklichkeit)
中的許多關聯
(Zusammenhangen)
在概念上結合成一個整體所形成的複合體
(RSI:30)
。用來標示這種「歷史性個體」的概念,韋伯稱爲「歷史性的概念」
(historischer
Begriff).
這樣的一個概念,由於在內容上涉及的是某種「因其個體性的特徵而富有意義」的現象,因此依其本性就必須逐步地由其個别的、從歷史實在中取得的組成成分加以組合起來。因此韋伯才會說,我們對資本主義的「精神」最後會得到什麼樣的概念上的掌握,只能在整個研究結束時才見眞章。換句話說,對這樣的研究而言,鋪陳研究成果的論述過程是極爲重要的,也因此
——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過的
——
韋伯才會信心滿滿地認爲,他全沒有必要改變
1904/05
年版《新教倫理》的重要實質內容,並相信「論述的進展,終將使得始終還有所懷疑的人,不得不信服這一點。」韋伯甚至明白的說:他將在論述過程中、並作爲《新教倫理》整個論述的一項重要成果加以展示的,就是「我們可以如何最佳地將我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的『精神』表述出來」,並補充說:所謂「最佳地」,是說「對我們在這裡感到興趣的那些觀點而言最適當的(
adaquatesten
)」。但韋伯同時也強調:他在《新教倫理》中所探取的那些觀點,並非我們分析《新教倫理》所要考察的那些歷史現象之「唯一可能的觀點」。只是,不同的考察觀點將會產生以不同的特徵爲「本質性特徵」的結果。這一點適用於對所有歷史現象的考察。因此韋伯認爲:「人們完全並非必然只能夠、或必須將資本主義的『精神』,理解爲那我們覺得是它身上對我們的觀點而言具有本質性的東西」,而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就
存在於『歷史性的概念建構』(
historische Begriffsbildung
)的本質之中」,因爲這種概念建構爲了自己的方法上的目的,不會想要將實在(
Wirklichkeit
)裝進一些抽象的類概念之中,而是要將實在安排進一些具有「總是並且無可避免地特具個體性的色彩(
individuelle Farbung
)之具體的、發生性的關聯中」(
RSI:31
)
10
。
這段方法論的反省,在
1904/05
年版《新教倫理》中就有了。熟悉韋伯的方法論思想的讀者,或許可以看出韋伯講這些話的用意;但對一般讀者而言,這些話實在叫人諱莫如深,不知所云,有必要作些簡單的說明
11
。對韋伯而言,「學術」(
Wissenschaft
)乃是「對實在所做的思想上的安排」(
denkende Ordnung der Wirklichkeit
);「自然科學」研究「自然」,但「文化科學」(
Kulturwissenschaften
,韋伯有時候也稱爲「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在內)則研究「文化實在」(
Kulturwirklichkeit
)。「文化實在」是我們這些「有能力也有意願有意識地對世界採取立場並賦予它一個意義」的「文化人」(
Kulturmenschen
)被置入其中、在其中生活的「實在」,韋伯也稱之爲「生活的實在」或「歷史實在」等等。這樣的一個「實在」,乃是一種李凱爾特所說的「異質性的連續體」:我們固然可以在這一「實在」中區分開各種相對獨立的領域(如:經濟、宗教、藝術、政治等等),但這些領域的現象之間,是會互相影響、甚至互相滲透的。例如,就政治與經濟的關係而言,國家會透過立法等作爲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因而是「與經濟相關的」(
ōkonomisch relevant
)現象;但就「國家的財政經濟」而言,我們統稱之為「國家」的複合體,基本上本身就是某種「經濟的」(
ōkonomisch
)現象;最後,就國家無論在經濟與非經濟關係上的作爲或特徵都或多或少受到經濟動機的影響而言,國家甚至可以說是「受到經濟制約的」(
okonomisch bedingt
)(
WL:162
)。《新教倫理》所要「看」的,就是「與經濟相關的」某些「宗教生活的過程」,看看它們是怎樣影響到經濟生活的。
既然韋伯所要看的東西是某種「異質性的連續體」的一個部分,是一種「歷史的現象」,則要怎麼看才能看得比較清楚些呢?韋伯基本上接受康德的知識論傳統,認爲「實在」不僅在「內涵的量」(
intensive GroBe
)上是無限的,在外延上(
extensiv
)上也是無限的,因而概念是永遠無法完全地掌握住實在的;並且「外延」(或「範圍」)越大的概念,其「內涵」(或(「內容」)也就越小、越空洞。這種情形,對於想要掌握住現象之間的共通性、普遍規律的自然科學,並不會構成問題;但對於想要探討「歷史現象」的文化科學而言,「自然科學式的概念建構」就顯得無用武之地了。因此,韋伯認爲,要探討歷史現象,必須改弦更張,探取「歷史的概念建構」,建構出合乎歷史的認知興趣與知識目的的「歷史性的概念」。由於這樣的概念建構方式,一方面必須取材於歷史中的種種過程,但另一方面卻必須由研究者在「思想的理想純度」上將取自歷史實在的成分組合成一個在思想上一致的整體,這樣的一個整體不能是「類」,只能是一種理論上可能的、理想的「類型」(
Typus
),因此韋伯將這種概念建構的方式稱爲「理想類型式的概念建構」,以這種方式建構出來的概念則稱爲「理想類型式的概念」或簡稱「理想類型」(
Idealtypus
,一般習慣簡稱爲「理想型」)
12
。在韋伯看來,在探討歷史現象時,要「看得清楚些」,便非得透過研究者自行整理、建構出來的「理想型概念」去看不可。
問題是,文化科學的研究者所要看的,既然並非某種現成的東西、更不是某種共通的現象或規律,則我們便可以問:為什麼研究者會想要看那些他要看的東西呢
?
「文化實在」這種「異質性的連續體」是無限複雜、具體、個別而又一體相關聯的連續體,光用肉眼是看不出個所以然的。研究者之所以會想要「看」、想要「看出」什麼東西,最終乃是因為我們有一種知識興趣,想要對我們被置入其中、生活於其中的這個文化實在就其獨特性(
in ihrer Eigenart
)加以理解,亦即:一方面就其今日的型態理解其種種個別現象的文化意義(
Kulturbedeutung
)與關聯,一方面理解其歷史上爲什麼會「如此而非不是如此生成」的種種理由(
WL:170f.
)。換言之,我們自然而然的就會想要認識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的獨特性,並想要知道這個世界是怎樣變成今日這個樣子的。而文化科學之所以爲「文化」科學,正是因爲這些學科都想要就種種個別現象的「文化意義」去認識這些現象。
韋伯在
1904
年的
<
客觀性
>
一文中強調,一個文化現象的型熊之意義以及此一意義的理由,只能透過我們將文化現象關聯到某些「價値觀念」(
Wertideen
)去建立起來。因爲,「文化」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價値概念(
Wertbegriff
)。「經驗實在對我們而言之所以是『文化』,是、並且只是因為我們將它與價値觀念關聯了起來,它包括、並且只包括了實在中的那些透過該關聯而對我們而言變得有意義的組成成分」(
WL:175
)。也是在這個意義下,韋伯將「我們是文化人」這個事實當做是「每一門文化科學之先驗的預設(
transzendentale Voraussetzung
)」(
WL:181
)。總之,文化科學對某一文化現象的探討,不但有共同的知識興趣作爲出發點,不同的研究者也可以由於價値觀念的不同而赋予不同的文化意義,甚至,由於價値觀念的不同,不同的研究者根本就會想要看、並且看到不同的東西。因此韋伯才會認爲,不同的研究者對「資本主義的『精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看法」不一樣,自然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隨著個人或歷史上具有支配性的價値觀念的改變,人們自然會以不同的價値觀點去看歷史,並且看出歷史的不同面貌。這就是歷史的文化科學可以「青春永駐」的理由。
也許有人會擔心,如此一來,這樣的研究還能算是「科學研究」、還能具有「客觀性」嗎?在這個問題裡,糾纏著許多有待釐清的觀念與想法,我們無法在此在細論下去。簡單地說,韋伯認爲,文化科學的研究是不可能擺脫與價値觀念的(理論上的)關聯的,但卻必須避免做出(實踐性的)價値判斷。文化科學的研究無論在主題的選擇、研究對象的形構以及價値觀點的選擇上,必定都是「主觀的」(更精確地說:有「主觀的預設」的);但研究工作的進行卻必須嚴格遵守「價値中立」的要求並服從「思想的規範」,從而使研究所產生的結果具有可以普遍被接受的「客觀性」。這樣的研究固然必定是「片面的」,卻仍舊是「科學的」、「客觀的」研究。更進一步說:價値關聯不僅是無法避免的,甚至是至關緊要的:一個研究者會看什麼、看出什麼,就決定於價値關聯。二個同樣「客觀」、同樣「正確」的文化科學的研究,由於價値關聯的不同,是可以有「高明」(
geistvoll
)與「拙劣」
(geistlos)
的分別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高明的錯誤」比「拙劣的正確」更有價値。在
1904
年的
<
客觀性
>
一文中韋伯說的一段話値得在此引述:
當然:沒有研究者的價值觀念,就不會有「材料選擇」的原則,也不會產生任何對於個體性的實在之有意義的知識,並且,正如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内容的意義的信仰,任何探討個體性實在的知識的研究工作亦將毫無意義一樣,研究者個人的信仰的方向丶在研究者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値的色折射
(Farbenbrechung der Werte),
亦將給研究者的研究工作指引方向。並且,科學的天才。
(der wissenschaftliche Genius)
將他的研究對象與之關聯起來的那些價値,有可能可以決定一整個時代的「觀點」
(“Auffassung”)
、亦即成爲具有決定性的價值:這不僅適用於被認爲是在現象中「有價値」的部分,也適用於現象中被認爲是有意義的或無意義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部分
(WL:182)
。
我們或許可以說,韋伯正是他自己所說的那種「科學的天才」。如此,我們便必須進一步探討:韋伯的「靈魂之鏡」的價値色折射給《新教倫理》的研究工作指引了什麼方向?換言之,我們必須進一步探討本文前面那段引文「就一個重要的個別之點去更接近問題之通常最難以掌握的那個側面」中的那個「重要的個別之點」指的是什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明確地表現在韋伯《新教倫理》的章節結構中。
1904/05
年版《新教倫理》的章節結構是這樣的:
I
問題:
(1)
宗教信仰與社會階層;
(2)
資本主義的「精神」;
(3)
路德的職業概念
(Berufsbegriff,1920
年版改成
“Berufs-konzeption"=
職業構想
)
。研究的課題。
Ⅱ
禁欲的新教的職業觀念
(Berufsidee,1920
年版改成
“Berufs-ethik"=
職業倫理
)
(1)
入世的禁欲之宗教基礎;
(2)
禁欲與資本主義
(1920
年版改成「資本主義的精神」
)
掌握韋伯的困難,始於掌握韋伯的問題之困難。從《新教倫理》的章節結構看起來,韋伯是由對德國新舊教都佔有一定比例人口的邦所做的職業統計所發現的一項現象開始談《新教倫理》的「問題」的,尤其倚重他的一個學生
Martin Offenbacher
於
1901
年發表的關於「巴登邦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經濟處境」的研究成果。這項引起當時天主教會注意的現象是:不僅資本家與企業主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工人中較上層受過教育的階層、尤其是現代企業中那些職務較高、在技術上或商業經營上訓練有素的人員,也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
(RSI:18)
。這個現象固然値得注意,而今日的「社會學」的研究大概也只會對這現象進行實證研究的調查與分析,但對韋伯而言,這卻只是韋伯爲說明《新教倫理》所要探討的問題的「出發點」。事實上韋伯是由對「資本主義的『精神』」進行初步的描述,再由路德的
“Beruf”(
職業
)
構想的影響著手去確定《新教倫理》的「問題」的。韋伯在《新教倫理》第一部分的結尾處說,他想要確定的只是:宗教上的種種影響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資本主義的『精神』」之「質上的塑造」與在全世界的「量上的擴充」,以及我們這個「建立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的文化」的哪些具體的側面是可以追溯到這些影響上的。並且,由於宗教改革這個文化時期的種種「物質基礎」、「社會與政治的組織形式」以及「精神性的內容」等等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的情形是極爲複雜的,因此我們首先只能研究一下:「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與「職業倫理」之間的某些特定的「選擇的親和性」(
Wahlverwandtschaft
),是否、以及在哪些點上是可以爲我們所認識的。韋伯並且希望藉此盡可能的弄清楚,由於這些「選擇的親和性」之故,宗教性的運動會以哪一種方式、在什麼普遍的方向上,對物質性的文化的發展發生影響。韋伯強調,唯有當我們明確地確定了這一點之後,我們才有可能進一步嘗試去評估:在其歷史上的產生過程中,現代的種種「文化內容」(
Kulturinhalte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那些宗教性的動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其他的動機(
RSI:83
)
13
。
由以上的簡短說明可以看出,韋伯在《新教倫理》第一部分的結尾處所提出的「課題」是相當複雜而龐大的。事實上,《新教倫理》所完成的(即《新教倫理》的第二個部分中所完成的),只是這個龐大的「計畫」的一個部分
14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本文前面那段引文「就一個重要的個別之點去更接近問題之通常最難以掌握的那個側面」中的那個「重要的個別之點」,指的就是《新教倫理》的第二個部分的標題所顯示的「禁欲的新教的職業倫理」,亦即該段引文中所說的「禁欲的新教之理性的倫理」。
最後,我們來看看,韋伯在《新教倫理》中透過他所建構的「理想類型」看到了什麼。韋伯在《新教倫理》的結尾處明白的表示,他的論述所要證明的乃是(以下引文在
1904/05
年版與
1920
年版中,文字幾乎完全相同)
:
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並且不只是這精神、而且也是現代文化的構成性組成成分
(konstruktive
Bestandteile)
之一的「以職業觀念爲基礎的理性的生活經營」
(die rationale
Lebensführung auf Grundlage der Berufsidee) ,
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的精神
(Geist der christlichen Askese)
中孕育出來
(geboren)
的」
(RSI:202)
。
這段話清楚的說明了:(
1
)韋伯所要「證明」的,乃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倫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