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王春林
既问苍生,也问鬼神
——关于石一枫长篇小说《心灵外史》
文 | 王春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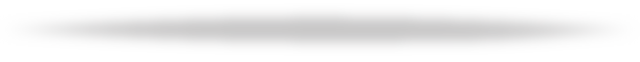
【续】
第三个时间节点,就已经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传销团伙的相关描写了。传销团伙的形成,与所谓市场经济时代到来后物欲的极度喧嚣,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石一枫之所以要在这一部分拿出不小的篇幅来穿插叙述李无耻(我们千万不能忽视作家在李无耻这一人物命名过程中所透露出的强烈反讽意味)的故事,正是为大姨妈的加入传销团伙做一恰切的铺垫式注脚。实际上,也正是在李无耻的故事中,作家对身为知识分子的“我”和李无耻们进行了颇为深入的自我剖析:“我从懵懂的傻球变成了孤僻少年,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因为欲望勃勃而愤世嫉俗的家伙。此时此刻,假如我和李无耻这种人身上也发生一次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或者是按照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思路,被照妖镜照出了原形,那么我们所最终变化而成的,应该不是甲虫狐狸琵琶兔子之类,而是一群在簋街夜市上深受欢迎的小龙虾。这东西学名克氏原螯虾,杂食,生存能力极强,擅长攫取,能够适应极其肮脏、阴暗的环境,并且总能在腐烂的泥土中发现养分。它们的形状外强中干,性情又非常残暴,在食物匮乏的时候会果断地同类相食。”
依照此种论调,则“我”与李无耻,大姨妈与其他的传销人员之间所构成的,正是这样一种非常令人恐怖的“同类相食”关系。关键之处还在于,既然如同“我”和李无耻这样的所谓精英知识分子都会被刺激出强烈的物欲,都会在金钱拜物教的主导之下,最终被金钱大潮席卷而去,那如同大姨妈此类普通民众对于传销团伙的积极参与,自然也就是可以理解的顺理成章之事。
虫虫宝传销团伙事件的相关描写中,最值得注意处,是大姨妈面对专门前来搭救自己的“我”时那样一种无以自控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真诚地相信传销是一种很好的致富手段:“她首先祝贺我加入了‘虫虫宝’,并论述,这相当于获得了‘人生腾飞的机会’……其次询问我的‘业绩’怎么样,有没有冲上‘黄金级代理’,如果我感到吃力,她可以对我‘扶上马,送一程’。”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企图凭借一己蛮力将大姨妈带离传销团伙时,大姨妈才会做拼死的反抗。但在另一方面,大姨妈根本没有想到,“我”为了搭救她差一点就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可要不是因为我,你就不会受那茬儿罪。我没想到他们会那样对你……杨麦,你别恨我,我把你拽回去真是想让你挣钱……”实际上,也正是依赖于大姨妈那种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劲头,“我”的性命方才侥幸存活下来。由此即不难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不管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信仰,一旦这种所谓的精神信仰与事实上被大姨妈视为心头肉的“我”发生冲突,那大姨妈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本能地站在“我”这一边。
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到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再到新世纪以来的传销活动,大姨妈的所谓精神信仰不断地发生着迁移。由此而生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她为什么要如此不断地盲信呢?对于这一点,大姨妈自己曾经对“我”做出过诚恳的自我剖析与自我反省:“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不光是‘虫虫宝’,还有以前练气功的师父,我一直不知道他们那些人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可再多想一层,真的假的好像又都并不重要,不能妨碍我让自己去相信他们……每当听到那种特别有劲儿的话,尤其当他们说是为了我好,为了我身边的人好,为了所有人好,我就特别激动。我觉得只要信了他们,就能摆脱世上的一切苦——生不出孩子、被男人揍、觉得自己没用……他们那些人对我说,信了吧,信了吧,这其实并不足以说服我,但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也在说,信了吧,信了吧,信了就越过越好。一到这时候,我就顶不住了,只想着把自己抛出去算了。”猛然间听了大姨妈的这一番话,“我瞠目结舌,似乎听懂了她的意思,似乎又没懂。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大姨妈正在向我破译她的思维密码,由此可以解释‘她为什么是她’。”
更进一步地,大姨妈强调说:“说到底还是赖我,但我也没办法。杨麦,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我的脑子是满的,但心是空的,我必须得相信什么东西才能把心填满。你说人跟人都一样,但为什么别人可以什么都不信,我却不能?我觉得心一空就会疼,就会孤单和害怕,我好像一分一秒也活不下去了,好像所有的日子全都白活了,好像自己压根儿就不配活着……我就想,信什么都无所谓了,关键得是先找个东西信了,别让心一直空着……”我们所读到的以上这些话语,都已经经过了叙述者的加工与修饰。不难设想,现实生活中的大姨妈,其语言表达恐怕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条理这样流利。但不管怎么说都无法否定的一点却是,这些话语的含义的确是大姨妈意志的真实表达。关键处显然在于,身为普通民众的大姨妈,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自己内心世界的空,为什么总是希望能够有某种外物成为自己的精神依托。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就必须联系中国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结构了。一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别的许多民族相比较,一贯崇尚实用心理的中国人,本来就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或者干脆说也就是精神信仰。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革命所造成的强烈社会震荡,原来具有代宗教或者代精神信仰意义的所谓儒道释也都渐次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样一来,对于如同大姨妈这样的普通民众来说,其内心世界长期以来实际上一直无所依凭。也因此,面对着诸如革命、气功热、传销之类具有极大蛊惑性的事物的时候,他们才会以飞蛾扑火的架势不管不顾地直扑上去。究其根本,由于缺失了现代理性过滤的必要环节,这就很是有了一些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意思。正因为如此,我们方才会无可奈何地断言其为盲信。
事实上,也正是面对着大姨妈这样一个处于不断盲信状态之中的个案,身为知识分子的“我”不由自主地陷入到了关于国人精神信仰问题的沉思之中:“然而也怪了,越是深入研究,我就越受困于新的迷惑。正如李无耻所言,神棍们的招摇撞骗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产业和色情业,和形形色色的‘腐败经济’一样,虽然半遮半掩但却确凿存在,并且有着清晰的利益链条,不知多少人指着它吃饭呢……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政府不是在建国初期就基本扫除了文盲,并卓有成效地改造了广大人民的世界观吗?出于各方面的需要,国家还批量制造了我父母那种‘有思想有文化的新人’。西方历经几百年才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而这个过程在我们这儿只用短短几十年就完成了,这不管怎么说都是伟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却目睹着身边的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莫名其妙的荒唐玩意儿所蒙蔽:打鸡血、红茶菌、气功与特异功能、一嘴鸟语的占星师、东北口音的仁波切……古往今来的怪力乱神在这片土地上大开宴席,每个敢于信口开河的江湖术士都能分一杯羹。哪怕是在中关村和学院路这些‘高素质人士聚集地区’,有关部门也不得不四处张贴‘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宣传标语……不免让人怀疑,难道‘不问鬼神问苍生’只是一小撮儿中国人一意孤行的高蹈信念,我们民族骨子里却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吗?或者说,假如启蒙精神是一束光芒的话,那么其形态大致类似于孤零零的探照灯,仅仅扫过之处被照亮了一瞬间,而茫茫旷野之上却是万古如长夜的混沌与寂灭?如果是这样,那可真是以有涯求无涯,他妈的殆矣。”
请原谅我无论如何都得把这段议论性的叙事话语全部抄录下来,因为这一段叙事话语严重地牵涉到了事关国人精神信仰缺失或者说总是处于一种盲信状态的根本问题。在这里,借助于叙述者“我”的口吻,石一枫实际上不无尖锐地揭示出了国人精神世界存在着的两大根本缺陷。其一,固然是精神信仰的严重缺失。唯其因为缺失精神信仰,所以也才会出现无数如同大姨妈这样精神信仰处于不断迁移状态的盲信者。其二,精神信仰的缺失,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所谓的启蒙理性无涉,但认真地想一想,就可以发现,在很多时候,牢固坚定的精神信仰,实际上往往都是建立在强大的启蒙理性基础之上的。你很难想象,一个缺失了启蒙理性精神烛照的民族,能够确立某种牢固而坚定的精神信仰。
这就不能不说到《心灵外史》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也即大姨妈最后信教的相关描写了。从事传销活动被拘留到派出所后,因为大姨妈拒绝写此后不再从事传销活动的保证书,所以被判处劳动教养一年半。但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被废止,大姨妈自然也就被提前释放了:“一个星期之后,大姨妈会从劳改农场转回县看守所,接受完警方的重新登记和再教育,她将获得就地释放;届时,我们这些亲属可以过去接她。”然而,等到“我”兴冲冲地从北京赶到河南某县的时候,大姨妈却意外地消失了影踪。“我”以及警察都未曾料到,大姨妈其实是跟着传教的刘有光上了其实已经差不多人迹罕至了的矿山。
按照警察的说法,刘有光曾经因为传教而被判处劳教。刘有光本来只是一位普通农民,他名字的来历,取的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意思。因为在县里别处的采石场干活儿眼睛被炸瞎的缘故,最终一个人落得孤苦伶仃的刘有光,就义无反顾地信了主。因为与政府对抗执意要在矿区传教的缘故,刘有光最终被关进了劳改农场。实际上,大姨妈自己的信主过程,也如同刘有光一样带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对此,大姨妈也曾经做出过形象的描述:“直到后来跟他一起进了劳改农场,这才听他背了几次经。背也不能全背,里面有警察看着。什么‘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还有什么‘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常随不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我也只能记下不多的几句……但那时候我没信,我觉得不信主就这么收拾我,那么这主也不是什么善主儿。然而刘有光不一样,他也不讲什么道理,光背经,一背,那些似懂非懂的话就钻到我的脑子里去了……我懵了,觉得我不是我了,直想哭直想笑。我觉得自己的面前展开了一条金光大道,只要走上去,那么犯过的罪都能抹掉,吃过的苦都会消失。我还觉得以前信别的东西都信错了,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就是为了绕到这条大道上来。有一个声音又在我耳朵边上响起来,它说,信了吧,信了吧,信了就一切都会好了……”
其实,正如大姨妈所真切描述的,在最后这次到底应不应该信主的问题上,她的内心世界里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自我斗争。一方面,她清楚地知道“我”正在赶来接她的路上,但在另一方面,冥冥中一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拖拽着她朝着“信主”的方向走去:“我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大姨妈听到这话时茫然的神色,我甚至还能体会到她心里涌动的激情——那一刻,她手握自由,有机会让身体回到我们的世界,但灵魂早已滑向了另一个世界。一条实在的门槛位于她的脚下,一条虚拟的分界线铺展在她的眼前。终于,她选择了其中一个方向,决然地迈了过去。”是的,正如你已经知道的,大姨妈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刘有光,选择了信主。
说实在话,当我读到走投无路的大姨妈最后信主的这部分描写时,内心里竟然一下子溢出了满满的感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除了跟随刘有光信主以获得内心世界的安宁之外,这个时候的大姨妈事实上的确已经无路可走。我甚至设想,西方的基督教所谓的上帝,或者耶稣,在当初最早传教的时候,很可能就是石一枫小说里所描写的刘有光这副模样。人都说,真正的宗教诞生于苦难,吾于今信焉。说到底,正因为人世间存在着非人力所能彻底克服的苦难,所以才会有宗教信仰或者说精神信仰的生成,也才会有刘有光。“上帝说有了光,于是就有了光”,有了刘有光,也才会有大姨妈对他的坚定追随。
假如说石一枫的《心灵外史》真实再现了女主人公大姨妈一生不无曲折的精神信仰史,那么,此前的全部信仰其实都属于盲信,而只有最后一次她的信主,她对于上帝的皈依,方才称得上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精神信仰。然而,从作家石一枫的角度来说,大姨妈最后到底信了什么或者干脆就不再信什么,实际上也都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在于石一枫《心灵外史》的写作本身,在于作家以如此一部具有心灵冲击力的优秀长篇小说关注、思考并表现了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本文标题中的所谓“也问鬼神”,说透了也就是这个意思。
但在结束本文的全部探讨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展开必要的分析,那就是叙述者“我”的设定问题。其中,尤其不能忽略的,是临近结尾处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但我最终打给的却是彭佳亿,那个和我说陌生不陌生,说熟悉不熟悉的心理医生。电话通了,彭佳亿的声音传了出来,我对她说:‘现在我需要倾诉。’”“然后不等彭佳亿说话,我就一气向下地讲了起来。我复述了大姨妈的历史,从她为了革命检举我母亲,到她在我们那个家庭行将崩溃时赶来照顾我,从她带我去西安接受‘发功’,到她下岗、离婚、加入传销,从我去找她结果被塞进了锅炉,到她自愿呆在看守所里又被改判劳教……我告诉彭佳亿,我的大姨妈特别会做烩面,面里有鹌鹑蛋、海带丝和卤羊肉。我还说大姨妈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但至今孤身一人。我也说了大姨妈为什么会是现在的大姨妈——她特别想相信什么东西,于是就信了。”直到读完这些叙事话语之后,我们方才会恍然大悟,却原来,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小说文本本身,也只不过是“我”对彭佳亿关于大姨妈这个人的一整个倾诉过程而已。
但问题到这里却并没有结束,无论如何不容忽视的,还有小说最后的“附录”部分。这一部分,是警察与“我”之间的对话。警察说:“知道你为什么在派出所吗?你在山上昏倒了,埋在雪里,差点儿冻死,幸亏有个看守所的管教警察把你背了下来。”事实上,这些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警察所叙事实与“我”记忆中的事实,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分歧。按照警察的叙述:“离你昏倒的地方不远,在山区的一个护林站里发生了一次集体死亡案件。死者共七人,其中就有王春娥,还有一个跟王春娥同天释放的盲人叫刘有光。其他五人也是附近的村民,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骨骼疾病。死因是煤气中毒,经过现场勘察,发现炉子的烟道被人为堵上了,所以初步判断为自杀。从事发现场附近的脚印推断,你是唯一一个去过现场的人,也是唯一一个从现场活着离开的人。”而在“我”的记忆中:“我是上了山,但见到的都是活人,都能喘气儿能吃面条还能背圣经。我大姨妈还向我讲述了刘有光的事儿,说他是瞎了眼睛后才开始传教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亲眼见,我听真真儿。”针对“我”的一再辩驳,警察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刚才查看过你的手机,昨天夜里,你跟北京的精神科医生通过电话,另外,我们还在你的背包里发现了大量精神类药物。现在我们怀疑你没有说谎,而是出现了幻觉……这也许是受到强烈刺激所致吧。”
正如你已经感觉到的,警察给出的这个判断,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明确知道,“我”的确罹患有精神疾病,不仅曾经去看过精神科医生,而且还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这样一来,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我”对于精神科医生彭佳亿的倾诉,究竟是真实的,抑或还是虚妄的?这就必然涉及到了整个小说文本的叙事真实与否的问题。
在我的理解中,石一枫的如此一种艺术处理方式,或许是他一种富有艺术智慧的障眼法。由他的这种障眼法,笔者自然而然地联系到了鲁迅先生,联想到了鲁迅的名篇《狂人日记》。《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中,直接指认白话文本的叙述者“我”是一名迫害狂患者,通篇日记不过是他发病时的疯言疯语。鲁迅借助于如此一种“佯疯”的形式,尖锐犀利地戳穿了中国社会的“吃人”本质。某种意义上,作家石一枫借助于精神病患者“我”的幻觉,所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部长篇小说《心灵外史》,也可以被看作是类同于《狂人日记》一样的小说文本。就此而言,作家石一枫,在通过这一文本“既问苍生,也问鬼神”的同时,也在向鲁迅先生致以遥遥的真切敬意。
注释:
①石一枫《关于两篇小说的想法》,载《文艺报》2016年3月25日。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017年5月29日下午16时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是为农历端午节前一日
2017-3《收获》
2017-2《收获》
2017-1《收获》
2016全年8本《收获》,特惠
2017《收获》长篇专号(春卷)
《收获》微信公号
微信号 : harvest1957
地址:上海巨鹿路67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