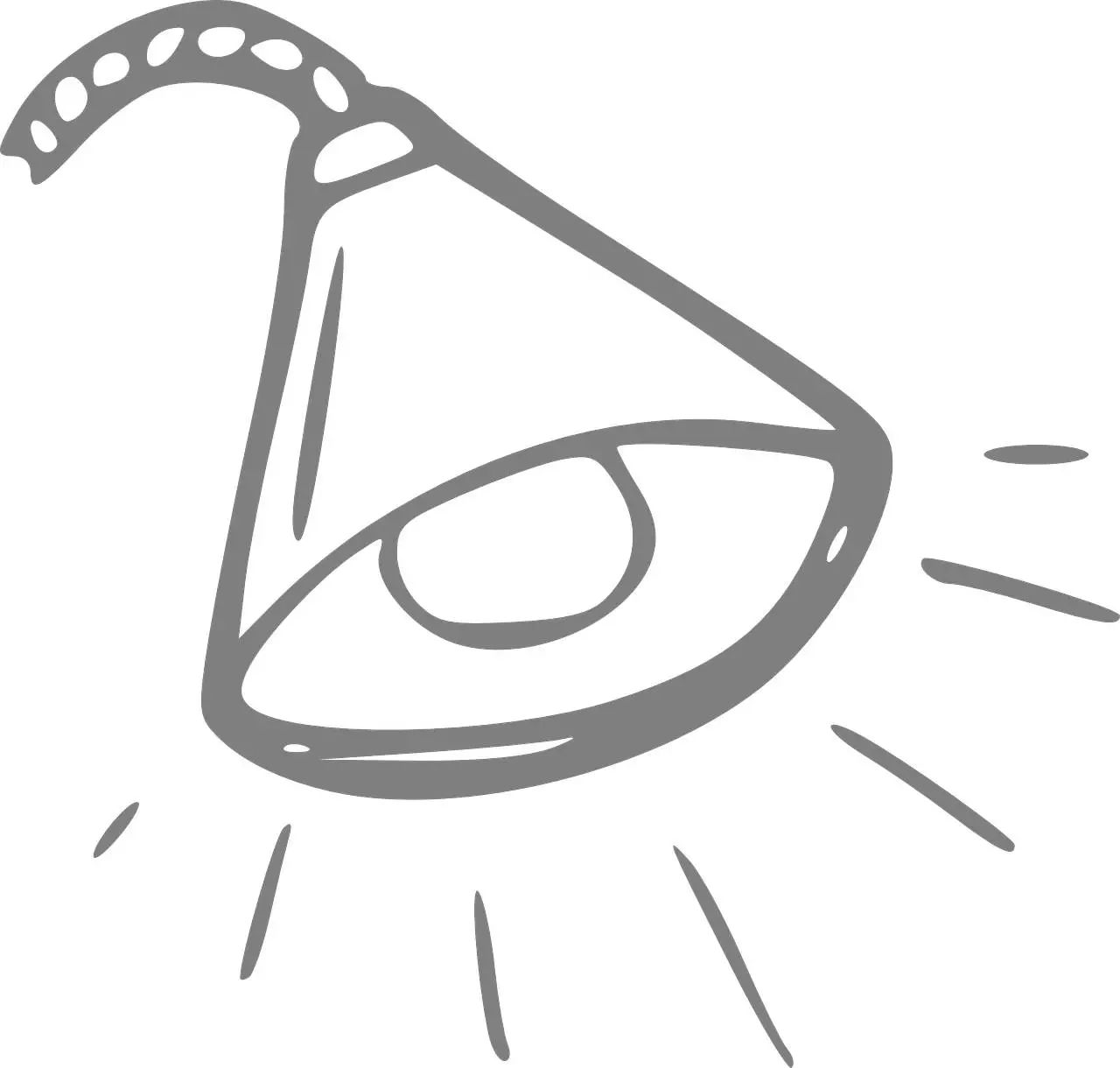屋外的雪飘飘扬扬,天地间一片昏暗。北风一阵阵呼啸着,把即将落地的雪花再次卷到天上,风裹着树枝、杂物不断拍在门上、窗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像是有无数人在窥探。
屋里虽暖和,但马家老爷子觉得心神不宁,他冲婢女英儿使个眼色,让她去检查下门窗,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没关严。英儿赶忙去了。
不到一盅茶的功夫,靠近院墙的西屋里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像是英儿的声音。屋里打着盹、算着账、做着活计的人们都一个激灵,马上有几个反应快的男丁跑了过去。
西屋是间客房,平时没有人住,不过英儿每天都打扫得很干净,新装的窗玻璃,日日擦得里外通透。此时,英儿正倒在这屋的地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户外面,一只手指着那个方向,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
半天之后,英儿才磕磕巴巴地说:“鬼!怨鬼……”
就在那扇干净得像没有一样的玻璃外面,英儿看到了一张脸,一张满脸都是血的脸,贴在窗玻璃上,定定地往里看。到人们听到叫声赶过来时,那张脸如同烟雾一样,瞬间消失在昏暗的雪夜中。
听了英儿的讲述,几个胆大的男人提上灯,结伙出去围着房子里里外外转了一大圈,却什么也没找到,雪地上连个脚印都没有,大家松了口气,纷纷议论说准是英儿精神恍惚,看错了什么东西。
踏着积雪,一行人穿过院子走回堂屋,落在最后的是桂六,住在马家的伙计。他明确地记得自己是最后一个的,但突然感到后面有人拍他的肩膀,他不耐烦地边伸手推开那只手边回头看,刚想说话,声音却憋在了喉咙,紧接着,他发出了一声惨叫,之后像逃命一样扔掉手中的灯笼,放开腿脚往屋里狂奔,前面几个人都没能拉住他。
刚跑进屋里,他就要闩门,被后来的人一把推开了。大家吵吵嚷嚷地骂了一阵,才听他惊恐地说他刚才看到了鬼,一个满脸是血的鬼,还伸出一只干瘦的爪子抓他的肩膀。大家面面相觑,心里渐渐生出了一些恐惧。
这一整晚,大家都没敢睡,不管男女老幼,都挤在堂屋待了整晚,不过后面的半夜,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夜晚过去,天放了晴,风也住了,太阳出来,阳光很和煦,让人感觉昨晚的一切都是错觉。
吃早饭的时候,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提起昨晚的事情。吃完饭,该去店里照应的就去店里了,该做家事的继续做家事,马老爷子背着手,围着宅院转了几个圈,然后一言不发回了屋。
马家宅院闹鬼的事还是传了出去,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说出去的。不过调查这事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没过几天,鬼又闹了一次,再后来的某些天,马家常常发现本该在这屋的东西,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那屋,或是本来藏得好好的东西,不仅被翻了出来,还被挂在当院的树上。
马老爷子现在走在街上,背后常有人指指戳戳地低声议论。他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也只能装听不见。
“当初真不如把这房子卖了!”有时候远离了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之后,马老爷子忍不住恨恨地这么想。自己家这个宅院,离淮镇最热闹的南北大街一箭之遥,背靠镇上唯一的一座小山坡,交通方便,又很安静,是人人觊觎的好位置。这些年来,常常有人主动拜访,求转让此宅,都被马老爷子喊个吓死人的高价,从而放弃了念头。
“这房也不是不能卖,只要价钱合适。”马老爷子常这么说。不过他认为合适的价钱,总离一般人能接受的相差太远。
“去年来的那个老儒生,开的价还真是可以商量呢。”马老爷子眯起眼睛,想起了去年的一个买主。可惜那人后来再没来过,如果他再来,就按他那个价钱卖给他算了。
可惜马老爷子心仪的买主并没有来,鬼还在继续闹着。马老爷子请过几个道士法师,做了几次法,然而一点作用没有,宅院里还是一天到晚地出怪事。桂六已经不在这里住了,他借口要看店,搬到了南北大街上马家的布料铺里。英儿跟老妈子吴氏住到了一间房,一到晚上形影不离,两人从来没那么好过。马家大少爷在家里话不多,不过他已经开始让人打听有什么合适的房子了。
马家想换房的消息也流传出去了,在淮镇这个小地方,没有什么秘密能保守住。陆陆续续来了几个打听消息的,问问马家现在的房子卖不卖,卖个什么价钱。马老爷子已经没以前那样的底气了,他照着以前人们提出过的价钱报了个价,没想到时移世易,曾经加钱也愿意的人,听了这个价也还是摇了摇头。
马老爷子心烦意乱。这房子是自己年轻时辛苦挣下的产业,自己为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就算比这个价钱高一倍,自己以前都不乐意接,现在竟然连这个价也卖不出去了。
第二年快入冬的时候,马大少爷买下了镇西头的一套老房子,收拾了一下,全家都搬了过去。新家在镇的边缘,去趟南北大街要走半天,大少爷现在去照顾铺子,必须要天不亮就出门。不过这地方倒是干净,再也没有奇怪的动静和吓人的东西了。全家只有马老爷子不高兴搬过来,其他所有人虽没明说,但都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马家旧宅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只好先赁给了一个外乡来此做生意的粮食商人,他只有自己和两个个伙计,那么多房间住不过来,把好几间屋子都搞成了仓库。马老爷子心里直咬牙,嫌他糟蹋房子,但有个人住着看守着,总比荒着强,没人气的房子容易塌。
但这个马老爷子不满意的租客也没在这里待多久,春节还没到,粮食商人死活要退租,再便宜的价钱也不干了。住了不到三个月,撞见了好几回鬼,吓得商人和俩伙计魂飞魄散,连淮镇都不想再待下去。
马家宅院荒了,没人敢再打它的主意。除了马老爷子偶尔白天来串串,除了镇上一些半大孩子到这里练胆量,这里平日连过路人都不再有,凡是知道它的故事的,都绕着它走。而淮镇这么个小地方,没有几个人不知道这宅院的故事了。
春天化冻,夏天落雨,眼看着老宅的墙就出现了颓唐的痕迹,马老爷子看在眼里,心都在滴血。他有时候趁哪个伙计空闲的时候,强拉着人家陪他来修修补补。伙计们没人敢忤逆他,但很快就都勤快得一点空闲没有了。
那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来了个买主,正是两年前来过的老儒生,他不是镇上人,原本住在献县。在马老爷子此时看来,哪怕白送给他,这房子也算所托得人了,至少这个人,像是个能好好照顾这房子的人。谈好价钱,马老爷子心里有些不忍,他忐忑地问老儒生听到过什么传说没有,老儒生笑了:“子不语怪力乱神。”马老爷子放下一颗心——至少怪不到自己隐瞒事实了。
老儒生一家秋后就搬了进来,没办什么仪式,也没张灯结彩。一家人都挺庄重有礼,男的沉稳,女的安静,让淮镇的人看着油然升起羡慕与自卑。也是奇怪,自打老儒生住进来,不知道鬼是消停了,还是老儒生根本不怕,反正再没听到这院子里有什么大呼小叫,不管多爱打探人家家长里短的人,也探不出什么口风。街坊邻居私下里议论,琢磨着一定是这老儒生年高德劭,把阴气压住了,鬼不敢出来。这议论传开,全镇的人对老儒生一家的敬重都多了几分。
又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夜,淮镇的人们都躲在暖暖和和的屋子里猫冬。呜呜的风声中,一些人隐隐听到了吵闹声、惨叫声、甚至打斗声,一阵一阵随着风声飘来飘去,但仔细张起耳朵,又不太确定那到底是人声还是风声。
一夜过去,太阳出来,早起的人们路过南北大街东边的小路,看到碎石路上有些暗红色的痕迹,像是泼溅在路上一样。疑惑的人们循迹而去,看到马家老宅,也就是老儒生一家现在住的那所宅院,门户大开。进到院里,一幕极为吓人的场景出现在众人面前——从院里到屋里,一具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身上都遍布刀伤,血溅得满院都是。老儒生全家,从老到小,从尊到卑,无论男女,没留一个活口。
跑得快的人马上去告官了,捕快来得及时,顺着碎石路上的血迹一路追去,在去镇不远,通往献县的路上找到了凶手,他自己也在搏斗中受了伤,因失血过多,晕倒在途中。多亏捕快发现得及时,再晚一会儿,恐怕也该冻死了。
审案那天像节日一样,县衙门口人山人海。献县虽是个繁华地方,但一向还算安定,这样灭门杀人案还是第一次出,附近的闲人们都想来看看热闹。
犯人没等用刑,就老老实实地招了——事是我干的,但我是被逼的,我只是想要回我该得的钱而已。
一场大戏就这样在献县人眼前揭开,淮镇人第一次知道,人生可以是这么长的一个局,而自己都是局中的一个角色。老儒生几年前就看中了马家这套房子,想买下作为终老之地,遗憾的是马老爷子的开价太高。老儒生回到家里思前想后,找到了献县泼皮姜三儿,给他谋划了一场漫长的表演。两年多来,姜三儿带着两个兄弟,风里雨里辛苦地在马家装鬼,逼走了马家,又逼走了租户,直干到老儒生得到了远低于预期的价格,把房子买下来为止。本来说好,老儒生最初出价和最终拿下的价格之差,都是姜三儿兄弟的辛苦钱。没想到房子拿到,老儒生翻脸不认人,姜三儿找他论理,他却说无凭无据,谁说过给这么多钱?就算去官府告,也没人会相信鬼是他装的。姜三儿吃了大亏,没法向兄弟交待,存了心要跟老儒生摊牌。那一夜他和老儒生吵到翻脸,他决定动粗。本来他也没想走到这步,但老儒生的家人冲上来要赶他出去,情急之下热血上头,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命案审结,房子又判回给了马家。但这房这下是真成了鬼屋,死了这么多人的房子,谁还敢住?马老爷子每每看到这房就伤心,好好奋斗一辈子,不招谁不惹谁,怎么就这么让人给算计了呢!
原故事来自《阅微草堂笔记》
淮镇在献县东五十五里,即金史所谓槐家镇也。有马氏者,家忽见变异。夜中或抛掷瓦石,或鬼声呜呜,或无人处突火出。嬲岁余不止,祷禳亦无验,乃买宅迁居。有赁居者嬲如故,不久也他徙。以是无人敢再问。有老儒不信其事,以贱贾得之,卜日迁居,竟寂然无他,颇谓其德能胜妖。既而有猾盗登门与诟争,始知宅之变异,皆老儒贿盗夜为之,非真魅也。先姚安公曰:魅亦不过变幻耳。老儒之变幻如是,即谓之真魅可矣
上一期:
转世以后,你还会记得我吗?
翻新怪谈——剜心
二十万慰安妇的命运
消失的民国“贵族”大学
你用火锅拯救冬天,你却不了解它
二战时纳粹德国的异族军团(一)
陈子昂:老子有钱任性! | 我唐日常(六)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我们读史不为装逼
严肃八卦才是目的
you态度的原创历史平台
欢迎你成为其中一员
关注微信公众号:时拾史事(historytalking)
投稿:[email protected]
读者群号 535858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