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华健
(蒋立冬 绘)
米华健(James Millward)先生现为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埃德蒙·沃尔什外交服务学院(Edmund A.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历史学教授。1983年,他获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学士学位,1993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另外,他也供职于亚洲研究协会与中央欧亚研究协会理事会,并于2001年担任中央欧亚研究协会主席。
他的研究专长为内陆欧亚大陆史及清代新疆史,被认为是美国“新清史”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代表作为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 1864(中译本为《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Eurasian Crossroad: A History of Xinjiang,并于近期出版了《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译林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我们的访谈,就从这本书开始。
米华健说,他始终坚持“大历史”(Big History)的观念,尝试从整个世界的框架出发理解中亚与丝绸之路——关于“丝绸之路”的定义,他的观点与一般的看法并不一致。在此次访谈中,他也特意回应了有关“新清史”的争议。他说,他现在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于文化史尤其是音乐史,而他所一直努力做的工作,就是理解和发掘游牧民族在历史上的意义与价值,并与更多的人分享。
采访︱郑诗亮
您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一本《丝绸之路》,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
米华健:我本来不是专门做“丝绸之路”研究的,前几年我看到牛津出版社的“牛津通识丛书”(Very Short Introductions)没有丝绸之路方面的书,觉得是个机会,就跟这个系列的编辑提到,我可以写一本,编辑同意了。之所以选择“丝绸之路”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知道出版社和编辑肯定对“丝绸之路”更感兴趣,如果我提议写一本“内亚史”或者 “中亚简史”之类的书,他们大概会表示拒绝。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本身有市场方面的考虑。读者更喜欢这个题目,不管是去博物馆看展览,还是选择旅行社、饭店,“丝绸之路”显然更有魅力。音乐也是这样,马友友就出了“丝绸之路”专辑。

《丝绸之路》
您曾经在综合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丝绸之路”的定义:“‘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更包括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您能谈谈为什么下这样一个定义吗?
米华健:前面谈到我向出版社提了一个建议。那么,出版社接受之后,下一步就是怎么写的问题了。牛津的编辑给我说,这本书不是Wikipedia式的小论文,而是更加个人化的Essay,要对读者更加友好。当然,相关的书我都读了一遍,一些最新出版的书都挺好的,比如耶鲁大学的Valerie Hansen(韩森)写的《丝绸之路新史》。以前关于丝绸之路的书,都写得太笼统了,而且几乎每一本书都会写到那几个故事:张骞出使西域、玄奘印度取经……这种写法对我来说太无聊了,我不想重复。所以,我就开始思考,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或者,丝绸之路不是什么。最后,我就想到了你提出的这个定义。现在美国的年轻人说到某某事情,会用一句口头禅:“Is it a thing?No, it is not a thing. ”套用这个说法,我们可以说:丝绸之路不是一条路,也不仅仅跟丝绸有关(Silk Road is not a Road,nor is only about Silk)——用“丝绸之路”来概括这段历史,显然是不够完整的。那么,“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于是我就想到了这样一个定义。而且,我不是根据时间的变迁来写的,而是分为好几个题目来写的。
世界史(Global History)或者大历史(Big History)里面的很多角度,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David Christian的几篇论文对我产生了影响。他以前写了不少有关中亚史的论文,也包括丝绸之路在内。他的视野特别开阔,尤其关注自己所研究的区域与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这对我很有启发。
还有,自从二十年前我在乔治城大学任教以来,一直在教中亚史和世界史。我的专业是清史。在美国学术界以前有一种观点:搞了欧洲史可以教欧洲史,搞了美国史可以教自己的研究领域十年时间左右的美国史,搞了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的,那就什么都可以教,亚洲、非洲、南美洲……到了乔治城之后,我的职位是inter-societal history,我刚去的时候,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其他人好像也不太清楚。所以,我只能一面做研究,一面教书,一面自己摸索,后来,我明白了,所谓inter-societal history,指的是跨越各个国家的边境、各种学科的框架,交叉的、综合性的研究。所以,《丝绸之路》这本书,是把二十多年的教学研究经验——尤其是中亚史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然后再写出来的。
我们知道,您的研究专长是清代新疆史,但是您对蒙古帝国也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对内亚游牧社会各个时期的历史做全面的研究,然后写一部新的内亚史呢?
米华健: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但还没有具体的计划。最近也出版了一些很不错的中亚通史,例如Peter Golden的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Christopher Beckwith的Empires of the Silk Road,还有Frederick Starr的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如果我打算写的话,还是要看读者是谁,写给本科生看,篇幅就不能太长。我现在还在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做学术编辑,编了一套Silk Roads,主要是跨学科的全球史研究,也有具体的区域研究,但并不直接涉及丝绸之路研究。我的写作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来是希望吸引更多的读者,尤其是非专业的读者,二来是推广世界史的理念,也就是大历史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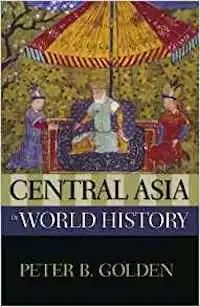
Peter Golden的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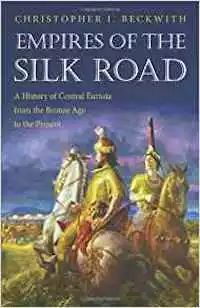
Christopher Beckwith的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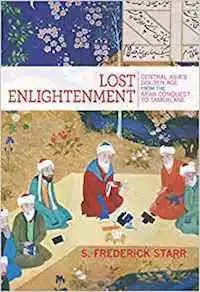
Frederick Starr的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您的《嘉峪关外》(Beyond the Pass)已经出版了中文译本,这对我们了解清代、清代的新疆乃至内亚有很大帮助。中国史学界对边疆民族的问题似乎关注还不够。能否谈谈您对中国的边疆民族研究的看法?
米华健:我不能说我自己读了很多中国学者关于边疆民族史的最新著作,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弱点。其实,对游牧民族在世界史或中国史当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还是有很多学者予以关注的。1990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在人大清史所进修,跟那边的老师讨论过相关问题,关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我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我的圈子里面,这样的学者是很多的,比如“文革”当中去内蒙下乡的学者就很多,经常去边疆考察的学者也很多。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史的美国学者,我不管来过中国多少次,依然是把中国作为一个“他者”来研究,如果我研究的是中国的边疆民族史,那就是“他者”的“他者”了。事实上,在中国并不如此,中国学者把边疆民族史当作自身的历史,并不会把那些游牧民族看作他者。很多中国的少数民族学者也是做这一行的,刚刚在复旦开的这个学术会议,就有各个国家的学者,中国、美国、日本、外蒙,还有各个民族的,汉族、蒙古族、藏族,用的是各种各样的语言。这表示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元化了,不断有新的观点加入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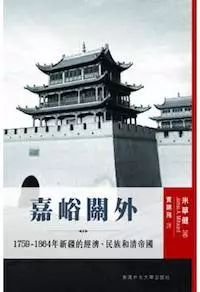
《嘉峪关外》
作为内亚研究者,您的关注领域非常广泛,涉及许多专门的技术领域,如生物学,又如医学和军事技术。这在您的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您是怎么做到的?
米华健:写这样的书,当然需要利用二手研究,而且需要快速地消化、吸收这些成果,提炼出其中的精华。这种做法,跟自己坐冷板凳、看档案当然是不一样的,后者是基于具体的实证材料的一点一滴的积累,而前者则是要基于一个理论视角,然后才能使得材料为我所用。当然,对我来说,这种写法可能还是太冒失了,因为很容易犯错——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外,不管我的阅读量有多大,我都是一个外行。
此外,这种写法,也跟我的世界史教学经验有关。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亚利桑那大学教中国史。我的妻子当时在华盛顿做记者,为了和她团聚,我不得不转而关注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这样才能在华盛顿谋得一份教职。我也喜欢弹吉他和曼陀林,最近还认识了一个特别擅长爵士乐的小伙子,靠音乐他也赚不了什么钱,只能到处找不同乐队演出。我跟他聊到这方面的话题,他说了句“You have to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这句话很难译成中文,其实意思就是你的胆子要大,这样才能挺得过去,就像马戏团演员走钢丝一样,你要一直不断地往前走,很快你就习惯了。
还有一点,我之所以选择研究清朝的新疆史,可能因为我个人的趣味就是对边缘地区更为关注——我喜欢站在边疆,从外向内看。在我开始研究新疆的时候,西方并没有多少学者关注这一领域。这还是我的性格使然,就是喜欢离开喧嚣的人群,关注边缘的地区——在这样的领域,我可以一个人做我喜欢的研究。
说到您喜欢的研究,您本人现在的学术兴趣是什么?
米华健:我现在的学术兴趣是中亚文化史,主要关注弦乐器怎么从原产地扩散到整个欧亚大陆,在这一方面,游牧民族扮演着发明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角色,这就需要把考古、音乐尤其是民族音乐和艺术史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苏联在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考古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了利用这些成果,这几年我一直坐在本科生的教室里面,跟着他们一起学习俄语。
您肯定清楚,现在中国学界非常关注美国的“新清史”,有批评的,也有赞扬的。作为“新清史”学派的重要成员,您怎么看“新清史”呢?从学术方面,您觉得“新清史”有什么贡献和局限呢?
米华健:中国有关新清史的讨论我看了一些,不能说全部看过,但是主要的讨论都有了解,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欧立德,都有激烈的批评。在这方面,我有几点意见。
首先,“新清史”这个词跟“丝绸之路”有点像,其实是不够完整、全面的,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事实。在美国亚洲研究会的一次年会上,从一个研究生做的报告里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我当时很惊讶,原来已经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学派、一种思潮来研究,虽然名称叫“新清史”,但我知道,既然由年轻人提出这个概念,就说明不新了,我已经是上一代的人了!
在我看来,除了边疆、民族、帝国性这些议题,许多用英文写作的、关注清史的汉学家的研究成果,都没有被“新清史”包括在内,这是很遗憾的,比如,性别史、环境史方面的很多研究,又比如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那本突破性的著作《大分流》——这本书当然是“新”的,也关注清史,而且有着广阔的全球视野。对这些学者来说,“新清史”这个提法是不公平的。
其次,我知道,很多人在不断暗示,甚至直接明说,“新清史”是分裂中国的学术阴谋,想要搞垮中国。这也是不对的。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但这的确是个误会。我们之所以进行被称作“新清史”的研究,目标其实是调整、修正包括费正清在内的那一代历史学家的学术话语(discourse),比如朝贡制度,比如汉化,又比如中国中心论。原来美国的本科生学的中国史,全是这套东西——他们可能连鸦片战争都不知道,但他们却知道朝贡,知道外国大使出访北京,要向中国的皇帝磕头。现在的美国新闻提到中国崛起,还会用到“朝贡”这种概念和“磕头”这类词汇。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举个例子来说,我在研究十八世纪新疆的哈萨克人与蒙古人、满人之间的牲畜-丝绸及棉布贸易的时候,发现与费正清所说的不一样。在费正清的历史叙事当中,当时中国与外界的物资交流都是朝贡性质的,没有商业往来,这显然是不对的。比如,曾有大臣向乾隆皇帝建议将哈萨克人集中到北京,遭到了乾隆皇帝的否定,理由就是这并非朝贡。随着档案的开放以及学术交流的增多,类似这样的发现只会越来越多。新清史所针对的,也主要是汉学领域的这类陈旧历史叙事。
事实上,在研究清朝新疆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清朝对新疆、西藏、东北这些边疆地区的经营与管理,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以新疆为例,清朝在征服新疆以后,差不多一百年左右当地没有出现大的叛乱,虽然有跨越边境的几次干涉,但是没有本地人的大规模起义。不单是中国史,哪怕是整个世界史,这在任何一个帝国的管辖下都是罕见的。正因如此,清朝作为一个帝国如何管理边疆的土地与族群,就成了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所以,与其说我的研究是在抨击、批评中国,倒不如说是从正面肯定了清朝对边疆的统治。
最后,我们这一代出生并成长于上世纪中叶的美国历史学者,都早已习惯从学术上批判美国。要知道,我们都经历过美国的民权运动,对我们来说,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对过往的总结和解释,通过它来反思、批评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关注原住民问题和人权问题。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会去研究边疆民族,我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感兴趣”。实际上,这份兴趣,潜意识里也是受到民权运动对少数族群的关注的影响。对我来说,我批评美国政府,不是为了搞垮美国政府,我只是想通过历史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削弱美国政府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对美国是这样,对中国,也是这样。
很多学者非常关注欧亚大陆的环境变迁。而您在《丝绸之路》这本书中第一章所讨论的,恰恰也是“环境与帝国”。您如何评价这方面的历史研究?
米华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研究课题——其实也不完全是新的。十九世纪就有地理学者和探险家关注到,中亚的环境、气候与游牧民族入侵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一方面有了更好的科技手段、更多的数据资料,另一方面,中亚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都促使我们关注环境方面的研究。当下我们面临一个欧亚大陆历史研究上的突破,就是把考古学、古生物学、气候研究和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可以刷新我们的历史认识。
有趣的是,您还建议读者去读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能谈谈这样的文艺作品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米华健:卡尔维诺的小说其实是一个循环,表面上写的是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关于不同城市的对话,事实上,你会发现,在小说的结尾,马可波罗说的每一座城市,都是威尼斯。这也让我想到,不管我走到哪里,研究什么,哪怕我关注的是“他者”,但永远离不开自我这个主体。客观只是历史学者的理想,而你的自我永远都存在于你的研究之中。这不是什么坏事,你的激情,你的文采,都由于你的自我才得以呈现。
最后要提一个宏观的问题,传统历史学所关注的,历来是欧亚大陆的两端,也就是欧洲和东亚,而夹在这两端之间的内亚史,似乎处在从属的、修饰的和边缘的地位。那么,您认为内亚史如何有助于我们认识整个欧亚大陆人类的历史?
米华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历史学界有一个倾向:找回“被遗忘的人群”,这个人群可以是工人、农民、黑奴、妇女、原住民,可以是欧美国家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群,还可以是社会底层民众。事实上,边疆游牧民族也是被遗忘、被忽略甚至被歧视的人群。但对我来说,光是这样尝试着从历史当中“拯救”边疆游牧民族,还不足以形成意义,更重要的是,游牧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连接东西南北欧亚大陆的重要角色。他们不单单是运输队,也有自己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诉求,尤其是大的游牧帝国,比如蒙古和突厥帝国。这对世界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土耳其盘
(1500-1525年,波士顿博物馆藏)

中国青花瓷盘(明永乐,1403-1424年),上图的土耳其盘是这个青花瓷盘的仿制品
我在《丝绸之路》这本书当中,也举了青花瓷作为例子。其实,不能说青花瓷完全是“中国”的产品。它的青蓝色来自于钴,而钴原本是由蒙古帝国从伊朗大量地运入中国内地的。青花瓷在当时的中国其实并不算最高档的瓷器,但元朝统治者喜欢,从而在西域的伊斯兰国家也引发了需求。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游牧民族的喜好和传播,现在全世界的民众才会把青花瓷当作中国瓷器的象征。所以,游牧民族在世界史当中扮演的角色,还不仅仅是“被遗忘的人群”这么简单,他们起过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作用和意义发掘出来。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