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学堂(来源:羊城晚报)
当然,所谓“新教育场域”的概念虽然有其整体的意涵,但也因教育层级、地域和世代等诸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具体内涵的差异,需要分别略加讨论。
首先,不同教育层级的差别。政学的张力在不同层次的学校表现出来的强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对大学来说,这种张力的强度最大。一方面,大学作为担负着学术创造使命的教育场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其问道为学常常形成较强的传统;另一方面,大学生的社会使命意识比中学生更强,对政治的敏感度也更高,介入政治的资源更广,从事政治的能力也更强。因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学数量还很少的情况下,一所大学里往往既有较强的学术风气,也可能同时有较高的政治参与度。而中学和师范学校则因为各自面临的校园环境的差异,容易在向学与革命上形成一边倒的趋势。比如,同样是二十年代江西省最著名的中学,南昌一中与南昌二中就有着显著的差异:前者有着更浓厚的学术风气,而后者则因为与国民党人士的渊源成为江西早期共产主义革命的基地学校之一。又如,在省立中学与师范学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省立中学常常是通向大学的台阶,因此对学生的学业有着更严格的要求;而师范学校则因为生源多来自贫寒之家的优秀学子,毕业出路大多是回乡当小学教师,他们既对个人能力有优越感,又易生不平感,因此更易走上改造旧社会的革命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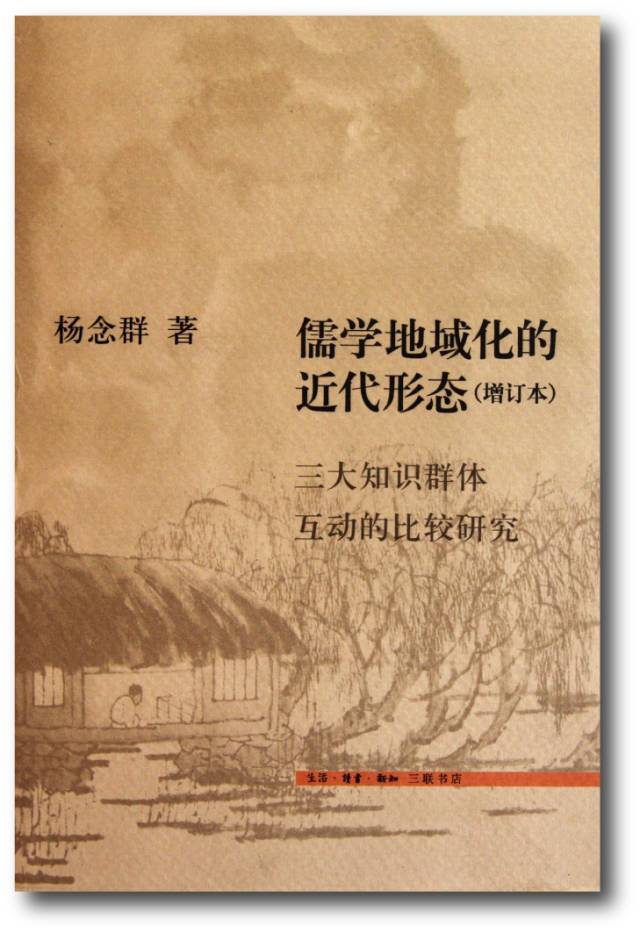
其次,不同地域的差别。就中国晚近士绅群体的分布来说,有三大区域的士绅是最为重要的:湖湘、江浙和岭南(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湖湘知识群体是晚清儒学地域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晚清地方军事化的重要助力。湖南既是晚清绅权扩张最为强盛的地方之一,又是产生诸多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政治、军事人物之重镇。在传统科举考试中,湖南远非称得上文风鼎盛之区。但在从科场场域到后科场场域的嬗变中,湖南民风中的蛮勇与新学堂环境中酝酿出的反体制冲动结合在一起,使其近代涌现的政治军事人物在全国高居榜首。这也使我们对湖南清末民初教育场域的个案研究在全国颇具典型性。而在对五四运动学生代的研究中,则需要考虑到另一种典型性。美国学者叶文心在研究杭州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根源时曾指出,以往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北京,但新文化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其实从“五四”开始就存在诸多分支流派。五四运动在杭州,代表了与北京的运动所不同的另一种讯息,即不是来自通都大邑对外开放的口岸的求变,而是来自中国内地乡土社会的求变(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传播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上海和北京位居全国的中心,广东、湖南、湖北、山东等位居区域的中心,江西等位居革命思想传播和组织发展较为迟缓的第三类地区。以往对早期中共组织的研究多集中在前两类地区。而对江西这样的第三类地区的关注,可以使我们较好地把握五四运动学生代在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时从中心扩散到边缘的发展脉络。
叶文心《乡下人的旅行:文化、空间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
再次,不同世代的差别。所谓“世代”(generation)更多是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代。也就是说,“世代”指的是一个特定社会结构中因个体占据了相似位置而构型成的具体的社会群体,故此,某代人的社会构型可以迁延上百年不变,而另一代人则可能整代处于被遮蔽状态,其中的关节便在于社会的变迁程度(《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一八九五年前后活跃着的是传统社会最后的两代士绅:此时已进入士绅上层队伍的一代;以及一八九五年仍处在士绅下层地位的一代。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一年,第一代新式学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代人被通称为“辛亥革命一代”。紧随“辛亥革命一代”的是“五四运动一代”。严格来说,五四运动一代又可分为师生两代,其中五四老师一代与辛亥革命一代在相当程度上是交叉的。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后是五四运动学生代投入政治的短暂高峰时期,随即学生运动即陷入了消沉的时期。其后新学生与政治及革命的关系已经揭开所谓“后五四时期”的新篇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