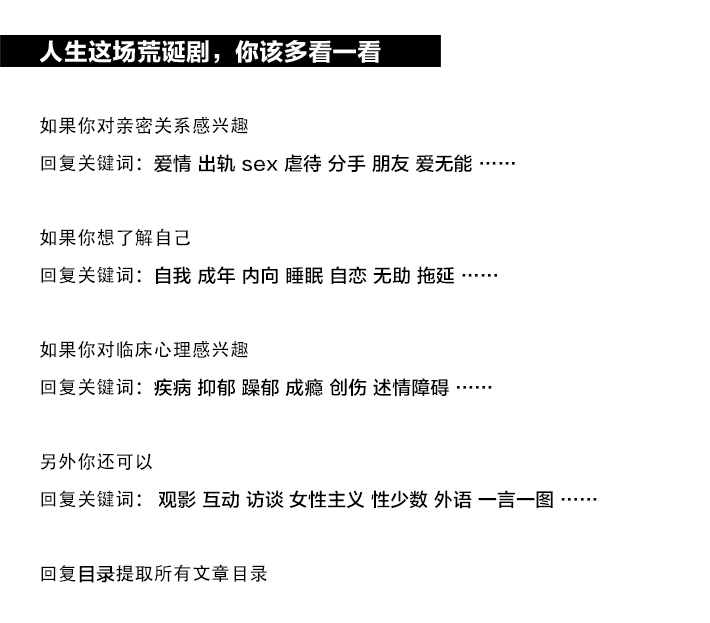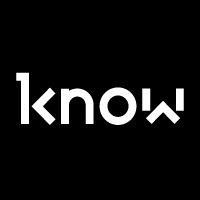在生活中,我们总是被教导要多一些“正能量”,少一些消极负面的情绪。我们总是称赞那些脸上挂着笑容、无论何时都充满希望的人。当一个人遇到挫折的时候,Ta总是被劝说“乐观点”。
但“乐观”真的是绝对的好吗?它究竟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称赞一个人总是很乐观,有时又会说陷入了盲目乐观?今天来谈谈“乐观”这个话题~

乐观是什么
乐观(optimism)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的optimum(意为“最好的”),它是一种精神态度,反映出的是拥有一种“期待未来会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的信念。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最先在哲学层面被提出。如果一个人认为,宇宙对于人类的目标和渴望来说,在整体上是舒适友好的,那么就会被认为是乐观主义的;而如果认为宇宙对于人类和文明的繁荣发展来说是冷漠和敌对的,就会被认为是悲观主义的。
随着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乐观/悲观的划分和自由意志有着重要的关联。17世纪的笛卡尔通过理性建立起了乐观主义的基础,他相信自由意志,认为科学能够使世俗世界免于恐惧、匮乏和疾病,人类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叔本华则是著名的悲观主义者,他是一个宿命论者和决定论者,认为一切事情都按照其严格的必然性而发生,我们所感觉到的自由意志仍然是处于表象世界的活动(Chang, 2001)。
而在现代心理学层面上,乐观和悲观被认为是“伞状的概念”,可以在不同的层面被解释(Chang, 2001)。
1. 乐观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气质类型而存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说一个人是乐观或悲观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气质性的乐观/悲观,它指的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期待最好的结果会发生。气质性的乐观是很难改变的,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气质倾向于乐观还是悲观,回复【乐观】可以做“人生取向测试”。
2. 乐观也可能是解释风格上的,它主要被认为是在对已有的事件进行解释,特别是在对负面事件进行解释时,倾向于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个层面的乐观被认为是可以改变或习得的。
3. 根据动机理论,乐观和悲观都可以是一种动机取向,即一种驱动人们的行为、影响人们对未来的准备的策略性方式,后文会有详细说明。作为动机取向的乐观是最容易改变或习得的。
在动机取向上,Norem(2001)提出了两种具体的悲观与乐观的策略,即防御性悲观与策略性乐观。读过我们关于悲观的文章的同学可能还记得“防御性悲观”,说的是在事件发生前将期待降到比较低的水平,想象出最坏的可能的情境,从而做好充足的准备,在坏的情境真的发生时也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策略性乐观”则指的是,充满自信,期待事情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要为对可能的负面结果的想象而烦恼。Norem认为,这两种策略应该被结合起来使用,既要充分考虑有可能的情况和做好准备,又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上(Norem, 2001)。
近年来的研究倾向于认为,人不是只能被乐观/悲观的二分法所划分的,一个人不会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也不会是绝对的乐观主义者。而且,在不同的方面,或者对待不同事物和情境时,同一个人都可能会有着不同的态度,比如有的人可能在社交上是乐观的,认为自己有能力交到很多朋友;但在学业或工作上是悲观的,总是很难相信自己会获得好的机会;同时,人的看法也是会变化的,比如在刚结婚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婚姻很乐观,认为以后不会离婚;但结婚几年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对婚姻的乐观度大大降低(Chang, 2001)。

影响一个人乐观程度的3个因素
1. 基因
英国研究表明,名为5-HTTLPR的基因对于一个人是否乐观来说非常重要,在它的三种变体中,如果拥有一种较长等位基因,会使人对于负面信息的抵御能力更强,另两种则会使人容易产生消极情绪(Fox, 2009)。
2. 人生发展阶段
在一个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乐观程度不同。针对72个国家、50万人的调查统计显示,整体来说,一个人面对负面事件时,对自己的处理能力的自信心和幸福感,在毕生发展中会呈U形曲线变化:从15-20岁开始不断下滑,在41-50岁时最低,然后再逐渐升高,到60岁以后乐观程度达到最高,并显著高于15-20岁时。不过,这里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最不乐观的平均年龄是38.6岁,男性则是53岁(Blanchflower & Oswald, 2008)。
3. 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影响
临床心理学家Chang认为,一个人的乐观与悲观程度或多或少地受到其所在的文化环境及被文化所塑造的价值观的影响。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显示,一个国家的GDP与人们的乐观程度大致成反比:GDP越高的国家,人们整体上更不乐观,比如,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人民的乐观程度,就显著低于肯尼亚、尼日利亚、孟加拉国等国家人民的乐观程度(Keller, 2015)。
然而,这里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就观察到,美国人对于“一个人的完全性有着生机勃勃的信念,他们都将社会视作永远在进步的主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用“美国梦”来形容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即便是在大萧条、经济危机之后,人们的乐观似乎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减退。研究者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和欧洲不同的是,“美国梦”强调通过个人努力能够获得成功(Keller, 2015)。
另一个趋势是,在东亚国家(中国、日本、韩国等),人们的乐观程度显著地低于美国,甚至显著低于乐观程度本来就不高的欧洲。而在美国人内部,亚裔族群也会比白人表现出显著的更加悲观。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更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而东方文化则更强调人际关系和互相依赖(Keller, 2015)。
除此之外,人们的乐观程度还会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马丁·塞利格曼发现,有宗教信仰的地区整体上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地区的人们更乐观 (Sethi & Seligman, 1993)。
不过,乐观一定是好的吗?
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总会将乐观视作一个绝对正面的词汇,它甚至被看作一切令我们苦恼的事情的通用解决办法。而悲观则是消极、负面的,甚至被视为是精神疾病甚至是抑郁的表现。已经有大量研究针对乐观带来的好处,比如,乐观会与一个人的幸福感呈正相关;乐观会减少焦虑和压力,甚至直接与身体健康水平相关,意味着更高的免疫力和更低的心脏病风险(Boehm, 2012)。
然而,Oettingen(2015)的研究发现,对未来的乐观幻想对你的健康的确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这种乐观是不现实的,它也会产生负面的结果。

* 一种名为“乐观偏见”的认知偏差
心理学研究中提到一种名为“乐观偏见(optimism bias)”的认知偏差。这个过程是被我们的记忆系统工作的方式所影响的:神经科学研究证明,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记忆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带有偏见的。
由海马体等区域掌管的记忆系统,其本身功能的设定不单单是帮助我们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在于使我们能够通过经验的累积来预测未来,在遇到同样的事情时可以有所准备。因此,当我们的记忆系统工作时,并不会完美地重现过去的片断,而是会进行加工,漏掉一些曾经发生的事,强化另一些细节(Sharot, 2011)。
无论是否主动、自觉,我们对记忆的加工过程总是会偏向乐观。比如,一个人本身觉得自己患癌症的几率是50%,但被告知患癌症的平均几率是30%,那么Ta的左额下回(负责接收正面消息的部位)会出现明显的反应,会倾向于迅速接受这个信息,在以后,Ta便会大幅度地修正自己的观点,比如转而认为自己患癌症的几率是35%;但如果一个人本身就认为自己患癌症的几率是10%,那么被告知平均几率是30%的时候,Ta的右额下回(负责接收正面消息的部位)的反应则会迟钝得多,在下一次做判断时可能只会做轻微的修正,认为自己患癌症的几率是11%。一个人越乐观,右额下回就越迟钝,越容易忽略负面的信息(Sharot, 2011)。
这种大脑的运作机制使我们对未来的预期会好过实际情况,从而出现“优越幻觉”(superiority illusion)。乐观偏见在对正面和负面事件的预测上都会出现,比如,人们会对经历正面事件的可能性估计过高,比如会认为自己的孩子要比别家更聪明,自己买彩票的中奖几率更高。在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中,93%的人认为他们的驾驶技术超过平均水平,大多数人甚至愿意为此投下赌注(Sharot, 2011)。
但“乐观偏见”更容易出现在对负面事件的预期上,比如,绝大多数人都会预测自己不会离婚,不会遭遇突发事故,大多数烟民都认为自己比起其他人来更不容易患上肺癌。他们总是会认为,那些统计数据和自己的关系很小(Weinstein & Klein, 1996; Sharot, 2011)。
陷入不现实的乐观,可能会导致一系列负面的结果。
1. 不现实的乐观会降低一个人的表现水平。这也很容易想象:当你相信一切都会更好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懈怠。研究发现,当一个人的“气质性乐观”和“不现实的乐观”得分水平都很高的时候,运动表现会出现显著下降;但如果“气质性乐观”得分很高,“不现实的乐观”得分很低,运动表现反而会提高(Chang, 2001)。总体趋势上是一个积极的人,但没有太高的乐观偏见的人,表现最好。
2. 过分乐观还会使人无法看清眼前的形势,从而做出错误的选择。比如,认为自己能够同时完成很多项工作,最后却无法按时做完;以为自己很喜欢并且适合进入一个职业,结果却发现在这个职业里,有太多与自己的期待、能力不匹配之处。
3. 乐观偏误还会使我们陷入“我们会越来越快乐”的幻觉中,但实际上,这种幻觉是不存在的,因为事实上,对每个人来说,快乐都会变得越来越难。我们会受到“享乐适应”(hedonic adaptation)的影响,这种效应最早是在彩票中奖者的身上发现的,即曾经能够让你非常快乐的事,在你达到目标、感受到快乐后,过了一段时间,同样的事情就不再能够刺激到你。比如,当你第一次在工作中涨薪2000元钱时的快乐,可能远远高于在工作五年后挣到10万元时的感受(Dahl, 2016)。
不过呢,仅仅在有些时候,盲目乐观也是有帮助的——在状况完全不受你控制的时候。比如,当你已经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仅仅是在等待一场考试的分数时,持有更乐观的心态则会减轻压力。此时即便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会是一种转移注意力、从焦虑中暂时逃离的好方法(Puniewska, 2014)。

什么是“正确的乐观方法”?
如果想要摆脱不现实的乐观,成为一个有建设性的乐观者,首先,你需要是一个问题解决者。有建设性的乐观者在处理挑战的时候,会先倾向于使用问题聚焦的处理策略;其次,只有在问题无法被解决的时候,才会倾向于情绪聚焦的处理策略,比如运用幽默、或者对情境进行积极的重构(Scheier, 1994)。
经过了20年的动机研究后,Oettingen(2015)提出了一个乐观者在实现目标时可以依据的过程,称为WOOP——愿望(wish),结果(outcome),障碍(obstacle),计划(plan)。这个过程是这样发生的:先找到你的愿望,想象出这个愿望有可能带来的最好的结果,精确地找到和描述其中最关键的障碍,想象它发生会怎么样,然后制定出可以战胜这些障碍的计划。
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心理对照”(mental contrasting)。“心理对照”指的是,当你拥有一个愿望时,先花几分钟时间,来正向地幻想和憧憬这个愿望成真;然后再转换角度,花更多的时间来考虑现实的因素,要实现这个愿望所要面临的障碍,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在这里,列出的挑战和障碍越具体越好。如果目标是可能被实现的,这种思维方法能够激励我们。在一项关于健康饮食和运动的研究中,Gabriele Oettingen把被试者分成两组,其中实验组被带领进行“心理对照”,四个月后,该组成员与没有受到干预的对照组相比,每周的运动时长是对照组的两倍,并且吃更多的蔬菜(Oettingen, 2015)。
而当愿望不切实际时,也让我们更容易在评估后选择放弃,转而去实现其他的、更合理的抱负。比如,大学毕业的你幻想成为一个护士,你会认为这个工作是多么美好,因为你喜欢医学,而且和病人沟通、照顾他们会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然后,你再想到护士的工作时间非常长,而且会使人精疲力尽,而自己非常不喜欢熬夜和加班,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更适合朝九晚五,这样,你的目标就会从“成为一名护士”变成“在医学行业内,找一份能够有足够闲暇时间的工作”。
在完成心理对照后,第二步策略则是“执行意图”(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也就是将发现的障碍整合到你所期待的未来当中,然后制定能够帮助你战胜或者绕过这些障碍的计划(Gollwitzer, 1999),也被称为“如果-那么”行为计划。它会具体到当每一个特定的情境发生时如何表现。这个计划会帮助你真正地完成目标。
研究乐观偏见的Tali Sharot在2012年的TED演讲中说到,我们一方面被自己的能力和现实的可能性所限制;另一方面,又很难摆脱自己“乐观”的认知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做的是,不让自己成为不切实际的乐观者,同时保持内心充满希望的状态:“悲观的企鹅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飞翔,那肯定永远也飞不起来,我们必须有能力想象与现实不同的未来,相信我们的想象能够实现,才能真正取得进展。但是,如果你是一只极为乐观的企鹅,盲目地直接跳下悬崖,那么可能会发现自己摔得很惨。而如果,你是一只相信自己能飞的乐观的企鹅,又给自己背上了一个降落伞,以防事情的发展不像你想象中那么顺利,你就能够像雄鹰一样在天空中翱翔,尽管你不过是只企鹅。”
我们对现在传播很多的“正能量”,也应该抱有这种谨慎接受的态度。正能量不能鼓吹教你忘记自己是一只企鹅的事实。所有的正能量都要在准确评估自己和现实的情况下,才能对你有帮助。一味做梦是没有好处的。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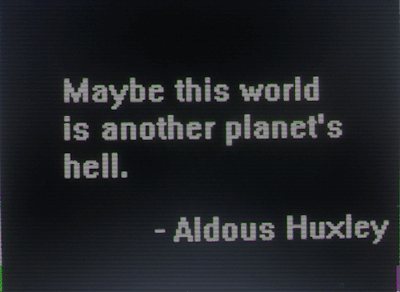
References:
Blanchflower, D. G., & Oswald, A. J.(2008). 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66(8), 1733-1749.
Boehm,J. K., & Kubzansky, L. D. (2012). The heart's content: the association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cardiovascular heal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8(4), 655.
Chang, E. C. (2001). Optimism &pessimism: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American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ahl, M., (2016). You’re Not Supposed to BeHappy All the Time. Science of Us.
Gollwitzer, P. M. (1999). Implementationintentions: strong effects of simple plans. Americanpsychologist, 54(7), 493.
Fox, E., Ridgewell, A., & Ashwin, C.(2009).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biased attention and the human serotonintransporter gen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Sciences, rspb-2008.
Keller, J., (2015). What Makes Americans SoOptimistic? The Atlantic.
Norem, J. K. (2001). Defensive pessimism,optimism, and pessimism.Optimism and pessimism: Implications for theory,research, and practice, 77-100.
Oettingen, G. (2015). Rethinkingpositive thinking: Inside the new science of motivation. Current.
Popova, M. (2012). Why We're BornOptimists, and Why That's Good. The Atlantic.
Scheier, M. F., Carver, C. S., &Bridges, M. W. (1994). Distinguishing optimism from neuroticism (and traitanxiety, self-mastery, and self-esteem): a reevaluation of the Life Orientation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6), 1063.
Sethi, S., & Seligman, M. E. (1993).Optimism and fundamentalism. Psychological Science, 4(4), 256-259.
Sharot, T. (2011). The optimismbias. Current Biology, 21(23), R941-R945.
Weinstein, N. D., & Klein, W. M.(1996). Unrealistic optimism: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Social andClinical Psychology, 15(1), 1-8.
Puniewska, M. (2014). Optimism Is the Enemyof Action. The 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