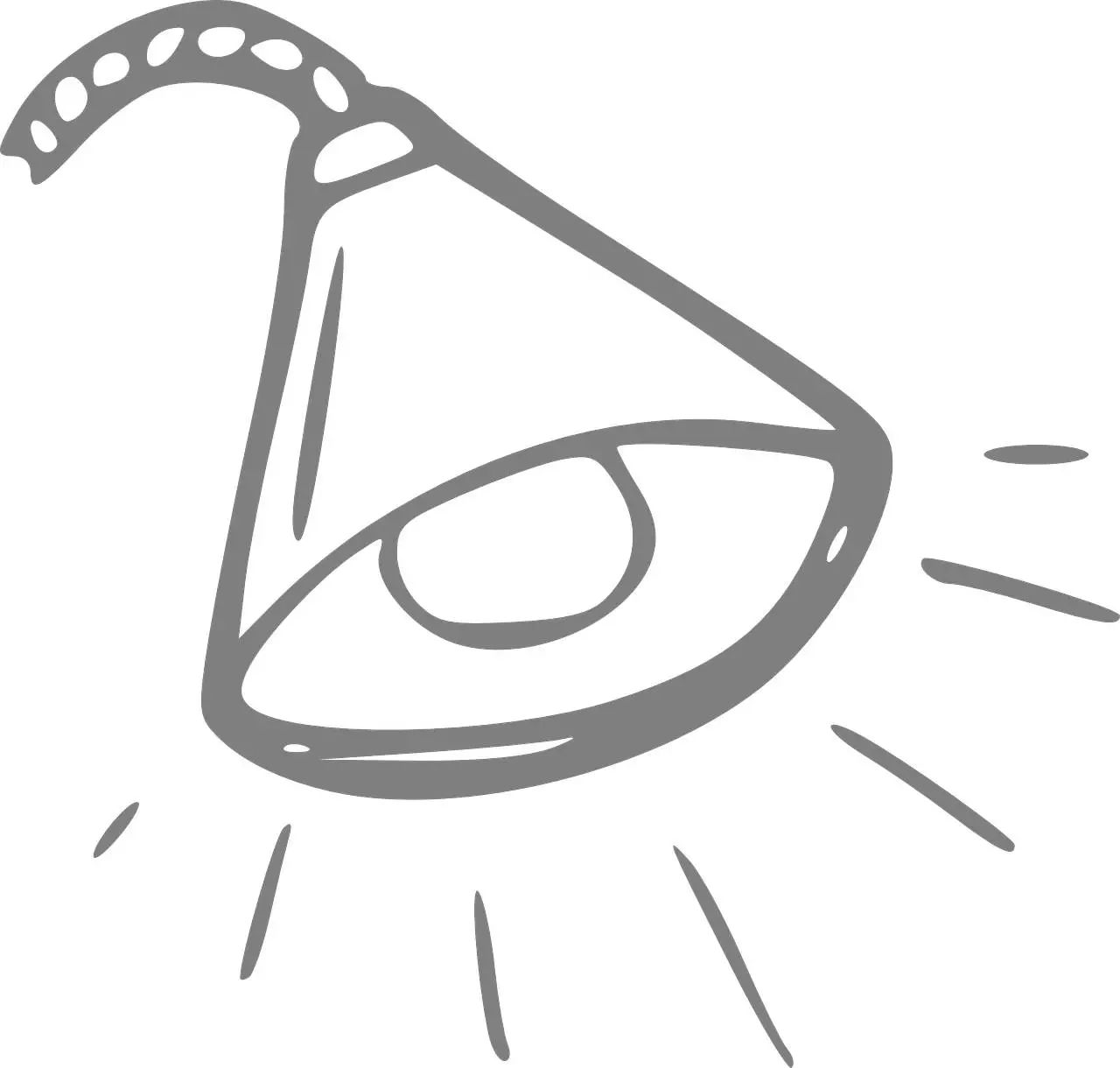11月中旬,川滇横断之旅的第15天,我和施展、郭建龙、李硕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及当今世界关系的对谈。他们三位都是我非常喜欢和尊敬的青年历史学家,我和施展曾经围绕着《枢纽》进行过一次对谈(对谈回顾:
换个视角看中国
),郭建龙的《丝绸之路大历史》《汴京之围》《帝国密码三部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历史著作(
对谈回顾:
且谈血肉盛唐
),李硕则凭借着独特的历史视角写下了《南北战争三百年》《翦商》《历史的游荡者》,所以希望这一场洱海晚风里的对谈,能通过字里行间的力量带你一同穿越古今,看向千年。
俞敏洪
:大家好,今天晚上我们将做一场穿越中国历史的对谈,我身边的是郭建龙老师、施展老师、李硕老师,这三位都是中国当代做历史研究时无法绕开的学者,今天晚上我们就轻松地讨论一下对学术研究的体会和感悟。郭建龙老师和施展老师以前都在我的直播里出现过,大家都比较熟悉,李硕老师则是第一次来,施展给大家介绍一下李硕老师吧!
施展
:李硕老师是非常有意思的人,他学术研究的角度、深度、视角、问题点都是中国学界非常独特的存在。如果说别的人不可或缺是因为整个拼图里需要那么一块,那李硕老师则是完全把拼图打破,重新组合起了一块拼图。
大家都比较熟悉李硕老师的《翦商》,但李硕老师真正的成名作是《南北战争三百年》,不是美国的南北战争,而是从卫青、霍去病那会儿开始,一直到南北朝后期的那段历史。我读完这本书后特别受启发的一点是,之前我一直不明白,匈奴跟西汉在早期彼此之间打的时候,战法是相互克制的,相互都能让对方很难受,但谁都没办法打掉谁,直到卫青、霍去病突然异军突起,一把就彻底把对方打穿了,怎么就那么牛呢?就因为这两个人牛吗?结果李硕老师在那本书里给了一个对我来说足够有说服力的答案,具体是什么,大家去读李硕老师的《南北战争三百年》(笑)。
之后他又出版了《孔子大历史》《楼船铁马刘寄奴》,以及《俄国征服中亚战记》。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在中亚争夺控制权,“大博弈”这个词几乎就是这个事情的专有名词,后来英国人彼得·霍普柯克写了《大博弈》(
THE GREAT GAME
),但这本书里只写了英、俄的视角,在这场大博弈当中,还有不在场的第三方——中国。英俄大博弈以帕米尔高原为代价,帕米尔高原上有所谓的“八帕”,本来全是中国的,但今天只有一帕了,另外七帕都是在大博弈的过程中被英、俄搞走了。所以英国人写的《大博弈》,中国是一个不在场的第三方,李硕老师则想写出中国人自己视角的《大博弈》,于是李硕老师就写了一本俄国在中亚怎么搞事的书,同时又计划写一本英国在中亚怎么搞事的书。为了写英国,他就要到当年英属印度的地方做调研,其中很重头的一个板块就在巴基斯坦,结果2023年,李硕老师在巴基斯坦突发疾病倒下了,当时一度以为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我们很多好朋友都非常地难过,上帝给他关了一扇门又加了一把锁,但万幸他自己把窗户推开了。
李硕
:我当时得病以后,回国住院一两个星期之后才知道消息,施展就跟我联系,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没来得及写出来,可以跟他谈一谈。
李硕
:当时那个场景就很像武侠小说里要传一本秘笈似的,这个东西我传了多少年,下面我要传给别人让他发扬光大的那种感觉。当时我记得我的第一家医院已经让我出院了,意思你这个病已经没有做手术的希望了,就不要占着病床了,我就换到了第二家医院,施展来的时候,我就在第二家医院。
施展
:李硕真是有豪侠之气,我到了医院,想着他在床上躺着,我陪他聊聊天,听他给我讲讲他还有什么研究计划,然后他当时拎着那个袋子和导管就下楼了,要找地方喝茶去。
李硕
:我当时的病症是胆管完全被肿瘤堵死了,胆汁无法进入消化道,所以在胸口插了一个引流管,把胆汁吸引到一个塑料袋里。
郭建龙
:我去看了两次,每次都拎着那个袋子,蹦蹦跳跳跟着我们一起走。
李硕
:施展那次来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我的大学同学和家人,到那跟我做一些类似告别的事,那些朋友还很不理解,你都快死了,怎么还有人跟你谈历史、研究?耽误你的时间,就想打他,哈哈哈。
李硕
:对,其实我理解他的这种做法,你出于客套来看看我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我那种状态很难看,也不想让人看,看了大家都伤心,所以也没必要。我觉得他这种还关心我脑子里还在想什么且没表达出来,想看有没有机会能把它记录下来继续去做,我倒认为是真正有价值的。
郭建龙
:他去巴基斯坦之前跟我联系过,我知道他想写一本什么书,所以我特别替他感到可惜。
俞敏洪
:印度河现在在巴基斯坦境内,当初印度河和恒河文明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后来被英国人人为分成了两部分。
郭建龙
:对。他去巴基斯坦游历之后,他想写的第一个层面是他观察的现在的巴基斯坦;第二个层面,也是最底层的层面,是四千年前的古印度河文明;第三个层面,最早捅破印度河文明的是一个英国逃兵,这个逃兵又和英俄大博弈联系在一起,所以第三个层次是英俄大博弈。如果他能写出来,就一定是非常好的作品,非常明显的三个层次,但又交错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惜。后来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非常认真地做了PPT给我们讲了一遍,我们还录了下来,以为这个可能就是李硕的遗言了。
李硕
:因为建龙以前也游历过巴基斯坦,他也关注历史,所以我还把我之前搜集的巴基斯坦的资料,包括1820年英国人在当地的游记,都给他拷了一个硬盘,全给他了。
郭建龙
:如果你死了,那个东西现在就已经整理出来了,但因为你没死,现在还扔在那儿呢。
李硕
:如果我死了,他肯定还会再去巴基斯坦,把我想去的地方再走一遍(笑)。
郭建龙
:这我做不到,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说的那些文字整理出来,把英国人的游记翻译出来,真正你想写的那本书只有你能写。
俞敏洪
:其实我读完你的书之后,非常喜欢,然后施展老师告诉我说,李硕老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把我吓得汗毛林立,我说他是有什么事吗,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需不需要我介绍下北京最好的医学专家?后来你居然活过来了,这太牛了。
俞敏洪
:我个人认为,
世界的形成是偶然因素多于必然因素
,我一直觉得这就是命定的。你们都是研究历史的,历史上很多的转折点并不是必然的转折点,而是偶然的转折点,人个性不同、性格不同、统治者的指挥方式不同就形成了历史的改变,是不是?
俞敏洪
:你的身体能恢复真的很让人高兴,能给我们讲一下心路历程吗?
李硕
:我为什么在2023年春天去巴基斯坦,其实这事说起来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因为写完《翦商》之后,我已经在大学找了一个工作,当时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差我这个人去学校报到了。我当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要去上班的那个学校,大半年以前在巴基斯坦办了一个孔子学院,那里发生了一起爆炸案,有三个老师在那次爆炸案中遇难了,我当时想的就是,如果我现在去这个学校报到、入职、上班,这学校肯定不会允许自己的老师再去巴基斯坦旅游,学校会担心再出安全事故、爆炸案件,所以我就想先不去报到,趁现在没有人管我,我去巴基斯坦好好转转。所以我在出发前,就已经有了各种心理准备,当我生病之后,我其实并不在意,因为这些东西我都准备过了,唯一不同的就是,原来我想象的死是我在路途中遇上恐怖袭击或者是车祸翻车,死得很干脆,结果没想到是在医院里拖泥带水、浑身插着管子去死,我反倒因为这个觉得很别扭、很不舒服,其他方面我真没什么特殊的想法。
(李硕老师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图片来源:“
自P
AI
”公众号)
我有一个很具体的印象,当你确诊绝症之后,哪怕是会诊后多数意见已经确诊了,医生也不会直接告诉病人本人,而是会告诉你的家属或者朋友,所以当时是我在成都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转告我这个消息的,他就说,李硕,你应该是日子不长了,我也理解你,你现在手里还有什么写完了但还没拿出来的,你是不是趁这个时间赶紧整理一下?他当时跟我说了以后,我就明白了,我应该没得治了,时间不长了。接下来的那几分钟,我脑子里浮现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班主任站在讲台上宣布,马上要放暑假了,同学们可以带着自己的板凳回家了,当时我那个板凳是蓝色的,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那个蓝色的板凳,我要把它扛回家了、放下了,我什么心都不用操了,我原来想干的那些事情,答应了别人但还没交代的东西,我都不用管了。
李硕
:对,就是准备放假的感觉。我当然也有牵挂,就是朋友说的我手里那些还没拿出来的东西,得去整理一下,其实就是我第二年出版的《历史的游荡者》,那是我在生病期间整理的,其实我那时候的心情很放松。
俞敏洪
:那时候没有突然觉得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吗?
李硕
:没觉得,我之前都想过了,如果这趟死在外面,就死在外面了。
俞敏洪
:如果真到了回不来的那一刻,你想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李硕
:其实就我的经历和病情,还真没到临死之前最后那一刻。但我想到过一个电影,好像是《非诚勿扰2》,里面有一位主人公得了一种绝症,他给自己办了一个临终告别会,就有朋友在告别会上问他,你现在要走向死亡了,你的感觉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感到前面有一扇门,但你不知道推开门之后,那后面会有什么东西。我当时在医院也是那个感觉,感觉自己离那个东西近了,但它到底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毕竟我还没有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俞敏洪
:这方面我的体会可能更深,当你走向失去知觉、濒临死亡的那一刻,其实你不可能想到那扇门后面是什么,我经历过两到三次这样的感觉。
李硕
:不过人或者病情有各种个案、各种可能,我有一位朋友是大脑发炎,被一种病菌感染,他昏迷了很多天,说那些天里,别人看他就跟死了一样在那躺着,但他大脑里产生了各种幻觉,就像吃了蘑菇产生的幻觉一样,因为大脑被感染以后就是那样的。所以他说他再活过来之后,他理解了为什么有些人会在濒死状态中得到一些神奇的感受,也许就是因为大脑被感染了产生的幻觉,但如果不死于大脑感染,可能就没有这些感觉。
俞敏洪
:《金刚经》说“如梦幻泡影”,我觉得如梦幻泡影是几种情况,比如我们喝醉酒也会有幻觉,吃了幻觉的药会有幻觉,濒死之前也有幻觉,因为幻觉是大脑给人的安慰。但我的几次“拉倒”都没有产生过幻觉,我喝酒过多以后突然送到医院,根本就来不及幻觉;我被打了超量麻醉针,送到医院抢救了七个小时,也完全没有意识,只知道他们把那个针打到我身上的一瞬间,其实也就是一两秒,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我儿子8岁的时候,因为长了蛀牙需要换牙,医生当着我的面说,你签字,我给你儿子打全身麻醉,那个麻醉针还没推完,我儿子一下就倒下了,我当时就吓得不行,医生说没事没事,我就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倒下的了,一秒钟都不到,根本来不及幻觉。
我觉得人是在慢慢失去知觉的过程中,他会产生一系列幻觉。我有这个经历是因为我后来去做肠胃镜检查要打全身麻醉,我第一次全身麻醉的时候,医生把普通人的剂量打完以后,边打边跟我说,俞敏洪,就10秒钟,你就慢慢跟我们聊天,你就没有意识了。然后过了一分钟,我还在跟他聊天,他说我给你加量,加完量以后,我过了五分钟才晕过去,后来他说人对麻醉有抵抗能力真不容易。
李硕
:这个还好,在手术之前没有及时麻醉,如果手术做了一半,你醒过来了,那不更可怕吗?
俞敏洪
:我没有做过任何手术,我唯一的手术就是肠胃镜检查,医生说我给你加了量,你比一般人醒过来的时间还早了十分钟,所以我抗麻醉的能力应该是比较强的。
俞敏洪
:你现在是缓过来了,但你去的那些地方可能会让你送命,你不会觉得不值吗?
李硕
:我去过的很多地方可能是很多人不敢去的,我去之前就会想,大家说这么危险?我就去看看,如果死了也值得,我觉得这就是足够大的价值。就像寓言《小马过河》一样,你去之前听过很多种传闻、很多种想象,你去看了之后发现都不是那个样子。
俞敏洪
:建龙也经历过这种生死考验,你跟他的想法一样吗?
郭建龙
:为什么我们俩能成为好朋友,就是因为我们俩的想法有太多一致性,所以他说的那些话,我基本都不用补充什么,完全一致。我觉得
人是需要冒险的,但当你选择冒险的那一刻,你必须知道冒险的代价是什么,当你愿意承受这个代价的时候,你才能去,否则就不要去。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冒险,但你一旦选择了去,你就要承受一切代价。
李硕
:建龙是在阿富汗和非洲的时候,被人绑架、打劫了。
郭建龙
:201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的城边上,有一个高山,在那上面看全景很好,上面还有一个古代的碉堡,就是希克马蒂亚尔(阿富汗前总理)不停打炮的地方,结果我快到顶的时候,当地人跟说我这太危险了,你赶快下来,我就跟另一个中国哥们按原路返回了,这就麻烦了,因为上去的时候就被人盯上了,下来的时候还原路返回,经过一个贫民窟的时候,出来几个小伙子就要把我们架走,当时我在这边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的同伴就跑下去了。
郭建龙
:我在非洲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其实打劫的是本地的一些小团伙,但他们打劫完你以后,会把你关到一个空屋子里,全村的人即便都知道这里关了一个中国人,也绝对不会有人跟警察说,他们会在几次转移之后,把你卖到塔利班手里去。我当时就坚决不进那个屋子,我就靠在那个墙上坚决不进去。当时我也被砸了,头上也有伤,但也没完全砸晕,后来突然贫民窟里出来一个人,他们一看我拉不走,就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拿走之后,走掉了。
郭建龙
:我当时有这样的意识,因为前几年正好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和一个美国教授到喀布尔的某一个大学访学,结果在校门口被一辆车直接绑走了,等到他们被放出来都是几年之后了,肯定是各种各样的人用了多少钱、花了多少努力,最后才把他们放出来,后来他还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类的(疾病)。所以我有这个意识,坚决不能让他们绑进去,但当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只能靠在那里坚决不动。
郭建龙
:在撒哈拉以南的马里,那次生病,但那次也有这个意识,因为当地人跟我说了,本地人会绑架你,一百万美元就卖给ISIS,ISIS接着就开始勒索,如果你是美国人就跟美国政府要价两千万美元,基本上降到两三百万美元,如果还不放人,就撕票了,基本就是这样一个程序。
俞敏洪
:为什么你一定要冒这样的风险去写一部历史书呢?
郭建龙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解答心里的疑问。有些人不太愿意做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他愿意做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工作,我觉得我们几个基本都是这样的人。
施展
:不太容易被很规范化的模式规训掉,不太愿意接受那样的生活。
郭建龙
:对,但你要首先考虑清楚其中的风险,在知道风险的前提下,你还愿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一旦选择了,你就要承担全部。
郭建龙
:去阿富汗的时候还没结婚,去非洲的时候结婚了,那时候我就小心一点了,有人骗我走,那人告诉我这个船第二天才离开,可以跟着他走,能带我去干嘛干嘛,实际上那个船一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如果我离开了那个船,就完了。
俞敏洪
:我很好奇,你恋爱前后,到外地考察时的人生态度有什么改变吗?
郭建龙
:有改变,真的有改变,特别是去阿富汗的那次,报警之后,伤口也处理完了,彻底没事了,我就借别人的电话赶紧加了她的微信给她报信,我就说我已经没事了,再倒叙我是什么情况,我说你千万放心,我绝对不会再这样冒险了。比如这里有一条危险线,以前老想着稍微越界一点去看一下,但现在我就往回收了,尽量不越过去,去非洲的时候我就没有越过安全线,稍微往回收了一点。
俞敏洪
:这很明显是对心爱的人和不心爱的人的区别,对心爱的人先报平安,再说我遇到了什么危险,他给我发的是我遇到危险了,过了半个小时告诉我“我平安了”(笑)。施展应该没有这方面的感受?
施展
:还没遇到过这种,我遇到过一些危险,但都没有到他们这么险的状况。当时是在加纳,读过《枢纽》的朋友可能知道,那本书前半段是写历史,后半段是写当下,里面有大量关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相互循环关系的讨论。我在书里形成了一个所谓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的理论假说,那个假说就是基于我在非洲那几年的调研建立起来的。我当时做了很多次调研,有一次去调研,我跟着一个公司去坦桑尼亚,那个公司打算去那边投资,邀请我作为顾问到那里考察。即将出发之前,那个公司要跟我一起去的人,就叫他雷欧吧,雷欧接到一个电话,说加纳那边有金矿,想邀请我们过去看看。
那段时间正好有一批广西人在加纳淘金,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一种独门技术,即使是别人淘不出来的矿,他们都能淘出金,赚了很多。他们有技术,但他们没有矿权,矿权都掌握在酋长手里,他们就跟酋长合作,酋长说开采,这些人就去开采,然后跟酋长分利,结果分利的时候他们没有报实数,自己揣了一部分想偷偷运出去,结果被隔壁尼日利亚的黑帮知道了,沿途就设伏抓他们。但广西是出太平天国的地方,他们不惧这个,这帮哥们自备武装跟尼日利亚的黑帮火拼,把尼日利亚的黑帮打跑了,加纳政府说这还了得,就派了警察来抓他们,结果他们装备太好了,警察也打不过他们,最后出动了军队,才把他们打跑了。
这帮人被打跑了,但金矿还是需要有人来开发,所以一个在加纳的华人,就给雷欧打电话,想邀请我们去那里考察一下。雷欧就跟我商量,咱都去了坦桑尼亚了,再往西飞进加纳也正好。刚好我也很想去考察一下,看看中国人在那边做的工作会拉动当地怎样的产业演化,这也跟我当时做的全球双循环的研究理论模型很贴近,我就特别想去看。但我们来不及办签证了,雷欧就问我怎么办,你还去不去?我就突然热血上头了,我说咱可以测试一下。当时我已经去过好几次非洲了,依照我在非洲的经验,如果这个人真有本事,咱没有签证他也能把咱给带进去,如果他能带进去,说明这个人在当地还是有一些实力,就可以考虑跟他合作,如果带不进去,就没必要跟他合作了。结果我就忘了,做这个测试的筹码是我,万一带不进去,是我被扣在那,而且我当时还觉得自己思路特清晰,实际上非常愚蠢。
雷欧说这个人打电话、通邮件,给人感觉有点像个骗子,而且那个人已经把在加纳的所有行程发过来了。我就先联系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退休之后在加纳设立的和平培训中心研究所的主任,后来又找到了当地总工会的副会长,那种工会多数都有黑道背景。我就跟雷欧说,我们到了以后先不按那个家伙的行程走,咱先去拜会这两个人,让他不知道咱水有多深,然后再去走他那些行程,他就不敢对咱使猫腻了。
我当时觉得这很江湖,思路很清楚,结果根本就非常愚蠢,我才是那筹码,如果我进不去,所有这些都白扯,结果到了那真就进不去,海关把我扣住了,对着我各种威胁、恐吓、大吼大叫,最后说要拘留我。一开始我仍然抱着幻想,又给工会的打电话,又给安南中心那哥们打电话,我说能不能把我捞出去?结果他们说你等我电话,半小时之后陆陆续续都给我回电话,说确实捞不出来。他们就准备拘我了,到了这一步,我不得不用别的办法,最后勉强让他们同意不拘我,而是把我遣返回来了。
俞敏洪
:最终给那个地方的人每人200元人民币(笑)。
施展
:一开始他们跟我要钱,给了钱就可以进去,我就不给,最后决定要拘我和雷欧的时候,雷欧说要不咱给吧,结果海关说现在来不及了,一开始你给我就行,现在晚了。
郭建龙
:加纳比较防范,因为黄金资源的存在,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盯着,在西非来说是一个比较难进的地方。
俞敏洪
:但我觉得你还好,你是在生死地边缘徘徊了一下,建龙是经过了生死地,李硕是真正地从生到死、从死到生。
俞敏洪
:我读李硕老师的《翦商》,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一直认为商朝文明是夏朝文明的延续,而且从夏朝就已经开始华夏礼仪文明了。但你在这本书中,通过考古学来证明商朝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突破了中国历史一贯的认知,你当时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李硕
:其实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以前了解过一些考古学的知识,我知道中国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夏商时期都有过一种宗教现象——杀人献祭,把人杀死之后献给神。当时同时杀的不一定只有人,也许有别的家畜,猪牛羊什么的,但都是作为一种礼物食品献给神,这种在早期多数人类古代文明都有过。但看考古会发现,中国到商代时期,这种现象特别多,留下了大量杀了人的尸骨祭祀坑,包括商朝向神献祭的时候,会把奉献给神的物品的数量刻在骨头上形成甲骨文,所以留下来了很多考古证据。当时我就想探究,这种杀人献祭的宗教行为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在新石器时代一直传承到青铜时代,最后又怎么从我们的知识、记忆中消失?我是带着这个想法去写这本书的。
还有一个具体触发的诱因,我当时看了一个美国导演梅尔·吉布森拍的电影《启示录》,反映的是拉丁美洲玛雅、阿兹特克这些中美洲文明里杀人献祭的现象,而且非常直观。
俞敏洪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起了阿兹特克人,我觉得你写的内容跟阿兹特克人尽管在不同时代,但行为是一致的,甚至比他们更惨。而且我看到过一些推断,说阿兹特克人就是商朝的后裔,当然不一定有历史依据,但他们的行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俞敏洪
:当然可以猜测,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最主要的研究方式就是猜测以后的论证,但我觉得你的书是做了充分论证的。
李硕
:需要查大量的考古报告、文献,得去梳理,从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那些很小的聚落、部落,有些尸骨坟墓是正常埋葬的,死者是正常死亡,但也有一些明显看得出来就是他杀,摆放得很整齐,而且伴随着其他牲畜的尸骨一起摆放,这肯定就是一种宗教献祭行为。准备写《翦商》的时候,我整天在考古报告里找这些东西,要么是各种完整或零碎的尸骨的照片,要么就是文字方面的记载,描述这个骨头是多大小孩的,胳膊怎么被砍没了,怎么碎尸了,我就感觉人的心态特别压抑、特别难受。
我在那个期间没有到医院做检查,但我知道那段期间,我心里应该是抑郁的。抑郁症有一些具体的指标,比如激素分泌水平、脑电波什么的,我没有做那些测试,但后来查抑郁症的相关症状,我都符合。不过我当时给自己一个安慰,我告诉自己,我的心态还是比一般人皮实,如果换个人来做这个工作,可能工作都没完成就自杀了,但我咬着牙把这个工作干完了。
俞敏洪
:那些尸骨都是三千多年前的了,怎么会这么影响你呢?
李硕
:这个不好想象,我在生活中也很少见人的尸体。可能就像法医的心态,你面对着这些残留的尸骨或者杀人现场,如果你想把它复原出来,就会去想象当时这些人是怎么被杀死的,杀人的人为什么要杀他……你的心情肯定就不会太好。
施展
:《翦商》里还有“翦”的部分,李硕在书里谈的是商朝的人祭是如何残酷,还有一部分是周公如何把商朝彻底掩埋掉。我印象特深,有天晚上我去俞敏洪家跟俞敏洪聊天,聊到周公要把商朝所有的过程彻底抹掉,让人们不知道这些事的存在。当时我们就讨论,商人不是周人的敌人吗?商人越残暴才显得周人越正当,为什么还要把商抹掉呢?后来我们猜测,是不是因为周公意识到,那些恶不是内在于商人,而是内在于所有人,如果不把它抹掉,周人的残暴一旦被诱发出来,下场也不会比商人更好,所以周公要制礼作乐,一方面要把商人人性当中最诱发的东西彻底掩盖掉,同时把另一种有可能向上的东西烘托出来。
俞敏洪
:商朝这种人祭的传统和周朝礼仪的传统是因为两个种族的不同,还是因为顺应社会发展的思想转变?
李硕
:都有。第一,从考古上能看到,周这个小部族在西部刚刚兴起的时候,确实没有杀人献祭的传统,至于为什么没有,就很难回答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先周遗址,即周人在灭商建立政权之前生活的遗址,确实没有杀人献祭的现象。第二,这些文化现象是可以学的,有些史料中就记载了,周武王灭掉商朝刚刚建立周朝时,也搞杀人献祭,而且跟甲骨文里商王杀人献祭一模一样。周这个部族也许原来没有这种献祭文化,但在学习商朝、和商朝斗争的时候,他会学这个东西,所以人性共通的地方是可以互相学习的。
郭建龙
:这就回应了施展老师的问题,周武王在灭商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变成商人了,这时周公才会防范性地一定要把这个现象灭掉。
俞敏洪
:我觉得周文王被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理解了商朝内部的运作规则,并且充分理解到了,他要怎样做才能把商朝反下去。现在考古论证,在夏朝甚至在夏朝以前,就已经有八卦图案了,所以八卦应该不是周文王凭空想出来的,也是历史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但我觉得他最大的思考是在于他被关在羑里时,意识到我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商朝给推翻掉,所以后来周朝的一些礼仪应该都是从那个地方延续出来的,要反其道而行之。至于神神道道的八卦也好,天命也好,都是为了说服老百姓想出来的东西而已。
李硕
:三千年前的人的认知水平和我们今天科学的、无神论的完全不一样,在那个时代,人都会带着迷信的、有宗教思维的体系去理解这些事情,所以所谓周文王演八卦、写卦爻辞,背后肯定埋藏了很多政治思想。
俞敏洪
:你觉得周朝和商朝突然间对人的观念的转变是出于什么样的契机?我读《翦商》和其他历史史料,感觉商朝和周朝对人的观念的转变完全不一样,有可能部分意义上还能把元朝和唐朝对人的观念进行对照。当然,元朝没有商朝那样的人祭传统,但他们会把人分成四个等级。此外,商朝和元朝都很注重贸易,唐朝和周朝很注重人性。尽管朝代关系是倒过来的,但还是有一点关联性。从草原或者更加广阔的地方来的,对天地尊重,对人不尊重,和文明演化出来的对人的尊重和天人合一的想法,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
郭建龙
:俞敏洪提到了元朝的四等人,其实元朝的四等人和印度所谓的种姓设置有一定的对比性。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是在古印度河文明衰落以后,带有游牧色彩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后,为了巩固他们作为帝族人的一种统治所逐渐强化和建立起来的一种体系和系统,贱民群体就是现在的达利特人。其实这是一种统治术落实在社会结构上,最后变成了一种固化结构,几千年下来还保存着。元朝其实和雅利安人建立的是有一定类似性的东西,也是想保留一定的阶层性,而且是以民族划分的方式保留下来,只不过没有做到更长的延续性。
施展
:但我觉得元朝统治的宽松度其实非常大,以至于后来朱元璋觉得元朝统治太宽松了,把社会搞得乱七八糟的。
郭建龙
:按照现在中原汉人的传统看法,元朝的统治有它宽松的一面,为什么?因为它的疆域比宋朝大得多,但它的税收连宋朝的一半都不到。它跟北魏金辽有一个什么区别呢?这些游牧民族下来以后,首先占据的是中原,这时候就会采取汉文化。但元朝有一个转向,蒙古人成吉思汗在本来可以拿下北中国的情况之下,突然转向中亚地区,所以他首先打下来的是中亚。
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拿下了很多中亚和波斯地区,所以他首先接触的是穆斯林的商业文明,他的税收系统等等可能更多采用了穆斯林的那套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色目人才会变成第二等,比北方汉人要高一等。他从财政制度、政治制度上更偏向于中亚和穆斯林的一种制度,才让他在完全拿下中国之后,没办法完全复制中国的那套制度,因为里面夹杂了太多成分。这里面有不好的地方,比如他引用了穆斯林的包税制,为了赚钱,把税外包给一个包税人,比如大理的税外包给俞敏洪,俞敏洪每年能从大理压榨出300万的税收,你只要交给我100万就行,剩下的200万就归你了,但好的方面在于他会重视商业。
郭建龙
:对。西方传教士到了哈拉和林后去见蒙古大汗,大汗说,你是基督教,我这也有和尚,也有伊斯兰教,你们在一起辩论一下,看看谁正确。大汗就听他们几个辩论,辩论完以后,大汗就发话,我们蒙古人信仰的是老天爷腾格里,但大家各有各的信仰,你不能干涉别人,也不要强迫别人,好了,大家喝酒吧。是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他们在信仰上非常开放,也形成非常独特的文化。
此外,重商主义会妨碍它建立更巩固的、基于土地的制度,因为农业社会最好的制度还是基于土地的,中国已经测试出来了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虽然看上去很死板,但是很稳固,江山能达到三百年。如果土地制度没建好,税收来源又主要在南方,南方的税收组织又完全没有结构化,这时候你还只能依靠一条大运河把税收运到北方去,一旦南方发生叛乱,把你的粮给断了,你的结构就非常不稳固。所以
蒙古的元朝集团,好在于激发了人的想象力,激发了人的商业精神,但坏在于他们没有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社会结构。
俞敏洪
:这个当然有道理,我认为后来元朝灭得比清朝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它的组织变革能力比清朝差很多,清朝只变革几十年就完成了,蒙古一百年都没有完成;第二,它没有很好地和汉文化或者中原上千年的文明做好融合。元朝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就应该统治你,清朝是假装跟你一家亲,皇帝们都写汉字、写汉诗。“假装”有时候很重要,会让你幻觉性地产生认同,觉得我跟你就是一家,而且还会产生另一种幻觉,奴隶会反过来认为自己把主人同化了,但主人其实很清醒。
俞敏洪
:我想问问李硕,各种历史考察都认为,商朝、唐朝来自东北,夏朝、周朝、秦朝来自西北,有人说这两种文化带来的两种统治方式很不同,你有这方面的认同吗?
李硕
:这个对比太粗略了,周和秦虽然都是从西北过来的,但风格太不一样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一点可以说,在商朝中期确实出现了一些中原本地文明没有的东西,最明显的就是马拉的双轮战车,在商朝前期没有这种东西,但商朝后期殷墟时期突然出现了,而且技术非常成熟,可能不只中国是这样,距今3000年到4000年之间,整个亚欧大陆都出现了马拉战车。
俞敏洪
:我觉得是世界贸易传播的结果,跟商朝和周朝没有关系,不管是商朝、周朝还是夏朝,只要在那个时代,一定会出现普及。我一直觉得
世界贸易和文明交流的脚步从来不会因为统治阶层或者朝代的不同而被阻止
,那时候刚好是两河流域发明出车轮后往全世界普及最集中的时期,所以商朝发现考古车轮的结构形状跟两河的战车形状非常一致。这就是一个文明传播的结果,跟人群没关系,但跟贸易的发展有关系。
李硕
:但在北印度的那些征服者,他们确实就是架着马拉战车的外来人群,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伴随着人种迁徙的技术传播。
俞敏洪
:当然,但中华文明包容性一直比较强大,可以接受外来技术、外来人种,所以中华文明一直是延续的,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施展
:实际上北中国人多半混着胡人血统,南中国人则多半混着东夷的血统,所以从人种的概念上来讲,其实没有纯种民族的人。
李硕
:分成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不用人种这个词,可以用人群。第二,我个人认为,人种可以说是没有最纯粹的。
李硕
:我认为马拉战车和这个地区有关系,但从人群上看没有大的变化。
俞敏洪
:是的,新疆小河墓地发掘出来的人有典型的西方人特征,现在我们的血液中或许部分流有小河墓地的血统,因为它是一个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结果。我们这次在横断山脉地区所看到的所有民族,谁会没有羌族、氐族、本土土著民族的特征呢?我觉得大部分都有,只不过他们在山谷中,过了一百年、二百年,部分风俗被改变了,就被分成了不同的民族。
施展
:我还是更喜欢人群或者族群的说法,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民族”经常被当成一种纯血的汉人、纯血的蒙古人、纯血的大和民族……但这些都是幻觉,所谓的纯血是不存在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没有人去追寻纯血,这种纯血就是近代民族主义诞生之后形成的一种新想象。
施展
:刚才建龙聊到元朝的开放、包容、各种人群的多元聚合,我就想到我正写的那本新书,书里刚好有一段是忽必烈还没有入主中原之前,他到了漠南金莲川组成了金莲川幕府,是忽必烈的参谋本部,“金莲川幕府成员的来源和信仰极为多样,有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开放性,其中有出身蒙古的将士群体,出身金朝的女真人、汉人,以及出身南宋的汉人谋士,有理学家,有文人群体,出身于西域以及中亚胡人的谋士和理财专家,出身于中原地区的著名道士、汉传佛教的高僧,出身雪域的藏传佛教的高僧。幕府当中除了蒙古人原有的萨满教,还兼容并蓄了儒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拜火教等等各路信仰。幕府的人员配备有包容天下的气象,当时的金莲川仿若一个世界帝国的胚芽”,金莲川在燕山以北,在今天的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那个地方,属于内蒙的正蓝旗。
施展
:金莲川在燕山以北,却让来自燕山以南投身幕府的汉人儒士群体获得机会,展开了一种远超越于中原之上的想象力,怀抱着超越“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在这些儒士当中溢出一种金莲川情结。我就引了其中的一首诗,“岭北乾坤士马雄,雪满弓刀霜满颈。稀星如杯斗直上,太白似月人有影。寄语汉家守城将,莫向沙场浪驰骋”。
李硕
:但对于金莲川幕府那么“白左”的包容性,你这种描写会不会过于渲染了?蒙古人会轻易和其他族群融合吗?
俞敏洪
:他的包容体现在一种另类性,不是对文化和思想的包容,是对文化和思想无感的包容,我对你无所谓,你别参加我的科举考试,你们汉人的好建议我接受,但不接受你们的思想。
施展
:其实用“白左”来形容蒙古人非常不合适,“白左”是一种我们要对世界充满爱的包容,蒙古人是把你们打服之后包容你们,前提是把你打服,这跟“白左”完全不一样。
李硕
:我不太懂元史。元朝的时候,蒙古人是不是很坚持部族内不能和汉人通婚?
俞敏洪
:不一定。当时元朝的人,不是今天的蒙古人,他们把人分成几个等级,高等级的人想和低等级的人发生性行为是很自由的,但低等级的男人,想和高等级的女人发生性行为就不行。举个比较庸俗的例子,美国的白人想跟当时的黑人女性奴隶发生性行为会很随意,但黑人男性当时想和白人女性相处是不可能的。今天,美国白人女性找黑人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在当时的蒙古,四种等级之间,从上而下是贯通的,但从下至上是不贯通的。
李硕
:这也是我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拿元朝和辽朝比,辽朝的契丹统治者对于和其他民族的人通婚更不介意,甚至他们的皇室、高级贵族都会和汉人、渤海人通婚。
施展
:辽朝的韩德让当时已经成为辽圣宗的亚父了
(亚父:主要作为尊称,表示仅次于父亲的人,是对某人表示尊敬的一种称呼)
。
李硕
:说到统治阶级对于血统的重视和是不是忌讳通婚的问题,在大航海时代以来,可能最重视种性区别和通婚限制的是北欧信基督新教的这派殖民者,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人,英国人所影响到的美洲、澳洲殖民地可能是最介意的。相对比较重视平等,不太介意的是南欧的天主教,所以现在拉美的混血程度非常高。
俞敏洪
:拉美更加开放,某种意义上形成了拉美族,他们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还是当地的土著,根本说不清,混在一起的,拉丁美洲本身的人群就这么形成了。
李硕
:是的。他们可能更重视宗教的虔诚性,默认只要信了上帝,都听罗马教会的,大家就都是平等的,甚至可以通婚。
施展
:天主教会里面有等级,但跟清教有很大的区别。天主教会内部的神职人员有等级,主教、大主教、红衣大主教,一直到教皇,平信徒
(指基督教会中没有教职的一般信徒)
和神职人员之间也有等级之分,平信徒必须听神职人员的。天主教认为所有人都会得救,只是究竟该怎么得救,对于天主教来说,不信上帝的你太可怜了,你居然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你好可怜,我要拯救你,但因为你可怜,你啥也不懂,所以你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就得下地狱,你现在既然能听到我的声音,恰好是神把我派来了,所以你得听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得弄你,但是弄你的目的,还是为了让你听我的。
李硕
:而且天主教的这些教士、神职人员是不能结婚的。
施展
:新教内部则完全没有等级,都平等,但新教徒和新教徒以外的人是两个世界的,我是新教徒,我是已经得救了的,只要咱们都是选民,咱们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区别,都能得救,但如果你不信上帝,你就注定要下地狱,这是上帝对你的惩罚。
俞敏洪
:中华民族是怎么从商朝走到了周朝,再后来走到了大一统呢?
李硕
:商朝本身的统治阶层还是比较在意和其他被统治族群的区别,一般商王不会跟其他部族的人结婚,只在商族内部通婚,是比较封闭的内婚制。周朝灭商之后实行了和商很不一样的制度,周朝人是不能和本家族的人通婚的,要尽量和血缘关系远的人通婚。
俞敏洪
:商朝是血缘之内,周朝是血缘之外。有什么证据说明周朝是血缘之外的吗?
李硕
:周朝人有一个明文规定,所谓同姓不婚,这个同姓不全是现在的赵钱孙李。
李硕
:应该说是防止同父系通婚。其实他们不介意表亲通婚,但很介意同一个姓通婚,因为他们认为同一个姓代表同一个部族,同一个部族的内部是不能通婚的。
俞敏洪
: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初步意识到了,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同族通婚会带有基因缺陷?
俞敏洪
:这就涉及到了当时周朝规定的同姓不能通婚、同族不能通婚,是不是经过了几百年、几千年的总结,人类发现同族同姓通婚后的弱智会比较多?
李硕
:是基于医学统计总结出来的规律,还是基于别的原因总结出来的,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他们就是有意识地想结束商人那种非常独立、封闭、高傲的群体状态,你不能族内通婚,必须跟外族通婚,大家混血之后就分不清谁是谁了。
施展
:王国维有过一个解释,同姓不婚,因为往外分封的时候既会分封姬姓的,也会分封异姓的,同姓不婚就意味着必须得跟异姓之间有各种联姻关系,通过联姻的方式把所有的诸侯、贵族联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但即便是分封出去的异姓诸侯实际上也是武装殖民者,武装殖民者跟当地土著之间其实还是会有阶级区别,所以他们虽然跟异姓结婚,但他们并不跟当地的土著结婚,而是跟武装殖民的异姓诸侯结婚。
李硕
:打破的是族群的界限,坚持的是阶级之间的区别。
郭建龙
:现代的民族学、人类学有过研究,这样一种同姓不婚的制度往往是为了把自己的关系网扎得更广,同姓之间的婚姻只会让这个族群越来越小,越来越封闭,如果这个关系网很广,就要让孩子有更多的舅舅才行。
俞敏洪
:我有一个问题,动物直觉地知道自己不能跟近亲繁殖,比如一头公狮子如果去找母狮子,发现有两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它就会把它们驱逐咬死,这是动物性的一种排斥。人类嗅觉其实闻不出来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那么人类之间这种“排斥同姓通婚”的意识是怎么来的?
施展
:我看过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只能有一个纯演化论的猜测,动物很可能在最早期也有同胞婚姻,但那些在演化当中都被淘汰掉了。同样在人类当中,人类有一个普遍现象是禁止乱伦,为什么会形成禁忌?我只能作演化论的猜测,没有这种禁忌的人群里,有病的太多了,最后在族群竞争中被淘汰掉了,最后能剩下的都是有这种禁忌的人群,这些人实际上也说不清为什么要禁止乱伦,但就是禁忌,最后形成了一种文化潜意识。
俞敏洪
:我发现中华民族就是不断融合的过程,黄帝和炎帝的部族融合,“黄帝+炎帝”又和九黎融合形成黎民百姓……你们认为
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有决定性意义的民族大融合有哪几次?
李硕
:多数是伴随着所谓民族政权的更替,特别是在所谓分裂的乱世,比如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但我在想,这背后有一个更恒定的因素,至少我们看到,自商朝之后,中国的华夏不强调人种、文化的区别有多么重要,基本上大家更多在默认人性共通的东西,哪怕有些人和你语言不一样,无法互相交流,但学会了互相交流之后,就可以在一起融合、结婚、交流,甚至可以学习、考科举,从来都是如此。
郭建龙
:这个我同意,它是文化层面的现象,不是生理上族群的现象。
李硕
: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很严厉的宗教划分所造成的身份上的天壤之别,中国文化里从来没有过这个东西,这种情况在一神教里更明显一些。我想唱一下反调的是,也许我们认为人种等级平等的观念在价值上是正向的,但反过来看,也许更好的人类社会的进化其实可能和大一统观念是相反的。换个说法来说,我觉得
只要实行过超稳定结构的文明政权,到最后经济上都发展不起来,并会逐渐进入一种衰落落后的状态。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中国历史上所谓长期的封建社会停滞时期,2000多年来其实变化不大,我们一直进化不到现代工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