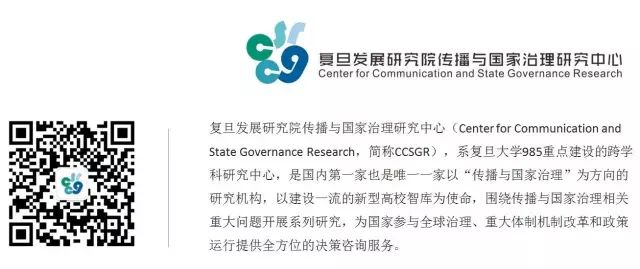欢迎点击上方订阅本公众号。
欢迎点击上方订阅本公众号。
导读
本文为CCSGR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级记者窦锋昌的《新的规制效果与规制模式转型研究——基于45起典型违法广告的分析》一文摘要,获取全文请参阅刊发杂志。
本文以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官方机构公布的45起违反新《广告法》的典型案例为素材,分析了新《广告法》实施后对违法广告的规制效果,概括出违法广告在违法平台、违法领域以及违法类型等三方面的特点。研究发现,新《广告法》延续了原《广告法》“政府主导型”的规制模式,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广告规制受到了互联网广告实践的强烈冲击,规制模式面临着从“政府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迭代的迫切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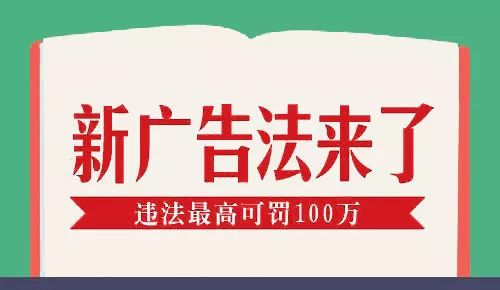
2015年9月1日,修订后的新《广告法》正式实施,经过这次修订,该法由原来的49条扩充到75条,文字由4600字增加到10000多字。新《广告法》颁布以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比了新旧《广告法》的异同,有学者以总体把握的视角指出了新法的创新之处,比如“四大亮点”“十大变化”等。
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产生于新法实施以前,而今新法实施三年有余,新法的规制效果如何?违法广告表现出怎样的特点?规制模式上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和迭代?借由此项研究,希望能够对这些问题给出尝试性的回答。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是新《广告法》实施以来官方公告的45起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上海市工商局公布的26起、江苏省工商局公布的10起、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9起。本文分析的框架包括违法平台、违法领域、主要情节、违法类别以及处罚结果,其中重点关注违法平台、违法领域以及违法类别三个框架。

通过对45起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广告法》取得了明显的规制效果,这些广告在违法平台、违法领域以及违法类别等方面表现出如下特点。
1.对广告主自有平台的处罚比例超过大众媒介
新《广告法》第2条区分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以及广告代言人四种广告活动主体。45起案件中,通过自有平台(自设网站、印刷品、店堂、网店、微信公众号等)发布的次数达到36次,而通过大众媒介(报刊、电视、户外、商业网站等)发布的只有16次(有些广告在多个平台发布,一个平台计1次),前者是后者的2倍有余。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通过自设网络平台发布的总次数是18次,通过印刷品和店堂等传统自有平台发布的总次数也是18次,自有平台中的新旧平台发布次数已经“旗鼓相当”。

2.特殊商品和服务是处罚的重点区域
新《广告法》对社会各领域的广告都有效,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所有广告具有同样的违法概率,若干领域经常出现广告违法现象,它们是违法重灾区,对这些重点领域需要做出专项规定。旧《广告法》仅规定了4类7种商品的专项广告准则,伴随社会发展,新情况不断出现,新《广告法》规定了9类19种重要商品和服务的广告内容准则。
这样的规制改变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20多年前《广告法》制定之时,房地产、教育、培训、招商、投资理财等领域的社会经济活动很少,彼时比较突出的是医疗、药品、保健品、烟草、酒类这几种类型的广告。20多年过去,中国人从原来的“温饱”时代步入“小康”时代,普通老百姓对房地产、教育、培训、投资理财等商品和服务产生了需求,这些领域的广告也大为增加,随之带来了大量的不规范行为甚至是违法问题。

3.违法类别:“虚假广告”和“用语不当”广告是两大类别
广告出现违法情形,最常见的原因是广告内容有虚假情形,但也有内容虽然真实但是因为用语不当被认定为违法的,这里就牵涉到违法广告的另外一个维度,即违法类别。违法类别指的是违法行为在法律上的类属和定性,违法类别直接关系到最后的法律处罚。具体到新《广告法》而言,违法类别主要包括虚假广告、违法使用绝对化用语、违法使用医疗用语、不公平竞争、以主管部门名义宣传等,其中,虚假广告往往会和其他违法类别有交叉和重叠。45起案例显示,虚假广告和用语不当在所有违法类别中最为突出,前者属于“事实错误”,后者属于“表达错误”。
总体来看,新《广告法》实施以来的三年间,各地监管部门有效查处了一批典型案例,显露出法律修订的成果。同时,新《广告法》在如今的新媒体时代还存在诸多不适应之处,比如虚假广告等固有的问题还持续存在,违法使用绝对化用语的认定标准不够明晰。更主要的是,伴随着广告发布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大面积转移,广告主体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原来清晰的行业分工变得模糊起来。
从根本上来说,45起案件所显示的广告规制效果对新《广告法》的规制模式提出了挑战。

我国《广告法》的规制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以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主,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为辅,这种规制模式虽然也强调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但是自律仅是促使行业遵守法律法规。在传统媒体时代,这种“政府主导型”广告规制模式是有效的。各地监管机构只要把本地的报社、电台、电视台纳入日常监控范围之内,就可以比较全面地对违法广告进行查处,因为在那个时代,广告发布者主要就是这些有限的平台,广告发布和新闻生产一样高度垄断,广告规制也处于相对简化的状态。
但是,2012年之后,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媒体平台迅速由专业化阶段进入到社会化阶段,广告也随之极大地分流。同时,包括广告主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体拥有了网站、网店、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终端,再加上原来就有的店堂、印刷品等发布平台,广告主和广告发布者的界限被打破了。此种情形之下,
“政府主导型”广告规制模式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

1.海量广告主体的冲击
在传统的广告模式中,广告主通常是有推销需求的客户,广告经营者是广告公司,广告发布者是媒体;而在网络时代,新的产业格局和新的媒介环境正在滋生和培育更多新的形态和业务取向的公司和新的组织方式、新的品牌、新的消费者定位。广告经营和广告发布的门槛大大降低,从广告制作、设计的角度来说,诸多网络广告形式,例如社交媒体中的广告,不再需要专门的设计和制作,简洁的文字加图片即可构成一则广告,一般的广告主自身完全可以完成。对45起典型案例发布平台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这种变化,新《广告法》相比于原《广告法》做出了很大调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自然人纳入到了广告发布者的范围之内,顺应了网络技术进步的趋势;二是在实际运行中,不要求自然人像大众媒体那样办理广告经营登记。这两处的修改无疑是巨大进步。
但是伴随着这种变化,广告主体从原来的有限化猛然间转变为海量化,几乎每个互联网用户都是潜在的广告主体,政府有限的执法力量如何规制海量的互联网广告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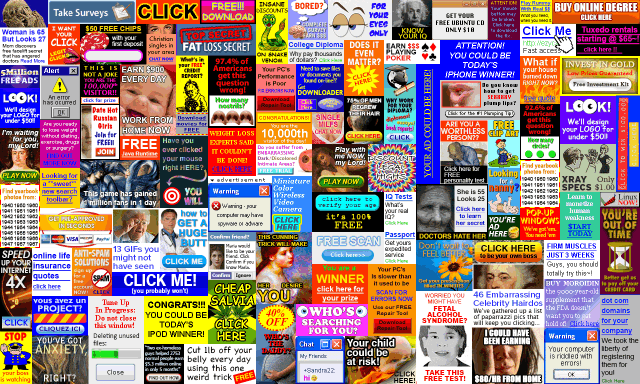
2.举证责任分配的冲击
打击虚假广告是《广告法》制定与修订的一个主要目标,新《广告法》实施以来,各地执法机构对虚假广告保持着高压态势,45起案件中有27起属于虚假广告。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何对虚假广告保持持续压力?这里就不得不思考执法机构的举证责任问题。前文说过,违法广告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事实错误”,一种是“表达错误”。对于后面一种,因为广告画面和语言有客观呈现,执法机构的取证和举证相对不难,但是对于“事实错误”也就是“虚假广告”而言,因为要证实广告表达与商家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对应关系,执法机构在取证以及举证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
在原《广告法》之下,执法机构承担广告真假的证明义务,在新《广告法》之下,这一点有所改变,部分规定已经吸收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FTC)的“广告证实”制度的思想,但距正式的“广告证实”制度还有距离。此种境况下,市场监管机构面临着很大的举证压力。
研究表明,举证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执法机构的积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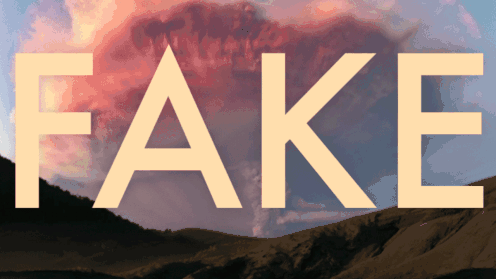
3.非法用语认定的冲击
广告制作是一门非常讲究语言使用的行业,打动消费者、让消费者记住自己的广告语是广告制作者极力追求的目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有些广告就要打“绝对化”用语的擦边球。45起案例之中,8起使用了“绝对化”用语,比例如此之高,需要反思新《广告法》关于绝对化用语的规定如何认定的问题。
新《广告法》禁止使用的“国家级”“最高级”“最佳”三个用语必须要禁,但是在现实的广告操作中,还有一批有相似含义的广告用语,比如“首个”“独家”“唯一”等是否要完全禁止?从“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推断,不能一律禁止,而是需要结合广告个案的语义、语境和事实依据综合判定。
要准确做出此类判断和认定,需要建立非法用语的全国性“词库”,要建起这样的词库,需要深入挖掘广告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力量,因为这些社会组织身处广告实践一线,对广告用语的使用有更加切身的体会和把握。

所谓“社会主导型”广告规制模式,有两层含义。第一,
以广告行业自律为主,通过加强由广告业各方共同组成的非盈利的行业自律审查机构的作用,规范广告市场竞争秩序、确保公正的市场竞争。
第二,
挖掘消费者个体对违法广告的监督和纠偏功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向违法广告主、广告经营者以及广告发布者寻求赔偿,让虚假广告等行为付出比较高昂的成本。无论是行业协会还是消费者个人,相对于享有公权力的市场监管部门而言,都属于社会主体,以社会主体主导的广告规制即为“社会主导型”广告规制模式。
不过,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倡导“社会主导型”模式,并不意味着降低政府机构在打击违法广告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政府的监管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算是在日本、美国等实行“自律主导型”广告规制模式的国家,政府监管机构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这里强调《广告法》的规制模式从“政府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的迭代无非是要强化社会主体在广告规制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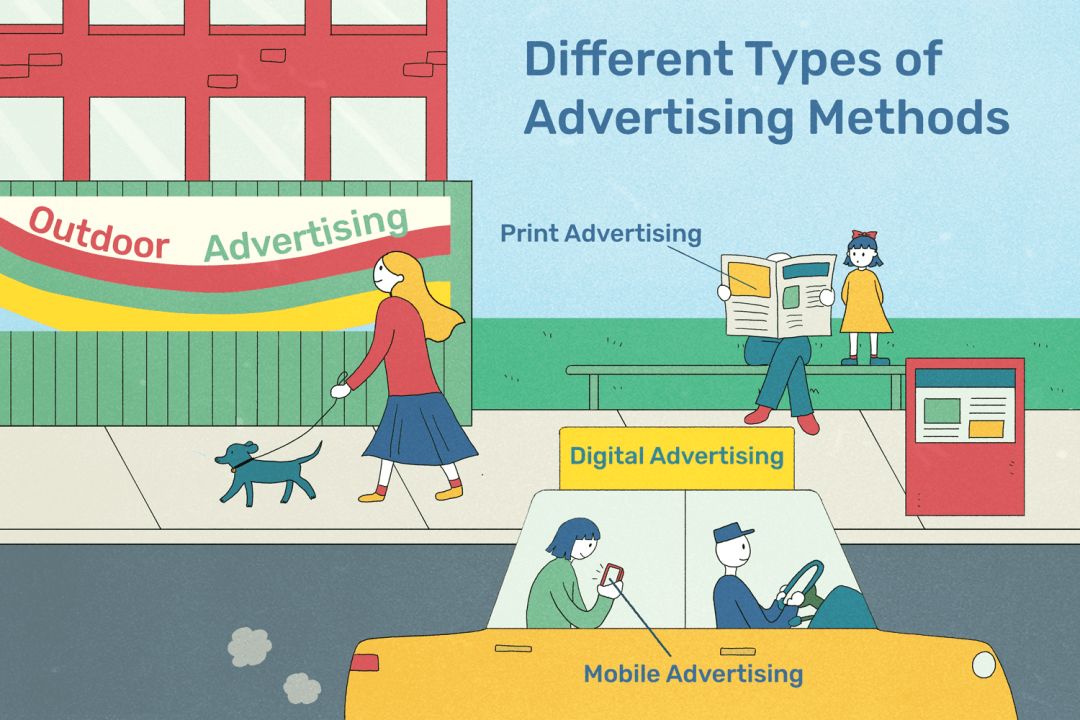
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多元广告刊发平台以及广告主体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广告业的形态和运转逻辑,有限的市场监管部门难以对海量的互联网广告行使监管职能。在这样全新的广告形态和业态之下,广告规制模式需要快速迭代,最基本的抓手就是激活行业协会和消费者这两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让它们和政府监管机构一起和违法广告做斗争,开展一场广告规制的“人民战争”。
虽然新《广告法》实施三年来在打击虚假广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实践中还是捉襟见肘,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广告法》只是原《广告法》的惯性延伸,两部广告法的基本假定广告发布依旧以传统媒体为主要平台,其规制模式是“政府主导型”。
作为一部调整商业信息流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关系的法律,《广告法》时时面临着来自于社会各方面的巨大挑战,《广告法》需要适度的弹性来应对这些挑战,特别是要适应互联网已经成为广告发布主阵地的现实。

事实上,作为新《广告法》的配套法规,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制定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已于2016年9月1日始施行,《暂行办法》的出台缓解了一些燃眉之急,但是因为它只是一部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很低,比如最高处罚额度不能超过3万元,不能解决新《广告法》内生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新《广告法》需要立足于互联网广告实践的更加彻底的修订。
(图片来自网络)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
高级记者
本文是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上海地区‘体制外’自媒体发展现状及应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17BXW002);复旦大学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重点项目“传媒融合的路径选择和方法——以上海为例”的阶段性成果。
本篇文章发表于《新闻大学》2018年第5期。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窦锋昌.新《广告法》的规制效果与规制模式转型研究——基于45起典型违法广告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05):109-116+15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