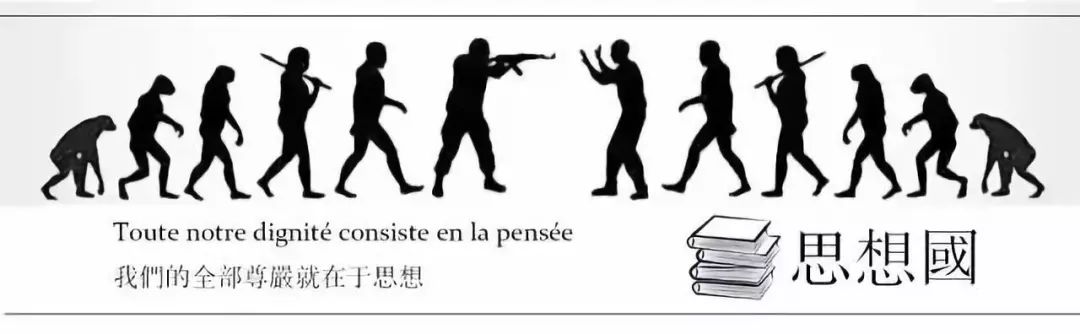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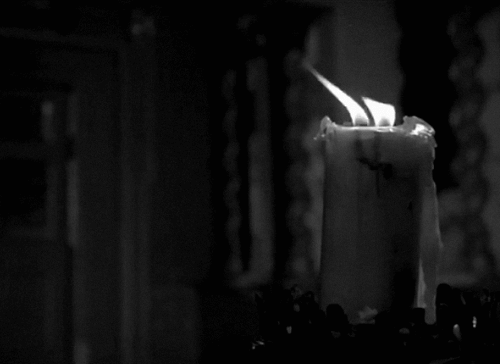
从盛夏到初秋,几次出行,感慨良多。
人类悲喜并不相通,有些合谋构陷时的卑鄙却是相通的。
此生何幸,人性中的光亮与黑暗,培云都见证了。一路所遇,有
善有恶,这就是他所热爱的人在人间的模样。
没有谁在绝望中饱受痛苦,唯有希望时刻折磨人心。今年在厦门做
讲座谈到:幸福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里不抱一点希望。
昨日早起,突然想到隔世而望 、隔日而生的邓丽君。世间尚有事物可以怀念。
若此生寻美之过往,承认并爱护,不可触摸与进入永恒了的虚无缥缈。
离开《南风窗》很多年了。除了在手机上写了十余万字,关于美、迫害的构成以及自我拯救……近两年很少再写东西了。近有昔日“同窗”约稿,虽诸事繁忙,盛情难违,匆匆写就以下短文,也算侧面补录了近月来路上的点滴。
愿有心继续生活并建设于此土地者,毋懈毋怠,作民之良。
以下为正文:《毋懈毋怠 作民之良——省锡中纪事》
前两年在牛津访学,花了不少时间在欧洲旅行,其中仅英国便走了东南西北四十余座城市。除了寻访雪莱、拜伦和莎士比亚的旧迹,还看了许许多多美术馆和博物馆。有一天,我突然抛给自己一个问题——你对中国的古老城市了解多少?为什么没有和在英伦一样的热忱去寻访?
过去这些年,因为外出参加读书会的缘故,北上广深自然没少去,但是还有很多心仪的古老城市,却一直未能成行。现在该做一些改变了。不能简单说是为了寻求一种东西地理知识上的平衡,而是在中国广袤的土地和古老的文明中,的确有一些特别的城市值得我去了解。
因了上面的自省与觉悟,2019年夏天《寻美记》出版后,我特地嘱咐编辑陈卓兄,这次各地书店、讲堂如有邀约,着重挑选去以前不曾去过的城市。就这样,平生第一次,我先后到了泉州、洛阳、开封和无锡等地。而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给了我许多收获,并且让我难免心生懊悔——要是早点来就好的。那样就会有不少新材料可以在过去写作某本书时补充进去了。
而这种感觉,在我抵达无锡后尤其强烈。有些细节,理应成为写作《重新发现社会》、《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等书时的重要材料,只叹当时孤陋寡闻或诸事随缘,未能及时发掘。
生长在被称为“吴头楚尾”的九江,旧称柴桑或浔阳,我算是地道的江南人。可惜大学毕业后多在北方生活。然而,我的心却一直在南方。除了年少记忆中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更怀念的是江南淅淅沥沥的雨水。从牛津回来后的半年内,我所在的北方城市滴雨未下。这样的糟糕天气让我的灵魂快干涸了。为此,有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周都会坐两次十小时的夜车,只为回到南方听雨。晴天让人走向外面虚无的世界,雨天让人回归自己真实的内心。我相信南方的斯文鼎盛是和雨水有关的。
一直以为对江南风物与文脉算是非常了解。2019年的秋天,先后在惠山书局、瑾槐书堂和省锡中做了三场讲座,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江南许多地方的根深叶茂依旧一无所知。虽然常叹“能不忆江南?”可我对于江南究竟了解多少?所幸,因为有缘在省锡中做了一次讲座,让我了解了这所学校厚重深远的历史,逃过一次“无知的后怕”。
由于面对的主要是高中生,当日除了简单分析真理与意义的区别,我着重讲了自己十六岁时所面对的人生五路向。讲座结束后,立即去了不远处的校史馆。省锡中的前身为始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私立匡村学校,创立者为实业家匡仲谋。徜徉馆中,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挥之不去。无论是办学理念,还是师生的精气神,都让我想起旅日造访过的北海道大学。在那里也有一个校史馆。晚餐的时候,我不无遗憾地和唐江澎校长说,若是来得早,提前看了匡村校史馆,再做讲座,今日主题恐怕要换成匡村学校与北海道大学了。如今北海道大学不复当年盛名,有一个说法却是,二十世纪初的日本走向,摇摆在崇尚自治、自由的北海道大学与崇尚扩张皇权的东京帝国大学之间。
我误打误撞,在大学念的是历史系。很多年前曾经听过一个说法,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而不是上帝。这种执念是许多西方人无法理解的。
一些信教者甚至傲慢地以为,没有上帝照料的中国人会为所欲为。那些人不知道,中国人的现世是时间,中国人的责任感是历史感。只要这一文脉不断,即使困顿于现实,终有迷途知返或柳暗花明的时候。
中国人崇尚源远流长,这种骨子里激情背后,不仅有对历史的敬畏,同样有对未来的敬畏。
真实发生的历史与某些被书写的历史常常判若天壤,正如我这几年所见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历史全无可信。读《省锡中校史资料长编》,让我感慨良多的是,该校创立之初,便极其注重小历史的记录。在1931年第二届中学毕业纪念刊中,有一篇《级史》的文章。“事无巨细,人无大小,必须有史,盖以过去之因果而测将来之得失也。苟无史,于人非噩噩无闻者流,即堕落不齿之伦也;于社会国家,则必文物荡失,典籍不传,精神涣散,一蹶不可振也。试观今帝国主义者之于殖民地,必先灭其文字。文字灭,而史不传。史不传,国亡而种灭矣!”虽然只是一个年级,但年级亦有年级史。三年同窗,转瞬风流云散。
旧雨重逢,未可预期。这里既有历史的态度,也有人生的态度。合在一起,就是钱穆先生所谓对历史该有的温情与敬意。
早先研读《大公报》,心中有一个谜团。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翌日,该报发表社评《日本投降矣》。社评开篇即引用了杜甫名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在八年苦战之余,得见这胜利的伟大日子到来,我们真是欢欣,真是感激,在笑脸上淌下泪来。”虽然被日本人害得颠沛流离,文章同时表达了对日本民众卷入战争的深刻同情。为什么当年的报人有那样的眼光与胸怀,而非淹留于民族仇恨?在我梳理匡村中学生的写作时算是找到了些端倪。
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由于中日时已交恶,许多人对此兴灾乐祸。在一篇题为《日本地震感言》的时评中,作者先是感叹了地震给日本带来巨灾,“伏尸数十万,而被房屋压伤者无算。其惨状,有不可言喻者。而子哭其父,妻哭其夫,相继狼狈于途。”继而对兴灾乐祸者提出批评。其一,中国同胞,如留学或经商者,面对此灾难,死伤者一定甚多。远在故国的亲人“想必食不知味,坐不安席”。其二,“日本虽屡无理于我,而幸灾乐祸、袖手旁观,此文明国所不为也。”
该文作者署名为黄月清,高三年级的学生。不知道这位学生后来命运如何。我承认,这位学生在我眼中的份量,远远高过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东林党人。
因为他瘦弱的声音里不只有党同伐异的低端政治,还有超越低端政治的人性与人情。
在离开无锡的高铁上,陈卓兄和我提到一个细节,看到现场有那么多学生排队签名,他原本想拍照的,却忍不住躲到幕后痛哭了一场。无论这些孩子将来变成什么样子,至少此刻都有着赤子之心。而我有时候宁可相信一个国家有怎样的中学就有着怎样的未来,而不是大学。以我自己的经验,一个人在灵魂上的关键性成长,主要发生在中学时代。陈卓兄是我几本书的编辑,北京人,现在准备到江南定居了,因为这里有读书人和他的江南啊。
在参观匡村学校校史馆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念念不忘。那是一份毕业证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学生陈明侯系江苏省无锡县人,现年十九岁。在本校高中普通科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依中学法第十二条之规定给予毕业证书。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