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覃里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ohistory
点此阅读本文上半部分
二、波尔图
天使喝掉的甜酒
在去到波尔图之前,我从来没有喝过波尔图酒,至少不记得喝过。到了之后,我才知道这种甜得腻人的加强酒,曾是英国人餐后常备,如今在大不列颠军队中(包括陆军,英国皇家空军RAF和英国皇家海军),正式场合都里还用它向女王祝酒。虽然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可能会觉得它品味不高,但英国人对波尔图酒庄的依赖却有了至少300年历史。自从1640年英国协助葡萄牙从西班牙重新独立,英国人就开始在波尔图得到了开拓酒庄的机会,正好1703年英法战争,法国酒被排挤后,不易变质的波特酒挤占了这块市场空白。
从里斯本到达波尔图,第一感觉就是松了一口气:城市忽然变得安静和宽敞了,街道上下坡度也缓了很多,修整的路不会硌人鞋底。唯一让人困惑的是,波尔图有很多非常可爱的涂鸦,风格动漫化,但每个涂鸦附近都会有尿骚味儿,就像它们代表了非正式的公共厕所一样。和里斯本一样,这里也有很多废弃的百年建筑,漂亮的树枝从窗框里伸出来,背景就是碧蓝的天,如诗如画。在河边上,我还看到了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牵牛花群落:它覆盖了一整片废弃的居民楼,至少有半平方公里。绿叶森森,紫色的喇叭花朵嵌满其中,偶尔露出下面的断壁残垣,真是奇异之极。
我们从圣若昂医院后面的老式公寓里出门,经过一群长期聚集在医院附近的瘾君子(他们在等待慈善机构分发的药物),沿坡而下,穿过杜罗河边餐馆外密集的游客,看一会儿成群结对从堂路易斯一世大桥上跳水入河嬉戏的年轻人,还有永久聚集在城市排污管口的鱼群,再从俊俏的河谷底岸爬上大桥,沿着电车轨道走过去,就会到达那些古老的波尔图酒庄。
770公里的杜罗河从西班牙发源,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最重要的水系。杜罗河谷在皮尼昂(Pinhão)和佩斯奎拉·圣若昂(São João de Pesqueira)周围地区被叫做“黄金河谷”,正是因为波尔图酒在这里诞生和繁盛,而欧盟“原产地名称保护”条例规定,只有这里诞生的波尔图酒才能打上“Port”或“Porto”标记。在葡萄牙境内,河谷的丘陵布满页岩,缺少土壤,夏季酷热冬季潮寒,这恶劣的条件倒是正好适合葡萄的生长。英国人自17世纪后期开始,在河谷下游开辟了满山的葡萄园,又在位于杜罗河出海口的波尔图搭建了密集的酒庄。
波尔图市内靠近路易斯一世的大桥下,各家古老的知名酒庄还各自留着一艘当年运酒的木船,纪念那些船艘如云往来不息的贸易黄金时代。船上的名字如今都是享誉全球的波尔图酒品牌:科伯恩(Cockburn),克罗夫特(Croft),陶氏(Dow),古尔德(Gould),格雷厄姆(Graham),奥斯本(Osborne),欧福雷(Offley),桑德曼(Sandeman),泰勒(Taylor )和瓦勒(Warre),全都是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姓氏。这些成功的商人们在这里组织的英国绅士俱乐部,如今自然不存在了,葡萄牙人、德国人和荷兰人也逐渐拥有了一些酒庄。
我们拜访的是泰勒Taylor酒庄,1692年始创,如今拥有Fonseca, Fonseca-Guimaraens, Taylor和Croft四个老品牌。酒的酿制方法基本沿袭了传统,虽然由青年男女脚踏葡萄的环节,如今慢慢由机器取代了——说真的,看着纪录片里年轻男女一对对挽起裤脚在葡萄上跳舞的场景,虽然很是浪漫,但总让人隐隐担忧,脚丫子会不会给葡萄酒里掺进点儿不必要的真菌。所以看到现代大型榨汁机运作的时候,大家还是松了口气。我也学到了一些基本知识,比如杜罗河谷不同地段的气候,会产出不同的葡萄,酿出的酒也各有长处;比如酿酒的过程中要加入白兰地酒,让糖分不会充分发酵,保留甜味儿。

在酒庄里还有一只巨型酿酒桶,装了大约13万3000多瓶量的酒,像个贪吃的大型动物在休憩。幽暗的酒窖里充满略带生味儿的葡萄皮和木头混合着酒精的气味。在酿酒过程中,有超过2%的酒会透过大木桶挥发掉。这部分挥发掉的酒,葡萄牙人调皮地叫它“天使份”(Angels’ Share),设想一下天使们把酒偷走,而人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场景,何其融融。
虽是人间和天使共享乐趣之地,这些酒庄也曾遭受战争的考验。1807年11月,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葡萄牙,作为敌对国公民的英国酒庄庄主们面临监禁和洗劫,匆忙带着酒和家人逃回英国。但幸运的泰勒酒庄有一名土耳其裔美国雇员,名叫卡莫(Camo),留在雇主身后照看生意。因为他中立国公民的身份,法国军队没有碰泰勒酒庄一根毫毛,他后来也把酒庄完璧归赵。为了感谢他,泰勒酒庄多年来一直出产一种名为卡莫的波尔图酒,以纪念他的贡献。这是一个关于移民、信任和忠诚的好故事,在这个逆流转向封闭的时代,也不知多少人听得见。
模仿与沉默
葡萄牙遍布东西南北半球的殖民地,为什么没有为它的文化留下更多鲜明的印记?我们在苏亚雷斯(Soares dos Reis)博物馆里还在想这个问题。苏亚雷斯博物馆的前身是葡萄牙美术和印刷博物馆,1833年由佩德罗四世下令建立,是葡萄牙第一座面对公众开放的艺术博物馆,诞生于“自由主义运动的光环下”,1911年后以著名雕塑家安东尼奥·苏亚雷斯(António Soares dos Reis)的名字重新命名。
博物馆安置在一座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城堡里,看起来很需要修缮。所有的艺术家名字我们都不认识:席尔瓦-波尔图,马尔克斯-奥利维拉,阿图尔-罗雷罗和恩里克-泊桑……或许因为我们的孤陋寡闻,也或许因为这些名字从未开创过什么先河。如果单看这里的展品,会觉得葡萄牙艺术家们在过去三个世纪里一直在试图追随欧洲的艺术中心成就,尤其是意大利、荷兰和法国,模仿得水平很高,但是总是慢了半拍甚至一拍,从荷兰弗兰德斯绘画的光影炫技,到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地下展馆里,当地美院学生的毕业展依然还在老老实实地抄袭达利和毕加索。

是因为居于欧洲边缘导致的不自信模仿,束缚了他们开拓的潜力吗?是这种不自信,使他们没有能像英国和西班牙一样更自如地探索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与前殖民地的关系吗?这些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在里斯本的热罗尼莫斯修道院,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记录中对殖民地的忽视:巴西、澳门、果阿、安哥拉、几内亚、马六甲市、莫桑比克……这些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对葡萄牙的影响似乎并不多,除了随处可见的巴西式巴洛克式的建筑和受中国影响的手绘瓷器。
大作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们聚焦于欧洲大国或者内心世界,但却对殖民地的记录和发掘却远不匹配。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追随欧洲中心的追求,使他们对自身的广阔视而不见;另一些人的记录,却似乎没有能树立一种更深刻而现代的视角,如今也难以传播。殖民地诗人、巴西教士杜朗(Santa Rita Durão)的史诗《卡拉穆鲁》(Caramuru)这样的本国知名代表作,是关于一个美化的葡萄牙殖民官员如何与巴西人相亲相爱的故事。
但是波尔图毕竟有一个全球知名的文化地标,那就是Livraria Lello书店,“全球最美的书店之一”。但它的真正出名,是在电影哈利波特把它作为取景地之后。自此它那画着佩索阿的售票亭外,永远排着十几米长的队伍。我们也挤进了闷热的书店,要不是人多得氧气稀薄,那些雕着轮状花纹的天花板、修道院一样的走廊拱顶、教堂尖顶窗一样的书架和神话宫殿一样的分叉木制楼梯还是很让人惊叹的。书店门口摆着佩索阿的诗集和哈利波特全集,很多中国同胞在四处拍照。一个20多岁的中国女孩向同伴激动地大声宣诏:“我要买一本哈利波特!”听起来,买书对她而言是件不寻常的大事,估计店里许多其他客人也差不多。
位于大桥上方山顶的圣柱圣母修道院很小,但因为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和河谷,风景醉人,也是游客常来的地方。这个修道院建于16世纪,属于圣奥古斯丁骑士团,它的圆形教堂是模仿罗马圣母大殿设计的,在建造它的72年时间里,葡萄牙被西班牙征服,于是修道院里接纳了一个西班牙圣人“圣柱圣母“。在1832年波尔图被拿破仑军队围困的时候,修道院有利的地形使它成了一个临时堡垒。20世纪初,它被用来当做军营,现在还有一部分不对公众开放。
或许因为修道院的后院太过简朴,圆形的庭院里没有其他游客。我独自在圆形回廊里游荡,在其中一个敞开的石室里,发现了葡萄牙第一位国王阿尔方索一世(Afonso Henriques)手持长剑的雕像。这个12世纪的开国之君是在击败自己母亲的军队之后登上王位的,他后来还击败了来自阿拉伯的摩尔人,被敌人尊称为“葡萄牙人”。
在静得出奇的石室里和高大的雕像对视是个奇妙的经验,我想象着他怎样披着长斗篷劈砍过阵。太过安静的环境激发了幻觉,8个世纪消失了,雕像似乎活了过来,要踏下高台。我连忙转身,在门旁的墙上发现一块石头门楹,上面刻的字已经被风雨消磨大半:“我细看,也聆听。我遭受折磨,并保持沉默。只为那个能找到自我的时刻。”这句话和东方哲学多么相似,然而也是基督教精神,归根结底,是所有人直面命运所需的信念。但沉默,沉默是葡萄牙的关键词,阿尔方索的石室提示了谜底。
在去往辛特拉的前一天,我们离开波尔图,在大西洋海岸的Granja小镇停了一个下午,小镇海滩上有一个盖亚海岸沙丘植物公园,沙滩上木板铺就的观光道两旁长满肥硕美丽的沙地植物,很多我都没有见过。大西洋海岸的风浪一直比较大,是冲浪的好地方,但那天下午柔和平静。大小不一的黑色岩石伸出海水,上面附满了各种贝壳、拇指大小的鲍鱼、成群出现的海蜗牛、焦糖布丁一样的半球形透明海藻(使劲儿一挤就从中心吐出一簇触须),水里暗绿的海草像头发一样柔顺地招摇。在岩石之间看见海水折射的幽深光芒,让人觉得美人鱼一定会在黄昏时出现,或许还会悄悄越过公园和铁路,爬到安静的小镇上,在那些19世纪的别墅门外紫色鸢尾花丛里偷看。在这个不知名也没有找到什么故事的小镇,我第一次感到纯粹的、无忧无虑的愉悦。
三、辛特拉
疯狂的秘密花园
古镇辛特拉是大里斯本行政区的一部分,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在离开波尔图,到达辛特拉的时候,里斯本仿佛就已经很遥远了。记忆压制了记忆,就像树叶覆盖了腐殖土,终将变成白垩土,在运动的碾压中碎散。旅途里的噪音和热度也是逐步减弱的,里斯本热浪席卷的铁桥与飞机轰鸣、有轨电车的尖叫和汽车喇叭,到波尔图就弱化成了间歇的马达喘息,夜里甚至可以幻想江上桨橹之声带来的清凉。而辛特拉更加深了一层宁静,离开游人聚集的主路,就是静谧的山林,远处大西洋的默默闪耀,山上骑警的马蹄,挟满山花香的夜风甚至有几分冻人,需要夹衫才能罩得住。
所以辛特拉历来是葡萄牙皇族和欧洲名流的夏日度假胜地,甚至生在巴西的殖民大亨也要回到这里来避暑,“躲开里斯本的热浪和臭气”。这里的山脉自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居住,被埃及法老托勒密命名为“月亮之山”。罗马人、摩尔人都曾在山间建造城市。我们居住的波西米亚小旅馆就在山上,旅馆的花园占了一大片山坡,开满紫色的百子莲(英文名叫做“尼罗河的百合”)。一排百年老树俯瞰着日落时分的山谷,温暖的风这里摇摇树叶,那里摇摇花朵。
接近黄昏的时候,我们沿着山间公路走到市中心寻找餐馆,忽然看到山坡上茂密的古树间露出一道雕琢精细的石廊,旁边的铁栏杆后面,隐约是一座不寻常的城堡。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爬上山坡,找到了雷加莱拉庄园(Quinta da Regaleria),没想到一整个上午和中午都没能走出去。我们不情愿地被它迷住了,向两个傻瓜一样,不时嘟哝一句:“不可思议!”
很难向没有亲眼见过雷加莱拉庄园的人描述眼前的场景,它就像电影里《指环王》的精灵居所再现。庄园里的建筑群把罗马、哥特、文艺复兴和“后曼纽埃尔”风格杂糅重组,加入了从古希腊神话以降神秘主义传说的意象。亭台楼榭借山体高低错落,繁复精巧的程度,让里斯本的热罗尼莫斯修道院(也就是曼纽埃尔风格)也相形失色。有时这些意象随意得让人发笑,比如四个狗头凑成一堆。但更多的时候它令人惊叹,因为它实在独特而丰富,打破了所有的风格和禁忌,却又保持了某种均衡的韵律。

4英亩的庄园固然宽阔,但两个最重要的建筑却拉升了它纵向的空间,增加了虫洞一样的维度。一座27米的雕栏深井(以及另一个未及完成的井道),像往地下延伸的高塔,旋转的印度古水井般的石级,通向贯穿花园的地道;而最大的建筑雷加莱拉宫高耸的尖塔顶上,只有模仿炼金师的主人持有唯一的钥匙。
这个主人名叫卡瓦尔霍∙蒙塔伊洛,是一位在殖民地巴西诞生长大的咖啡和宝石巨商,也是一名昆虫学家、书籍爱好者和收藏家。网上英文资料里,关于他的生平记录不多,我们只知道他通过继承父母遗产和成功的生意积攒了巨额财富,终于可以离开巴西回到葡萄牙。他在葡萄牙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科英布拉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1892年,他从雷加莱拉女子爵那里买下这座庄园,用来实现他庞杂而惊世骇俗的幻想和理念。从1898年到1912年,他先后雇佣两位大建筑师完成了这座庞大的花园,主体部分建筑是1904年到1910年之间完成的。
显然,他雇佣的第一位建筑师没能够体会他的梦想,所以他又雇佣了另一位意大利人,路易吉∙曼尼尼。这位并不是建筑师,而是个舞台和剧院设计师,这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和蒙塔伊洛心意相通:最戏剧化的建筑想象,是必须通过幻想的舞台背景来实现的。曼尼尼用炼金术、石工术、十字军圣殿骑士团、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的元素,嫁接在各种建筑风格里,设置了一个立体的大型舞台:宫殿、高塔、小教堂、公园、地道、深井、湖泊、喷泉、亭台、长廊、马舍,甚至还有一个水族馆。蒙塔伊洛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或者是这场大型戏剧的导演,在这里,异教徒的狂野想象、冒险家的丛林和海洋历险与基督教和神秘主义的神圣肃穆都结合在一起。他不受任何流派和教派的约束,他要收纳人类一切最隐秘的知识,无论是向天堂还是地狱。
这种无拘无束的想象和自信,或许只能来自于帝国边缘,财富和现代性的扩张也支撑了这种可能。今日辛特拉的大多数建筑建于19世纪,粉色、黄色的多装饰别墅充满了这种被称为whimsical(随心所欲突发奇想)的特点。殖民和贸易的财富夸大了这种特点,就像一群百科全书式教育长大的富有孩子肆意购买最精美的玩具。但是蒙塔伊洛的想象如此丰富、内容如此宽广深远、对美学的追求又那么专注,使它超越了普通新富的粗鄙炫耀,而成为可爱迷人的nerd世界。
1942年,庄园被卖给一位私人买主作为住宅,1987年又被日本Aoki公司买下,整整十年花园大门紧闭,直到1997年辛特拉镇委员会把它重新购回并修缮。从1998年开始,它才对公众开放,葡萄牙文化部把它列为“公共利益财产”,我们才得以见到这座19世纪葡萄牙浪漫主义狂欢的产物。
在城堡里,我们穿过许多装饰着大理石、金丝绒帷幔和满壁徽章的房间,每一个落地长窗和阳台外,都能看到绿荫深邃的山脉和古树。但最让我着迷的是一间灯光极为黯淡的小房间,走进去时颇为恍惚,只见穹顶上希腊女神壁画旁电灯的微光,但定神下来仔细打量,却忽然发现自己站在一块玻璃上,四壁是高耸的书架,大约有7米高,而玻璃底下也是同样深入地底的书架,我们竟然漂浮在图书馆的空中!再仔细一看,底下的书架其实是个幻觉,不过是镜面的反射。这或许就是博尔赫斯想象中的天堂图书馆吧,肉体在这里失去了重量,无穷无尽的书籍把追求知识者引向永生。
从庄园里出来,又到了吃饭时间。我们找到一家小路旁的拥挤餐馆,在斜着的小餐桌上点了烤猪扒。胖乎乎的餐馆主人大约60来岁,可能有呼吸道的病,但是喘着粗气忙里忙外,一刻也没歇着,热情又很有尊严。他非常为自己的菜娇傲,一顿饭里询问了好几次:“味道怎么样?”我很诚恳地说:实在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烤猪扒。事实上,伊比利亚半岛的猪似乎的确是最好的猪,新鲜香嫩,完全没有北部大陆上那些同胞的粗糙和腥味。而这家餐馆,是我们找到的唯一一家不会把肉烤糊的家常餐馆,让我们终于吃出了葡萄牙猪肉的美味。
摩尔人的长城
第二天,我们向更高的山顶爬去,去到摩尔人搭建的城堡。在路上经过许多迷人的庭院,其中一家门外居然挂着安徒生故居的招牌。1866年,61岁的童话作家访问了葡萄牙,他是这样记录辛特拉的:
“毫无疑问,葡萄牙最美也最受赞誉的地方,就是辛特拉。拜伦把它叫做‘新天堂’。葡萄牙诗人加列特称颂‘春天的宝座就在这里’。我们正在去往它的路上……据说每一个外国人都能在辛特拉找到自己的祖国。我在那里找到了丹麦……风景无限变化,充满生机。月桂树结着深红的果实,天竺葵茂密丛生,吊钟海棠竟长成了树……通往山顶的路上有一个花园,自然和艺术相映成趣,那是你能想到的最美的路。”
那就是通向摩尔人城堡的路。摩尔人城堡是阿拉伯帝国时期的穆斯林在8世纪到9世纪时建成的,那个时代被称为“伊比利亚的穆斯林时期”,但1147年,基督教军队就夺得了控制权,当时,摩尔人要塞脚下的山还是荒秃的。令安徒生着迷的山岭植被并不是自然造化的结果,而是浪漫主义催生的人造景观。除了几个世纪的贵族皇室对古树的保护之外,还有不少引进的外来植物,模仿的是英式园林的自然美:尤加利树、松树、相思树、夹竹桃、杜鹃花……19世纪40年代,女王玛丽亚二世的德国丈夫费尔迪南,还在另一座山顶上花巨资建造了中世纪风格的避暑名胜佩纳宫和它美丽的公园,我们没有来得及去看。

辛特拉的贵族和王室热爱英式花园,英国人也一直热爱辛特拉,因为这里的绿地和多云的山脉让他们如回故乡。“哦!辛特拉这伊甸园般的神作,山丘和谷地如迷宫一样斑斓多变。”诗人拜伦在1809年的休假之旅后写道。不过,现代英国人对此并不买账,英国旅行记者克里斯托弗·萨默维尔(Christopher Somerville)对佩纳宫的第一印象是“吹大了”,他回忆起一个事实:费尔迪南不就是打造德国新天鹅城堡的那个疯子路德维希二世的亲戚吗?“疯狂”是辛特拉的关键词,它实在太特殊了,就像低调的葡萄牙人忽然迸发的一些大笑和呓语。
摩尔人的城堡是建立在巨型山石上的小石头长城,它看起来实在是太像长城了,以至于我怀疑阿拉伯人曾经向蒙古人窃取了中国边疆的情报。我们爬上悬挂着摩尔人和十字军旗帜的墙头,牛奶一样浓厚的雨雾就从大西洋上涌了过来。大洋、船只和士兵都被遮住了,这正是十字军进攻的好时机吧。但是事实上,摩尔人并没有血战死守。在了不起的“葡萄牙人”阿尔方索一世征服里斯本之后,城堡里的穆斯林就自动缴械投降了。阿尔方索把城堡交给30个住户看守,给予他们居占城堡的特权,这里建起的教堂后来还成了重要的教区。
不过,今天攻占城堡的,也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了。从山脚下各大餐馆打出的中文的大招牌来看,这里的中国游客也是主力军。“漂亮的菜呈给漂亮的女士!”在一家中文大字写着“牛肉、猪肉、烩饭”的餐馆招牌旁边,年轻的侍应生给两位年轻女孩努力献着殷勤。放了醋的辛特拉本地土豆炖猪肉块非常不错,切成小方块的土豆和猪肉都略煎过,咸酸味恰到好处。倒是牌子上看着诱人的“香菜炒大虾”非常糟糕——虾子可能已经登陆半年了,很可能还从深冻箱里偶尔出来散过步,大约就是在侍应生调情的时候。
大烟囱和闯入者
镇中心的广场旁就是辛特拉的国家宫殿,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两根巨大而怪异的烟囱——上小下大,活像两根肥白的巨型萝卜,或者像倒扣的白色漏斗。“太胡来了。”L带着无奈的笑意说,他决定留在宫殿外面看书,让我去完成游客的必备项目。

国家宫殿最早是10世纪摩尔人建成的另一个城堡,12世纪被阿尔方索一世占领。但是15世纪开始的重建把城堡完全变了样。原先的遗迹基本抹去了。直到19世纪,葡萄牙国王都曾在这里居住。宫殿诚实地留下了历史记忆,结合了摩尔风格(瓷砖绘画和窗口)和曼纽埃尔风格(装饰石雕的门廊),还专门有一间简洁而充满几何图形的“阿拉伯房间”。宫殿里没有对旧日敌人的丑化宣传,只有对英雄和征服的歌颂,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
在这里,国王们不仅度过酷暑,也曾被监禁。精神不正常的阿尔方索六世,在被他的弟弟佩德罗二世驱逐出皇位之后,就软禁在皇宫里,从1676年到1683年,直到死亡给了他最后的自由。
虽然已经被两周的宫殿、城堡和博物馆之旅喂饱,国家宫殿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特别的印象。除了每一个拐角如诗如画的窗外山景,它内殿的装饰也非常有特色:喜鹊大厅,天花板就画满喜鹊;天鹅大厅,天花板就画满天鹅;纹章大厅,镀金的天花板就画满了带着不同家族徽章的武士。那可是在安迪沃霍尔之前两个多世纪的作品!
皇宫里还有一个“中国房间”,陈设着澳门参议员送给玛丽亚一世女王的礼物,一个结构繁复、大约一米高的象牙塔,和一座象牙中国楼台和庭院。这个塔是不是也激发了博尔赫斯的想象呢?清代服饰的小人站在阳台上和大门前,门匾上歪歪扭扭大书三个字:淮阳王。据说塔的原料大部分是象牙,小部分是骨头,雕刻也的确费功夫,但门匾上难看的字暴露了一切:糊弄一个远方的外国女王,字嘛随便刻刻就好了。
在一个小厅里,一幅油画吸引了我的视线:难道我看到了一个异装癖的耶稣穿着“维多利亚的秘密”牌睡衣,抱着一头小羊驼吗?凑近旁边挂着的说明,我才发现画上穿着蕾丝边真丝吊带睡衣的人物,原来是施洗者约翰,所以他抱着的应该是一头代表纯洁德行的绵羊,而不是小羊驼(动物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看法),然而黑色蕾丝边吊带幽蓝真丝睡衣却着实是太逼真了。画家名叫弗朗切斯科·弗朗西亚(Francesco Francia),来自16世纪的意大利,他只活了27岁。英年早逝,或许他过于超前的想象力,让他和时代格格不入呢。
厨房自然要去的,那两根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大烟囱,从厨房里面看竟然有壮观的工业美感,白色的墙高耸如云,下面挂着一排漂亮的黄铜大锅,非常有气势。唯一的问题:不知道下雨的时候,厨师们是不是需要打一排大伞,因为向蓝天敞开的烟囱口正对着灶台。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
我带着困扰,在博物馆的商店里闲逛,竟然在二楼找到了一个免费阅读室。我翻了翻那些架上的册子,找到了葡萄牙国家诗人卡缪的介绍。诗人曾经从首都被放逐,他借此游遍了葡萄牙衰落中的帝国,开始一场传奇的经历:在摩洛哥当兵的时候瞎了右眼,在柬埔寨从一场海难里逃生(但是没能救出他船上的中国情人),在莫桑比克花光了所有的钱,最后幸得历史学家朋友蒂欧格·都·科托(Diogo do Couto)的资助,回到里斯本,从此转运,发表诗集并得到塞巴斯提奥国王的资助。我翻阅了几首他的十四行诗,除了无数为追求“可爱的女士”写成的情诗之外,对故土的思念也颇为动人:“温柔的塔霍河水,宁静地流淌/穿越绿色的田野,越是流淌,越是清新……命运已经强赋我这哀伤的告别/只为把我的快乐变成绝望/这哀伤的告别压着我的岁月/它们悲诉着,渴望着你/我只有叹息着闯入远方的空气/让我的泪水打扰其他河流的安宁”。
回到旅馆,日落前再沿山路向上散步,闯入了雷加莱加庄园坡上更高的空气。在那里我们见过一个风景极美的法式公园,旁边的栏杆里有围满粉紫色大绣球花的网球场,和一个更大的花园。我好奇地到处寻找入口,发现这是一家酒店的后花园。提沃里帕拉西奧酒店(Tivoli Palacio de Seteais),一座18世纪的宫殿改造的酒店。华丽的大厅里挂的巨幅挂毯织有贵族狩猎图,看起来和那副漂亮的花卉油画一样,是18世纪之前的作品。从大理石台阶下行至后厅,就找到了花园入口,一座柔美细腻的大理石少女雕像正对着门,门外就是俯瞰海岸和绣球花园的露天酒吧。
L对我的长驱直入惴惴不安,这个花园看起来太像私人会所了。我还受着卡缪的迷咒,旁若无人地带他在迷宫一样的法式花园里走了一圈,坐下来读了一会儿葡萄牙诗集,顺便听邻桌快乐的英国商人谈论新买的两英顷地上面有哪些树——他们的声音实在太大,大笑的时候还前后晃着避开障碍物,偷看我们的反应,不参与微笑是不礼貌的。
这时候,很有姿势和腔调的经理送上了饮料单,上面用华丽的语言讲述茶的精妙之处,提供了大约十来种茶,这殖民时代的腔调,大约也是住店客人喜欢的体验。
但我不想喝茶,我想要奶昔。 “水果或者冰淇淋是什么意思?有哪些水果口味?”我问。
“什么水果都有,要什么有什么!”经理挺起胸脯说。
太好了,我一整个夏天都在想吃地中海的无花果。“无花果有吗?”
经理毫无遮掩地愣住了,我们忍不住笑出声来,这让他的面子非常挂不住,转身去问了厨房。无花果自然是没有的,“只有干的”。这次他把有限的几种水果数了一遍,带着点儿恼火。
我选了木瓜奶昔。
他转身离去之前,似乎是无意地问了一句:“你们是酒店的客人吗?”
“不是。”我们略带羞愧地说,两个闯入者暴露了原形,经理胜了一回合。他满意地走了。
奶昔的牛奶不是新鲜的,葡萄牙人似乎不常喝新鲜牛奶,而多用盒装奶,闷人的粉末味。不过在大西洋岸上金色的花园里,闯入者已经很满足了。
太阳下山的时候,宫殿酒店门口亮起橘色的灯,宫殿优雅的剪影衬在粉红的天空里,越来越远。北方和现实等待着,葡萄牙的隐秘花园关上了门。我转过身来,感到徒劳无力,明日的世界正在像巨轮一样翻转,它轰隆的声音震动着大地。
梦游者的结语
两次深浅不同的游历,葡萄牙好像一直留在在窗外,我只是伸手触到了它废弃别墅里的无花果枝,毛茸茸的绿色芬芳像无解的谜题。一个梦游的外国人怎么可能在两周之内穷尽这个沉默的谜呢,就连葡萄牙人自己也不能。桂冠诗人索非亚·德·麦罗·布雷纳(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resen)的《里斯本》,画出了它不可捉摸的灵魂。这首诗用葡萄牙语和英语、法语篆刻在在里斯本山顶公园的石板上,我尝试把它的英文版翻译成中文,作为两场葡萄牙行程的结语:
“我说:‘里斯本’/当我从南方抵达,并越过河流/当城市舒展开来,有如从它的名字里降生/它展开,升起在它无边无际的夜晚/在它的湛蓝和河流的漫长微火中/在它诸多山丘坚硬的身体里/.../里斯本,携它存在又不存在的名字/和它的惊诧无眠、它破旧木屋的蜿蜒/还有它隐秘的剧院,闪烁不定/它面具般的微笑,惑媚而心照不宣/当广阔的海洋向西延展/里斯本摇曳着,像一艘帆船/里斯本冷酷地建造着,在它自身的空洞之旁。 ”
(本文将收入作者的文集中,该书即将由巴比伦图书与中信出版社联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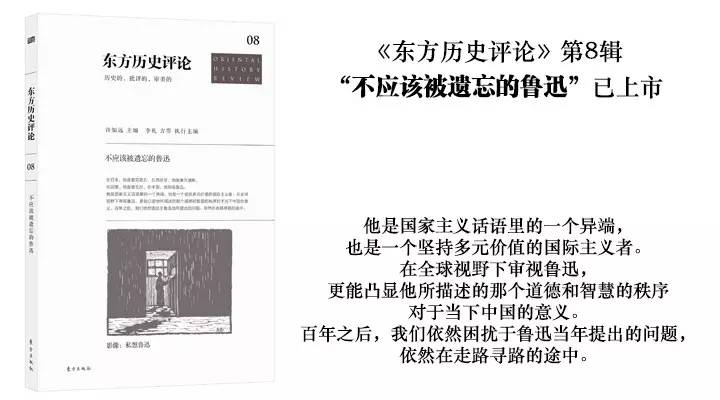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
|
李鸿章
|
鲁迅
|
聂绀弩
|
俾斯麦
|
列宁
|
胡志明
|
昂山素季
|
裕仁天皇
|
维特根斯坦
|
希拉里
|
特朗普
|
性学大师
|
时间
|
1215
|
1894
|
1915
|
1968
|
1979
|
1991
|
4338
|
地点
|
北京曾是水乡
|
滇缅公路
|
莫高窟
|
香港
|
缅甸
|
苏联
|
土耳其
|
熊本城
|
事件
|
走出帝制
|
革命
|
一战
|
北伐战争
|
南京大屠杀
|
整风
|
朝鲜战争|
反右
|
纳粹反腐|
影像
|
朝鲜
|
古巴
|
苏联航天海报
|
首钢消失
|
新疆足球少年
|
你不认识的汉字
|
学人
|
余英时
|
高华
|
秦晖
|
黄仁宇
|
王汎森
|
严耕望
|
罗志田
|
赵鼎新
|
高全喜
|
史景迁
|
安德森
|
拉纳・米特
|
福山
|
尼尔・弗格森
|
巴巴拉・塔奇曼
|
榜单|
2015年度历史书
|
2014年度历史书
|
2015最受欢迎文章
|
2016年最受欢迎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