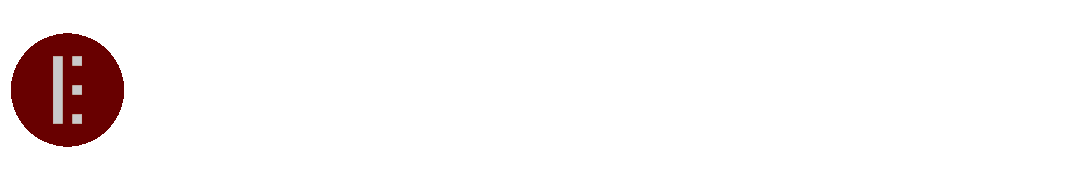EXTITUTE|批评·家
|
理论与历史碰撞/个例与议题交织
文|
黄清怡
/
责编|yy

本文主要讨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俄罗斯的先锋派电影,在欧洲的社会思潮和先锋艺术运动的语境中,梳理电影创作者对于蒙太奇手法和电影媒介的探索和实验,并考察创作者关于电影蒙太奇的理想和观念,最后借助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视角,反思电影和蒙太奇的可能性。
论文意在说明,蒙太奇运动中的主要人物维尔托夫和爱森斯坦看似对立的新闻电影和艺术电影两个路线,实际上折射出了美学-政治这一问题式中的两个重要话题,即传播与经验结构;而对于电影的批判研究则在更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引出了这种新的媒介所包含的复杂可能性。
开篇第一节,作者尝试借用蒙太奇理念将庞杂历史有线索地书写成“电影式”的历史景象,在意图明确而非泛泛的论述中,“先抛出一个俄国罗斯先锋派电影超越于个别图像的整体意象,再仔细地去拆解、分析它的样貌”。本期推送的内容为论文的第一章第二节,
由于俄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文化和艺术领域取代了过于危险的经济和政治领域,成为了各种观念进行角逐的唯一真正战场。而俄国当时的机器相对于西欧还很原始,因此俄国未来主义者眼中的机器是更具有社会建设性的机器。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艺术面临了更加实际的社会使命,俄罗斯的先锋派也发展出了两个不同的方向,所谓“白色人文主义”和“红色煽动”,也可以用艺术史上更为通行的“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来理解。前者,力图找到一个最小但实在的支撑点,后者,把沉思中的构造转化为现实生活的组织。不过,他们的计划又是超越于某一特定政权的。

《电影眼睛》
kino-eye
|维尔托夫|1924


俄罗斯先锋派电影与蒙太奇理论|2020

第一章 俄罗斯先锋派电影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艺术
不管怎样,俄罗斯先锋派的艺术实践有力地回应了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具冲击力的一个事件,也就是十九世纪以来工业技术对于生活的侵入。
世界作为与上帝意志对应的完满造物这一图景被打破了,艺术家模仿“客观”世界以接近上帝意志的使命随之剥落。[1]先锋派相信这种坠落是无可挽回的,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家已经遵循了尼采的信条:“坠落的东西应该要再推一把”。[2]
而俄罗斯艺术家在一个剧变正在发生的时代和国土之上,也做出了自己的行动。还有一个因素也影响着俄罗斯艺术的发展方向,就是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政治性的内容难得自由,而与政治无关的琐碎题材也遭到反对或禁止,因此,公众的注意力就集中到了在形式上具有实验性的作品上来。而且,文化和艺术领域取代了过于危险的经济和政治领域,成为了各种观念进行角逐的唯一真正战场。[3]
这段时间,被以赛亚·伯林称为“苏联艺术的孵化期”,其间,马雅可夫斯基、马列维奇、罗钦科等诗人、造型艺术家和戏剧家做出了各种令人惊讶、充满幻想的艺术作品,年轻的维尔托夫和爱森斯坦,或许那时还未被称作“电影导演”,也进行着开创性的艺术实验。

[1] 鲍里斯·格罗伊斯解释了这一转折:“欧洲艺术家一直以来对于细心复制外部现实的热衷——他们追求更完美模仿的意志——是基于对自然的崇拜,这个自然被认为是与唯一的上帝对应的完满造物,而如果艺术家的天赋接近神圣的话,他就必须去模仿自然。十九世纪技术对于欧洲生活的侵入,导致了这样一幅世界图景被打碎,并逐渐引向上帝已死的感觉,或者说上帝被现代技术人文主义谋杀了。”(Boris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Translated. Charles Rou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p.14.)
[2] 借自鲍里斯·格罗伊斯:“如果先锋派追随了尼采‘坠落的东西应该要再推一把’的信条,这只是因为它深深地相信,这种坠落已经无可挽回了。先锋派把世界这一神圣艺术作品的毁坏看作是一个完成的、不可逆的事实,如果要为损失做一些弥补,那么只能尽可能激进地去解释它的后果。”(Boris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Translated. Charles Rou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p.15.)
[3] 以赛亚·伯林描述了这一情形,并把俄罗斯的这一情况和一个世纪前的德国作比:“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只允许发表经过仔细筛选的作者的作品和观点,许多与政治无关的艺术形式(特别是琐碎题材的作品:通俗的爱情故事、神秘故事和侦探小说,以及一切传奇故事和各种乌七八糟的作品)又遭到反对和禁止,自然就把公众阅读的注意力集中到新的实验性的作品上来。……或许是因为在政治和经济这些显然更加危险的领域进行论战极易被认为太过于危言耸听,所以文学和艺术领域(就像一个世纪前梅特涅统治下的德意志文学和艺术一样)就成了各种观念进行角逐的唯一真正的战场。”(【英】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2页。)

《关于列宁的三支歌》
Три песни о Ленине
|维尔托夫
|
1934


马雅可夫斯基是俄国先锋派早期的一个缩影,他也接纳并发扬了尼采式的激情:抛却腐朽的过去,对抗决定论和习惯,宣扬人类意志。1912年马雅可夫斯基发表了一篇宣言,题为《给大众趣味的一记耳光》,他和赫列布尼科夫等等的一帮人像他们的意大利前辈一样,把都市生活的紧张节奏纳入到他们的美学中,他们的艺术必须向现代生活一样,是不连贯的、充满能量的,就像机器或城市,这将使人战胜时间和空间。就像马雅可夫斯基在《韵文是如何写成?》(1926)一文中写的:“要描写爱情的温柔,就去坐卢扬斯基广场开往诺金广场的7路巴士。骇人的震动会比任何事物都更好地让你体会到新生活(life transformed)的魅力。”[4]不过格罗伊斯分析了俄罗斯未来主义者和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不同:“在当时俄国人的头脑中,机器具有革命性的功能,这种功能也反映在艺术中。不过当时俄国的机器相对于西欧还很原始,因此俄国未来主义者眼中的机器并不是马里内蒂推崇的“流线型赛车”,而是更具有社会建设性的机器。在政治上,俄国未来主义也因此与意大利未来主义区别开来。[5]未来主义者或多或少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有热情。比如在1917年之前,还是个学生的马雅可夫斯基就参与革命宣传了,他在1918年更发表了一篇《给艺术军团的指令》,呼吁未来主义者加入布尔什维克,用一种政治与美学结合的攻势来对抗过去。[6]
苏联电影制作者的观念和实践显然与马雅可夫斯基的路线有所交汇。[7]大卫·波德维尔指出了电影人和马雅可夫斯基代表的左翼艺术阵线的联系:“1923年,维尔托夫跟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先锋派左翼艺术阵线(LEF)小组联合了,这个小组集合了构成主义艺术家罗钦科和斯捷潘诺娃,语言学家布里克和什克洛夫斯基,未来主义者克鲁乔尼赫和帕斯特纳克,以及剧场导演梅耶·霍尔德和爱森斯坦。......1923年,维尔托夫在《左翼艺术阵线》(LEF)杂志六月号上发表了他的题为《电影眼睛》的宣言,两个月后,同一本杂志刊登了爱森斯
坦的文章《吸引力蒙太奇》。”[8]在创作上,维尔托夫与马雅可夫斯基的联系更为密切,他1926年的电影《前进,苏联!》就借用了后者创作的罗斯塔(ROSTA)橱窗海报的手法,是诗性与新闻的结合[9],但和海报不同的是,电影使用了流动的图像,而不是单张图片。另一方面,研究者杰里米·希克斯写道,马雅可夫斯基等人也试图与维尔托夫合作:“1927年,在《左翼艺术阵线》以 《新左翼艺术阵线》的名字重新创办时,它把纪录片作为艺术和社会转型的关键策略,不过这一合作已不在维尔托夫的掌控之内了。[10]

[4]
Edited. Malcolm Bradbury, James Walter McFarlane. Modernism, 1890-1930.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8. p.261.
[5]
Edited. Malcolm Bradbury, James Walter McFarlane. Modernism, 1890-1930.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8. p261.
[6]
Edited. Malcolm Bradbury, James Walter McFarlane. Modernism, 1890-1930.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8. pp.261-267.
[7] Jeremy Hicks. Dziga Vertov. New York. I.B.Tauris & Co Ltd. 2007. P.14.
[8] David Bordwell. DZIGA VERTOV. Film Comment, Vol. 8, No. 1 (SPRING 1972), pp. 38-42.
[9] 杰里米·希克斯认为:“这里维尔托夫借用了马雅可夫斯基被称为罗斯塔‘橱窗’的内战海报里的押韵和口号机制。”(Jeremy Hicks. Dziga Vertov. New York. I.B.Tauris & Co Ltd. 2007. P.43.)
[10] David Bordwell. DZIGA VERTOV. Film Comment, Vol. 8, No. 1. 1972. pp. 38-42.

《战舰波将金号》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
谢尔盖·爱森斯坦|
1925


事实上,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艺术领域激起了一股实验精神浪潮,只要是能够给资产阶级趣味“一记耳光”的艺术,无论是什么形式,都得到鼓励。[11]但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艺术面临了更加实际的社会使命,俄罗斯的先锋派也发展出了两个不同的方向,格罗伊斯将它们称为“白色人文主义”和“红色煽动”,也可以用艺术史上更为通行的“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来理解。
前者的代表是马列维奇,他并不想做“进步先锋”,而是要找到一种不可化约、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且超越历史的东西作为依靠。马列维奇曾经写道:“所有的造物,不管是自然所造还是艺术家所造,还是具有创造力的总体的人所造,都是一个如何构造机制去克服我们无止尽的进步的问题。”[12]这个不可化约的、超越性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黑色方块”,一个沉思的纯形式的标志,这个沉思的对象是无,也就是他认为进步所趋向的那个无,这种沉思假定了一个超验而不是经验的主体。在马列维奇看来,技术的突进破坏了原初的和谐关系,而技术让这个世界遭受的损失也必须通过技术去弥补,进步的混乱特征将会被重构整个宇宙的总体方案接替,而上帝会被艺术家-分析家所取代。这种“白色人文主义”的意识是非对象化的,并不朝向任何具体救赎的渴望。[13]在格罗伊斯看来,马列维奇的根本观念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维也纳学派的逻辑还原主义,以及列夫·托尔斯泰对于简单化的呼吁相类似,它们都力图找到一个最小但实在的支撑点[14]——“处于中心的是一个激进观念,即潜意识统治着人类的意识,而它可以被逻辑地、技术性地控制,并用来建构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个体。”[15]但是马列维奇这样的先锋派在这些平行观念中的新贡献并不显著。

[11] 这是以赛亚·伯林的总结:“十月革命在俄国的各个艺术领域激起了一股巨大的创作浪潮;大胆的实验精神处处得到鼓励;只要能体现是给资产阶级趣味“一记耳光”,那些新的文化监控者就不加干涉,不管你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英】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52页。)
[12] Boris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Translated. Charles Rou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p.15.
[13] 鲍里斯·格罗伊斯这样解释马列维奇的理念:“马列维奇美学的基本论点是这样一个信念,即这些纯粹、非对象化形式的混合体“潜意识”地决定了主体与一切可见物以及主体在世界中的总体境况之间的关系。马列维奇假定,无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古典艺术中,原初的至上主义元素都处于一种“正确”的和谐关系中,虽然艺术家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识地反思这一事实。技术的突进破坏了这种和谐,于是有必要揭示这些从前无意识地运行着的机制,以便学会有意识地控制它们,并用艺术家独一无二的秩序化、和谐化的意志征服这个新的世界,在其中获得一种新的和谐。”(Boris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Translated. Charles Rou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p.16.)
[14] “即使是在先锋派圈子之外,也能找到与马列维奇的根本观念相平行的同时代观点。他的还原主义类似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维也纳学派的逻辑还原主义,以及列夫·托尔斯泰对于简单化的呼吁;所有这些都力图找到一个最小但实在的支撑点,并且都转向‘普通的’、‘民俗的’(马列维奇是经由民俗艺术、偶像画和广告牌到达至上主义的),而且都有一种“反进步主义”精神。”(Boris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Translated. Charles Rou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p.18.)
[15] Boris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Translated. Charles Rou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p.19.

《战舰波将金号》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
谢尔盖·爱森斯坦|
1925


罗钦科等构成主义者在艺术上重新解读了这一思想,这就是所谓的“红色煽动”。这个重新解读把沉思中的构造转化为现实生活的组织。[16]在十月革命和两年内战之后,曾经的俄罗斯帝国到达了一个“零点”,这个国家化为灰烬,正常的生活被打乱,社会关系被切断。正如格罗伊斯所说:“至上主义不再需要证明已经成为明显现实的事情,也就是说,物质就是无。既然末世已经到来,事物都被打乱,以向全面的末世景象揭示自身,先锋主义和形式主义关于“转移”的理论(将事物从它们正常的语境中拿出,通过非自动的感知“使它们陌生化”,并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它们可见)不再仅仅是先锋艺术的基础,而是对于俄国公民日常经验的一种解释。”[17]对先锋派艺术家来说,外部世界成了一片黑色的混沌,他们必须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机器成为他们的艺术楷模,现实本身是艺术建构的材料,而这个艺术计划是美学-政治的。构成主义者们坚信,是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注定要承担这个国家的美学-政治组织,虽然他们在政治上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但是归根结底,他们的计划是超越于某一特定政权的。这个似乎凌驾于一切的艺术计划有这样的内在逻辑:“既然这个世界本身被看作是材料,现代艺术观念背后对于凌驾于物质的权力的要求,含蓄地包含着对于凌驾于世界的权力的要求。这种权力不会感觉到任何界限,也不会受到任何其他的非艺术权威的挑战,因为人和所有人类思想、科学、传统、机构等等都被宣称是潜意识地(或者换种方式说,是物质地)被决定的,也因此会受制于一个整体的艺术方案所带来的重构。”[18]
1900年到1928年这段动荡却富有创造力的“苏联艺术孵化期”随着托洛茨基的垮台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务实的“集体创作时期”。[19]虽有高尔基等具有极高文化声望的人物保护着一些引人注目的艺术家免于过分的监管[20],但苏联的艺术总归是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本文的主题俄罗斯先锋派电影,偏向于“红色”,且本身从工业技术中产生的电影,比停留在画布和模型中的构成主义艺术更接近构成主义的实质。至于他们的实验和理念怎样地带有红色的构成性,又怎样地超出了这一时期这一国度的社会使命,有待后文详述。

[16] “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列维奇和赫列布尼科夫的后继者把早期先锋激进化了,那些后继者认为至上主义和超理性诗歌太沉思性了,因此,即使他们沉思了世界内部的“潜意识”结构而不是它的外部形象,他们也没有完全脱离艺术的认知功能。罗德琴科后来的构成主义重新把至上主义建构解读为艺术家的组织、构造意志的直接表现,而波瑞斯·阿瓦托夫,一个专论后期生产主义构成主义变体的理论家,谈到赫列布尼科夫诗歌中的构造天性。”(Boris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Translated. Charles Rou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p.19.)
[17] Boris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Translated. Charles Rou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p20.
[18] Boris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Translated. Charles Rou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p.21.
[19] 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早些年的确是由反叛和挑战西方艺术的精神所激发,以为是对资本主义最后的殊死搏斗的那种思想,如今则被强大、年轻、唯物主义和务实的无产阶级文化扫荡出艺术和所有其他的各条战线。”(【英】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4页。)
[20] 【英】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5页。

《战舰波将金号》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
谢尔盖·爱森斯坦|
1925


▶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
2020年硕士毕业论文《俄罗斯先锋派电影与蒙太奇理论》
论文指导|
周诗岩
未完待续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绪论\1
第一章 俄罗斯先锋派电影/5
第一节 苏俄文化概略/5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艺术/7
第三节 俄罗斯先锋派电影的发展/11
第二章 蒙太奇理想/14
第一节 对于形式的探索/14
(一)蒙太奇作为新闻形式/14
(二)蒙太奇作为艺术形式/17
(三)形式的意义/20
第二节 电影与社会/22
(一)何为真实:维尔托夫的“电影真理”/22
(二)何为现实:爱森斯坦的“一切为了人”/24
(三)艺术的界限/25
第三节 电影的可能性/27
(一)传播的视角:维尔托夫与电影眼睛/27
(二)感知的视角:爱森斯坦与声画蒙太奇/29
(三)联结与结构/30
第三章 再论蒙太奇/33
第一节 集体性与解放/33
第二节 经验与现实/35
第三节 美学与政治/37
结语/41
参考文献/42
致谢/43


▶
院外计划
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
汇集、
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
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
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
这一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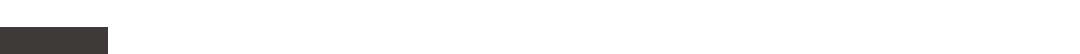
苏联电影的诞生
本文作者什克洛夫斯基,作为苏联电影从萌芽到初绽的实际参与和见证者,切实记录下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们如何从零开始,凭借真挚、天真与勇敢,将生命的热情诉诸新型的电影事业: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列昂尼多夫...在暴风骤雨的革命前线,这些青年人伴着苏联电影崭露头角,传递着革命的热血,也传达着春天的微笑。那是闪烁着奇迹光芒的年代,也是脚踏实地、幸福奔走的日子,他们所有人——普多夫金、演员鲍·里凡诺夫、摄影师阿·戈洛夫尼亚、美工师乌特金、导演米·道拉尔——坐在桌子周围,为电影争论,把自己想的东西直接告诉对方,只说最重要的东西;努力让自己的艺术修养符合这个时代。然后来到街上,迎接那个时代的、还非常寂静的、楼房层数不多的莫斯科。
那是一段天真的岁月。但却是各种伟大发明频出的年代。我们都在等待着,第二天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迹。
苏联电影诞生的时代——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我们这群人仿佛是他们所需要的那批人。我们仿佛和他们同一个时代,而同时又像是一群未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