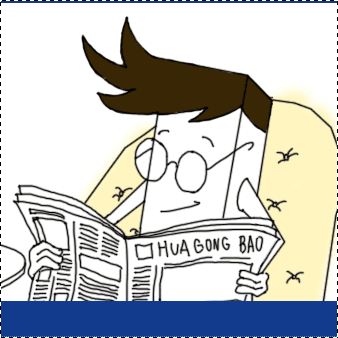司法实践中,一些犯罪分子通过盗窃、抢劫、受贿等犯罪取得物品后,将物品消费、出售或转送,致使涉案物品灭失或无法查明去向。此时,涉案物品价值的确定,事关定罪量刑以及涉案财物处置问题。办案中对这类物品价值的确定,是否必须经过价格认定,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只要涉案物品灭失,就不能进行价格认定,因而不能认定为赃物。对此,笔者认为,涉案物品灭失并不必然需要通过价格认定的方式进行物品价值认定,也不必然能够进行价格认定,即使进行价格认定也不一定能够作为认定物品价值的证据使用,而是需要结合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研判物品价值体现形式,确定价格认定的必要性。
依据不同的标准,物品可以分为多种,如合法物品与违禁物品、消耗物与非消耗物、特定物与种类物、原物与衍生物、有形物与无形物等,而不同物品的价值体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根据《被盗财物价格认定规则(2020年)》(下称《价格认定规则》)第3条规定,对于涉案物品是否需要进行价格认定,首先,看有无有效价格证明,其次,价格证明是否合理。如果没有有效价格证明或在案的价格证明不合理时,就需要进行价格认定。对于具有有效价格证明且合理的,不管涉案物品在不在案,都不需要进行价格认定,如常见的购物卡、消费卡(券),因其价值是通过面值或余额体现的。对涉案物品不是以面值或余额的方式体现其价值的,如原持有人购置新车、烟酒送给受贿人,此时车辆、烟酒的价值是通过行贿人支付形式体现的,该车辆、烟酒的价值若有支付记录等证据证明其具体价值的,就不需要进行价格认定。但如果行贿人将其正在使用的车辆送给受贿人,此时的车辆价值是通过残值体现的,就需要进行价格认定。
查明物品的来源与属性,确定价格认定的可行性。
根据《价格认定规则》第4条规定,对物品进行价格认定应当结合物品的规格型号、质量及真伪等具体情况,以一定的证据为依托。通过查明涉案物品的来源与属性,才能准确界定其名称、数量、规格型号及真伪等基本情况,进而确保价格认定能够准确实施。实践中,有人认为,只要双方对物品的种类均予认同,就具备了价格认定的可行性。显然,这一观点违反价格认定规则,也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例如,行为人盗窃他人香烟,而香烟实为假烟,若以真烟进行价格认定,就会出现行为人实际盗窃物品与事实不符、原持有人因持有假烟而获益的情况。因此,只有弄清物品的来源与属性,才能确定价格认定的可行性。对不具有价格认定条件的,就不能进行价格认定。
结合全案证据状况,确定价格认定结论的客观性。
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在对价格认定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研判的基础上,要对业已形成的价格认定结论进行全面审查,确保程序合法、方法科学、结论客观。
一是
看程序
,要看证明物品情况的证据包括未灭失的物品到案情况是否合法,委托价格认定的程序是否合法,价格认定结论告知与权利救济是否合法。
二是
看方法
,看价格认定的方法是否科学、严谨,价格认定过程是否符合操作规范。
三是
看结论
,看结论是否符合当事人认知,是否符合普通大众认知。
四是
看反馈
,看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该结论的意见。对不合法、不科学、不合理的价格认定结论,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应当重新认定或复核决定,必要时进一步补充完善证据;如果仍然无法得出客观的价格认定结论,则应当秉持刑法谦抑原则,对该价格认定结论予以排除甚至对有关涉嫌犯罪的事实不作认定。需要说明的是,《价格认定规则》虽然适用于侵财类犯罪,但鉴于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和要求是一致的,结合《价格认定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类型包括受贿犯罪涉案物品价格认定的要求也应是一致的。
针对灭失涉案物品的价格认定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笔者建议,通过提前介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制度机制,推进构建全面、稳定、有效的证据链条,以证据的确实、充分助推价格认定工作质量的提升。
一是从涉案财物的原持有人与非法持有人出发,构建严谨的言词证据。
通过对原持有人和非法持有人的严格规范讯问询问,确保言词证据的客观性;通过言词证据的相互印证,确保涉案物品指向的确定性;通过对申辩辩解的理性处理,确保言词证据的可靠性。
二是围绕涉案物品流转处置全过程,构建延伸的证据体系。
从原持有人向前延伸,同时从非法持有人向后延伸,通过询问知情人员,调取售买、流转、处置全程的书证,进一步确定涉案物品的真实性、价值变化情况以及处置问题。
三是严格遵守价格认定规则,构建规范有序的认定体系。
检察机关要加强法律监督,监督和督促价格认定机构切实发挥专业作用,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价格认定,对不具有价格认定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委托不应受理,进而形成规范、科学、有效的价格认定结论,提升现有资源利用质效。
四是针对可能存在的合理性怀疑,构建严谨的反证处理证据体系。
通过延伸取证、反复验证、重新认定或复核决定,认真核实反证的证据资格和证明能力,确定物品价值认定的合理性,加固事实认定的证据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