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当代社会,“同性恋”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政治正确了,也同时被消费和商品的逻辑征用而逐渐失去抗争性,在这样一种互异的因素交织缠绕迷离复杂的都市情境之中,你难获心灵的安宁。
——砂丁
/ 同 性 书 写 系 列 诗 选 /
夜饮
——寄彬
2017-2-16 凌晨
聚会
——寄彬
2017-4-8
相见欢
——寄彬
2017-1-30 沪东北
郊外
2016-5-30
/ 在 内 心 的 破 烂 店 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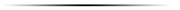
砂丁
布罗茨基在评论卡瓦菲的著名文章里谈到,身为同性恋者,卡瓦菲体会到的痛苦的深度要比其他(性取向)的作家和诗人多得多。需要辨明的是这种“痛苦的深度”,或者生命意志的玲珑多面、非模式化是何原因造成的。这样的说法似乎根深蒂固,使得这个群体既自负又自卑,在某种文学想象的光环之中对镜自照,在迂曲的生命线条中不断突破和轮回、收敛与放纵。“同性恋”是一个包含多重表意和自我回返的概念,一个矛盾的集中体。作为一种(无论生活还是文学表达上的)例外状态,同性书写里对欲望的表达既腼腆含蓄,又令人尴尬地赤裸、直接和生动。

卡瓦菲
文学作品是最难处理的一种文本类型,因为它包含的信息远比理论要繁杂得多,并且与语境和历史之间有着斩断不掉的错综联系。一些非常幽微、缠绵悱恻和痛苦的成份,只能在对文本细部的微观层面抽丝剥茧般的反复理解和体会中才能获知它们的功能和意义。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可以很轻易地、客观地谈论性别语言的各种话语建构方式,它们在大众传媒中的呈现模式,语言表述中的性倾向在何种意义和策略上被界定为一种“政治的”行动,在理论层面上如何破除“性别认同”的神话,以及基于例外状态下性少数群体建立共同生活的诸种可能性等等。在大众传媒中,性话语被建构为一系列社会学意义上的、彼此互为关联的系统性知识,并且伴随着过于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权力意志,或者直接为消费和商品的逻辑所淹没,成为一种指物的话语。但当理论入门的部分讲授完毕,直接面对文学文本对同性欲望的多重书写,无一例外地,权力视野下的外部分析在这些生动、细密、充满能量的个人化书写中失效了:理论遭遇文本的挑战,而它实际上一直是被文本挑战着的,除非理论本身呈现为一种布朗肖式的迷离混沌,其面目本身模糊不定、是无限潜能的载体。
布罗茨基是懂行的人,他对卡瓦菲的评论通常是描述性的。在涉及到一些呼之欲出的关键问题时,他欲言又止了。欲言又止不仅是一种批评的风度,更是对书写中的例外状态的合法性的承认,其合法性的建立并非寻求一种霸权的重新分配,不是去建立异性恋社会建制的另一个摹本而使权力加身(这个群体自己给自己加冕、戴上王冠),也不是就此在视野里抹除群体之外的广大他者,一叶障目式地自说自话和构建一种狭隘的性别身份。文学的功能是描述——文学从来都是描述性的,描述自己的生命体验,细密地探索属己的微观内面,去书写它、展示它,这就是政治。这种政治是能产性的、友爱的,是一种有关潜能的书写。在当代社会,私己的经验如此容易地为各种话语征用和归类,在政治神话、大众传媒和学院的知识生产中被构建为一个个权力加身的“问题”,这已经太令人疲惫和厌倦了。文学所保留的空间,那混沌沌的一团,那种内省目光的注视,缱绻的、难以言明的东西,零碎地铺洒在雨水和阳光交织的角落,像无人捡拾的破烂堆在一边——但只有书写者自己珍爱它们,珍爱这些属己的经验一如珍惜自己无从排遣的苦难和愤懑。
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的同性题材的文学作品都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无从善终、悲伤和疏离的结局。卡瓦菲在相当部分自己的诗里采用了回望的视角,这几乎成为同性题材写作的一道教科书式的金科玉律:在回望的视角之下,那些金辉般的年轻岁月仿佛重临,而甜美的时光已逝了(或许从未发生!),在曾经最蜜意浓浓的时刻,在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最深的刻度里,彼此的离散也可能即刻发生,没有任何承诺的保证。我的书写亦难逃这样的诅咒,它来自内在的深度里对爱的那种嫉妒、敏感又痛苦的体验,又在即刻的欢欣中无比沉酣、快乐和甜醉。一夜过后,人将分离,聚饮的时光和友爱的讨论让位于平庸的日常时刻,就像《会饮》里被苏格拉底拒绝的阿尔喀比亚德,从酒神的迷醉和昏沉中微微醒来,天光放亮,苏格拉底已离开多时了——他脚步如此轻盈,没有跟他打招呼。

艾伦金斯伯格与他的同性终身伴侣彼得·奥洛夫斯基
一直以来我崇拜的爱欲英雄是阿尔喀比亚德。他是真正的爱者,不是苏格拉底。我试图在书写中做到坦诚,但仍然无法像解剖刀一样地切割自己,把自己淋漓的血肉和骨架全盘展示在书写之中——在我看来,这无疑对读者也是一种过于鲁莽的冒犯。难以避免的,多年的文学训练使我熟练于在不失真的格局下婉转地出入于一定程度的虚伪和矫饰,比如营造某一些戏剧性的冲突和场景,通过不易察觉的叙事节奏的转换来推进诗意的层递,尽量做到戏剧性的内化和不动声色。对语调的经营也使得我个人在琢磨分行和字句的锤炼中更多把文本中铺排的元素服务于一个结构和整体,而较少制造不必要的枝节和斜出。当然,对于经验的写作者而言,文本不可能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整体而没有任何与主题无关的东西,一些看似自然的跳宕轻盈之笔或某个重词的临门一跃都是技术性的设计内化为书写的潜意识的结果。至于借用历史中的人物原型来重述一种爱欲政治上的左翼革命史,把在历史中行动的年轻身体纳入从善如流的绵密日常生活,以之来实现一种历史的肉身化、一种亲密关系的微观政治,在文学写作上得到的如此灵感的来源也是卡瓦菲。会有一些东西形成自己的视野,它们作为背景延伸于整个书写生命的时间历程之中:对于现代文学史全心的热爱、吉登斯、欧洲的共同体理论、关于友爱的伦理学和爱欲政治。
诚实地书写自己最内在的爱欲体验就是写作的政治。你无需考虑政治,因为当你把这些矛盾的字句写下来并发布在公众平台上的时候,它们就正在实现政治化。传播的力量——像无形之网——把你的写作裹挟进话语编织的洪流之中,你根本无需担心它们不被人看到(相反,需要担心的是它们被人看到!)、不被人为地议题化。在纷繁复杂、各种话语角逐不清的世界,你其实是不知道如何自处的。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经典性的评判标准好像都失效了,你仿佛可以尝试任何东西,仿佛可以做任何事,但又没法去做、去行动。你混混沌沌一团,写下在无数种政治正确和话语偏见的包拢中裹足不前的困境——伦理和爱的困境,这是文学空间留给自己的真正属己的部分,它们才是你赖以生存的那个荆棘之地,布满高矮不一的丛林、野果、毒蜂,但同时热风习习,天宇嵌钻广密的蓝天白云。
在当代社会,“同性恋”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政治正确了,也同时被消费和商品的逻辑征用而逐渐失去抗争性,在这样一种互异的因素交织缠绕迷离复杂的都市情境之中,你难获心灵的安宁。爱欲书写者的内心是破烂的,一如叶芝所言,一旦有什么东西被编织成话语,大概就是你应该离开它的时候了。
2017/5/11 沪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