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文飞
(俄语翻译家)
大自然的忧伤无处不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同时推出阿斯塔菲耶夫的两本书,即《鱼王》和《树号》,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树号》一些,倒不是因为后者更简短,文字更精炼,而是因为我觉得阿斯塔菲耶夫在《树号》中的表达更自然,更纯真。
原先以为这只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可没想到在《树号》一书中居然读到,阿斯塔菲耶夫自己也这么认为。他在《最珍贵的稿酬》一文中写道,《鱼王》中的某些段落“是官方腔调,夸夸其谈,后来评论家们出自对我的怜悯,把这些货色统称为政论作品”,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写道:“我不喜欢《鱼王》。”(《树号》第124-125页)
当然,《鱼王》和《树号》一样,都是20世纪俄语文学中的杰作,都已在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我觉得《树号》亲切,因为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了更多的忧伤,读到了阿斯塔菲耶夫在大自然中发现的忧伤,他在面对自然时流露出的忧伤,以及他在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之现状时体味到的深刻忧伤。

《树号》
作者: [俄] 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
译者: 陈淑贤/ 张大本
版本: 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树号,是在原始森林中行走的先行者们在树干上砍出的长方形痕迹,砍掉树皮后,露出树木的本色。两个树号之间的距离,大体上是从这个树号可以肉眼看到另一个树号那么远。在莽林中只要循着树号向前走,就不会迷失方向。
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创作轨迹的记录,他在文学的莽林里一面探索,一面砍下自己的“树号”,这些记号又引导他向创作的原始森林纵深前进,向陌生的领域开拓。
在阿斯塔菲耶夫的眼中,大自然的忧伤无处不在,大地、大海和天空,森林、树木和落叶,全都是忧伤的:“我可爱的土地入睡了,它睡得很沉很沉,由于过分疲劳而大声喘息,鼾声不止。灾难和欢乐、爱情和仇恨都飘荡在我可爱的土地上。”(《俄罗斯田园颂》)“大海见过世面,大海仿佛银白眉毛的老者阅历很深,所以它才忧伤多于快乐。”(《故乡的小白桦》)“天空,它虽然忧愁、痛苦,却一直念念不忘人间和田园。”(《麦田上霞光闪烁》)被践踏过的森林“拼命想用蘑菇的伞形菌盖遮掩住创伤和疮痍”,林中弥漫着“一小片弱不禁风的桦树叶的淡淡哀伤”(《叶飘零》),“深红色的羽状叶从树上凋落,沙沙作响,声音哀婉凄凉,它们落在洁白但不耀眼的雪地上,感到孤独,充满忧伤”(《绿色的星星》)。河边的古树“年轮最多,瘦骨嶙峋,而且满面愁云”(《水下公墓》);在“秋之将至”,“疲惫和担忧笼罩着自然界,接踵而来的是全然融入秋色,是依依不舍地与温暖告别”(《秋之将至》)。
无处不在的忧伤,铺天盖地的忧伤,这忧伤是大自然中的客观存在,更是阿斯塔菲耶夫的主观情感投射。阿斯塔菲耶夫说,面对一株渐渐凋零的白桦树,他之所以能“嗅到了一股令人怆悢伤怀的苦涩气息”,“我不是凭听觉、视觉,而是凭着我身上还没有泯灭的对大自然的某种感应”(《叶飘零》)。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的道德必修课
与“大自然的某种感应”,让我们联想到了普里什文所说的对大自然“亲人般的关注”。阿斯塔菲耶夫如此执着地描写大自然的忧伤,他能如此细腻精准地写出大自然的忧伤,首先就是因为他与大自然有着超乎常人的亲近关系。他和普里什文一样,对大自然怀有亲人般的情感,他不是在居高临下地保护自然,不是在给自然以赐予,而永远以一种平等的态度看待自然,在自然之中,他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而就是自然中的一员,是自然中的自家人。但是与普里什文稍有不同的是,阿斯塔菲耶夫似乎更“关注”大自然本身的忧伤。
阿斯塔菲耶夫善于以品味忧伤的方式接近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形成一种“患难与共”、“患难之交”的关系,其实也是他对自然所持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态度。对忧伤的体验,“你的痛苦我承担”,是俄国人、是基督徒面对包括自然、包括人生在内的整个世界常有的一种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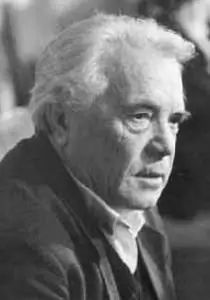
阿斯塔菲耶夫
“我们热爱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我们的痛苦。”
体验忧伤,将忧伤上升到审美的范畴,这是人类艺术由来已久的一种处理方式,更是俄国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阿斯塔菲耶夫面对自然的态度,同时也是一种伦理立场,他将对自然的态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世界观,他试图告诉世界,面对自然的态度就是面对人的态度,反过来,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的道德必修课,是一个人完满成长的必要前提之一。能体验到自然界中的忧伤,既是一种更深刻的面对自然的态度,也是一种更积极的道德自省,它代表人的情感深度和道德境界。
阿斯塔菲耶夫在《树号》的序言中写道:“失去了思想的生活,失去了’思考和痛苦’的生活,就是空虚的生活、卑微的生活;有的时候,尽管已是成年,在痛苦之中发现了似乎是身边平常的真理,这真理充满了伟大的意义:‘我们热爱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我们的痛苦……’”(《树号》第iii页)
他称“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是“痛苦”,当然不是指他遇见的一切事都是“灾难”,他遇见的一切人都是“灾星”,而是指他试图、也能够在一切事和一切人中品味出值得痛苦的东西。这种痛苦是发人深省的东西,因而让人成为思想的动物;这种痛苦是让人心软的东西,因而让人成为善良的动物。阿斯塔菲耶夫在《隔海不隔音》中写道:“他人的痛苦成了我的痛苦,他人的哀怨成了我的哀怨。在这样的时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树号》第78页)同样,体验到了大地的痛苦,体验到了自然的哀伤,也就是与大地和自然融为了一体:“真希望和大地一起肃静一会儿,我怜悯自己,不知为什么也怜悯大地。”(《秋之将至》)
阿斯塔菲耶夫在《树号》中体味到并再现出的忧伤,并非消极的而是自省的,并非沉沦的而是净化的,是悲悯,更是升华。

精彩书摘
《蓝色的光》
碧空清澄。青山隐隐,蔚蓝色的雾霭迷蒙。
夏日酷热,慵倦的大地恬然地吮吸着青草和树木成熟气息,好像闻着从俄式烤炉里刚刚取出的奶油鸡蛋大面包的香气一样。
不过,夜里空气清新爽朗,玉露铺满大地,夜空的群星更大更亮。
这是仲夏已过的时节。
《亚麻田里蓝莹莹》
蔚蓝的天空下,一片蔚蓝的田野。
我闭起眼睛——这幅景色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在那些葳蕤的、强悍的植物反衬下,亚麻的绿色枝叶显得纤细柔弱。田地恬静,向信赖的心敞开。在这里主宰一切的是古已有之对生命的忠顺。这就是对太阳、对这个天体之光的忠顺,田野从太阳那里蓄足了颜色,这颜色素淡、古朴,同时又沉静得可以信赖,它们色调单一千篇一律,令人索然寡味,仿佛是在孤芳自赏,流露出一种婉转取悦的羞涩。在相距不远的地方,田野渐渐融入朦胧无垠的天际,越是接近地平线,蔚蓝色越是清湛透明,以至于分辨不清哪里是天空,哪里是田野——生意盎然的蔚蓝色,把一切都包容到自己深邃中去的蔚蓝色。
……
被人们冷落的一轮明月悄悄挂在高空,宣告短促的夏夜降临大地。亚麻田蔚蓝色的微光从田野里向月亮走去。这一时刻,夏夜的天空、夏夜的皓月都屏住了呼吸,凝滞不动。它们保护苍穹下的世界不受骚乱和恐慌,也保护羞怯的、默默闪出蓝色微光的田地。
茫然失措的人,还是沉着些吧!忐忑不安的心啊,安静下来吧!倾听吧!谛视吧!欣赏吧!世界充满天赐的恬静爽适。你要相信,它是稳固的、永恒的。不要饶舌,不要哭泣,也不要呻吟——周围是睡梦和安谧。
万籁俱寂。田野静悄悄,静悄悄。远方,神奇而美妙。这就是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