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杨德昌遗孀彭铠立女士前段时间透露,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很有可能举办杨德昌作品回顾展。
2007 — 2017,杨德昌离开我们十年了,这是最完美的时机。
为什么说是很有可能呢?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
影迷可能有所不知,杨德昌的作品要在大陆放映,是存在一些障碍的。比如他的代表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都存在不小的障碍。所以这么多年来,杨德昌作品很难得在大陆放映。
但有心的策展人从未放弃过努力,相信终有一天,杨德昌作品的全集,能够在大陆的大银幕上,和爱他的影迷见面。
今天推动一篇刘起的文章,重新谈谈《一一》。
可能你读过不少关于《一一》的影评了,但这篇肯定还是能让你有新的收获。
没有人比杨德昌更愤怒,也没有人比他更柔软。
一系列对立的特质,以一种势均力敌的方式,呈现在《一一》中。
浪漫与现实、悲伤与欣喜、冷漠与热烈、同情与嘲讽、天真与老成、梦想与世故、说教与静观、理性与感性、既置身其中又抽离于外。这些异质性元素的碰撞,带来了一种复杂的调性,成就了杨德昌的独特性。

《一一》(2000)
很少有一部作品能像《一一》一样,在文本主题层面,呈现出这样多层次、多面向的维度。
很多人喜欢《一一》,认为这部作品像人生一样,表现了人生各个阶段。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最简单、最轻松的判断。这种判断只会滑向一种感性的、自怜自哀、自我投射的感受,对于理解《一一》的深度起不到任何作用。
《一一》包罗万有地展现了人生散漫又琐碎的全貌。影片结尾,敏敏感慨「人生哪有那么复杂」,NJ说「你不在的时候,我有机会过了一段年轻时的日子,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
洋洋说「我觉得,我也老了」。这些诗意且抒情的人生感悟,最容易获得一种情感共鸣,但也最容易遮蔽《一一》的社会维度与思考深度。

理解杨德昌的关键,在于其作品积极介入社会的意图。杨德昌是解析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状况的最严谨、最好的分析家。
《一一》拒绝以一种纯粹抒情的方式来呈现人生。杨德昌之所以成为杨德昌,就在于他在抒情的诗意之外,总是维持着一种尖锐批判的距离。这种更为疏离化的态度,使其有可能获得一种对于台湾当下社会的深刻体察与尖锐对质。
《一一》如同一个时代转折的缩影,以一种全景式的呈现方式,深刻地反映出台湾这个东亚儒家社会在现代性进程中,社会生活的矛盾与存在的问题。
《一一》中每个成年人的人生困境,都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都市人的特有处境。《一一》呈现了一个新旧交替的世界中,社会的剧烈变革对于个体生命经验的影响和改变。
NJ的人生困境,来自于社会规则对于人的绑架与形塑。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NJ,一直是一个沉默的男人。在日本一处静谧的公墓,NJ终于向阿瑞道出了多年前他离开阿瑞的原因,他父母和阿瑞都希望他学工程学,但没有人关心他自己的想法。这种无法选择自己人生轨迹的痛苦,也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

洋洋和NJ
观众能在NJ 身上,看到杨德昌本人的生命经验。杨德昌先学了工程并从事计算机行业,后来才转向电影。
这是当代东亚社会进入现代化时的某种社会现实,一般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都会要孩子选择一个能迅速赚钱的行业,比如科技、医药、法律或金融。中国人传统的实用主义,在现代社会,就体现为对孩子人生规划的功利性。
阿弟人生的荒诞剧,也来自于社会转型期一种新与旧的撕扯。阿弟的前女友芸芸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现代女性,也是他的工作伙伴,与年轻貌美未婚先孕的小燕形成一种反差。而阿弟那十分具有戏剧效果、起起落落的投资生意,也来自于他模糊的合作理念——前现代的人情关系/现代商业社会的生意法则。

阿弟
在NJ妻子敏敏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矛盾性。
敏敏是公司高管,一个典型的女强人,但当她遇到挫折(母亲昏迷)时,却慌张无助,只能求助于传统的宗教——上山静修。在一个并不引人注意的场景中,也能看到现代与传统(标准的现代化工作流程与黄道吉日)的分裂:敏敏一边以机械化的高效方式处理工作事务,一边说「我弟弟说,昨天是这一年最好的一天,所以我妈妈不会有事的」。

敏敏
传统的东亚儒家社会的人际关系,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消解和颠覆。
NJ的合作伙伴以一种商业利益为原则进行人际交往。他们对大田的态度体现了这种利益原则。而NJ身上,保留了那种前现代的人情关系,「大田是个好人,你们不能这样对他,你们这样很伤」。NJ的理想主义与天真,也是他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原因。
杨德昌的作品,一直在讨论个体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牯岭街》中,杨德昌的姿态是对抗、不妥协的,这种愤怒在结尾激化为小四刺向小明的那一刀。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
在《独立时代》和《麻将》里,依然是杨德昌对这个冷酷、自私、荒谬、迷失的世界的一种批判,他依然愤怒。但是,《独立时代》结尾再一次打开的电梯门,《麻将》结尾马特拉与纶纶在街头的重逢,却留下一个和解的可能,带来一丝温暖。

《麻将》(1996)
到了《一一》,杨德昌似乎与这个世界和解了。但敏感的观众不难发现,杨德昌依然保留了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和嘲讽,虽然是以一种温和的态度。
《一一》的美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文本的深度,来自于杨德昌对于世界的复杂态度,一种带着批判的和解、一种混杂着嘲讽的同情。这种矛盾性,带来一系列异质性元素的碰撞,同时又获得了一种和谐,使《一一》如万花筒一般,又深又美、既复杂却又无比清晰。
杨德昌在形式与美学层面,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早期《海滩的一天》和《恐怖分子》,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美学风格——远距离的、抽象化的深层视角,一种安东尼奥尼式的批判客观主义。

《恐怖分子》(1986)
《牯岭街》宏大的主题,复杂的叙事结构和众多的人物,比较接近史诗的叙事。
这之后,杨德昌跟赖声川做了一段时间的戏剧,所以,就不难理解《独立时代》和《麻将》的场景、对白和叙事结构的戏剧性。赖声川的《乱民全讲》和杨德昌的《独立时代》有某种相似性,都是当代台北的都市讽刺剧。

《独立时代》(1994)
《一一》回归到主流的宏大叙事传统,以一种情节剧的框架来结构故事。从形式上看,《一一》既是戏剧性的,又是高度电影化的。
朱天文说侯孝贤「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电影的特质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与此相对,杨德昌更倾向于叙事。《一一》中,NJ、敏敏、阿弟、婷婷、洋洋——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一条完整的叙事线。
通过一种精密复杂的叙事结构、准确高效的情节设置,将多条情节线并置。并通过呼应、变奏、镜像的方式,在多条情节线之间反复切换。这种高度理性的叙事方式,是杨德昌与很多亚洲导演的最大不同。而抒情的成份,就像是在严谨叙事结构中流动的空气。
从他的所有作品中,都能清晰的看到,杨德昌是怎样一个言辞锋利而内心温柔的人。对厌恶的人物,他能在批判时保留一丝同情;对喜爱的人物,他也能巧妙的限定他的热情。比如《独立时代》中,世故狡猾的小凤,自有一种爽直利落;天真善良的琪琪,也有一种优柔寡断。
《一一》从始至终,杨德昌都保留了他作为创作者同情且嘲讽的复杂态度。尽管他尽量克制不流露出这种嘲讽,我们多少还是能察觉到。比如在婆婆昏迷的悲伤时刻,阿弟一边哭一边说,「我算过,今天是今年最好的一天,妈妈不会有事的」。
杨德昌常被诟病的一点在于他的说教。确实,杨德昌的每一个人物都像哲学家,滔滔不绝的表达着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似乎每个人都能发表一番哲理性的深刻见解。八岁的洋洋说,「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这样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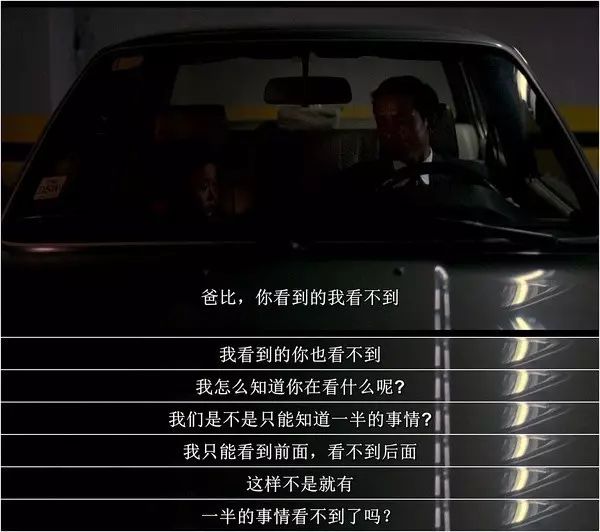
然而,如果观众只看到这个层面,我只能说太遗憾了,你把杨德昌与那些心灵鸡汤作家划了等号。
其实,杨德昌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他用对白消解对白,用说教抵抗说教。当每个人物滔滔不绝的讲着人生哲理,众多声音被并置于一处,最终就只留下一样——寂静。
比如对生活的态度。敏敏在对昏迷母亲诉说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我每天讲的都一模一样,早上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几分钟就讲完了。怎么只有这么少,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我每天像个傻子一样,我每天在干什么?」每天重复的上班族也许对敏敏的话颇有感触。

然而,大田却说,「每一天都是第一次,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同一天不可能重复过两次。」
比如对艺术的态度。「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三倍,在电影里面得到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双倍」。迷影青年很容易在这句话里找到共鸣。但其实杨德昌是带有讽刺意味说出这句话的。说出这句话的人物胖子,最终用电影中的方式——杀人,来解决自己的情感问题。
这让人想到张爱玲写的,「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再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试图通过电影中的经验来替代人生的经验,就会产生一种反讽效果。
如果不能体会杨德昌的人物话语中包含的复杂性和解构性,就无法真正理解杨德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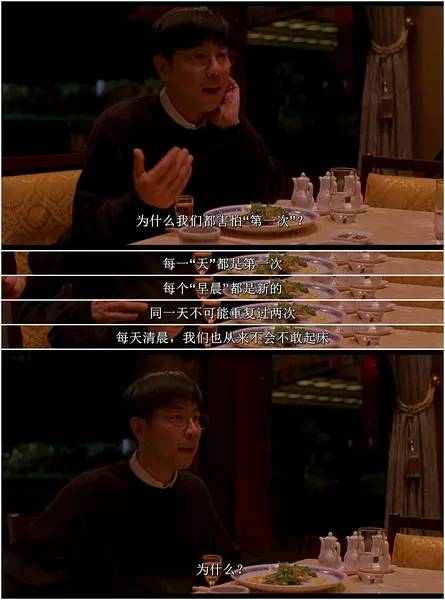
说教的目的是要灌输一种理念,是明确告诉观众作者的理念,杨德昌却并无此意。《一一》中,杨德昌似乎讲了很多道理,告诉观众很多人生哲思,但这其实更像是一种讽刺,令人想起《麻将》中红鱼所说,「每个人都等着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最终,杨德昌用这种众声喧哗的方式来抵达静默——一种审慎的静观姿态。
在这一点上,杨德昌与侯孝贤路径不同,却殊途同归。
侯孝贤的影像,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命力,很多作品都是其自身生命经验的累积和发酵。
杨德昌则不太一样。虽然在《牯岭街》和《一一》中,我们都能看到杨德昌主观生命经验的投射,但他是以一种理性的思考和高度技巧化的结构,来呈现自己的生命经验与感悟。这种对生命经验的书写方式,使作者能够获得一种既置身其中又抽离的姿态。
从个体的生命经验中抽离出来,以一种反省、批判的姿态来观察,就有可能获得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从个体性进入社会性。詹姆逊在分析《恐怖分子》时,就敏锐的发现杨德昌的这一特点——「社会的总体性是可以被感知的,但似乎要从外部」。
《一一》以婚礼作为开头、以葬礼作为结尾,这个工整对称的结构再简单明显不过,称不上有什么巧妙之处,一个平庸的创作者能很容易照搬这个结构。

杨德昌对于结构的精确把握,更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沉稳地以一种辩证关系来发展叙事:将喜剧性和悲剧性巧妙而又复杂的混合在一起。杨德昌将人生悲欣交集的复杂况味,用一种明晰的叙事来呈现。
他如此擅长转调,总是能在一个欢乐的瞬间,轻巧的滑向悲伤,又或者在一个悲伤的场面中,突然加入某种荒诞性的喜感。阿弟在看着新生的婴儿时,莫名其妙就哭了起来。这个瞬间,就是我们的人生啊——一种像是欢欢又像是悲哀的感觉。
还有一些异质性的元素,也被统一在《一一》中,形成了一种既对峙又和谐的奇妙感。
比如浪漫与现实。NJ二十年后对阿瑞说,「我从来就没有爱过别人」。曾经,我嘲笑这句情话,觉得这种浪漫虚假的近乎幻觉。

尤其是NJ回到家,疲惫的对妻子说,「如果再重来一次,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个情节似乎告诉我们,杨德昌更相信生活的现实。然而,当我今天重看《一一》,忽然觉得,杨德昌对那句话同样是深信不疑的。

比如温柔与暴戾。杨德昌的愤怒,在作品中,一定会被具象化为一个暴力事件,这也是凶杀事件贯穿其作品脉络的原因。《恐怖分子》《牯岭街》《麻将》与《一一》,都以一次凶杀作为结尾。
比如天真与老成、梦想与世故。杨德昌所迷恋的主题——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往往会被呈现为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的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的冲突。
《牯岭街》中的小四、《独立时代》的琪琪、《麻将》的纶纶、《一一》中的NJ和洋洋,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人物。在这些中心人物周围,则是一些不再纯真、自私荒谬的「社会人」,他们的老成世故,更衬托出主角的格格不入。
《一一》是集大成者,呈现出杨德昌的理性思辨力量,以及一以贯之的批判和自反。
《一一》如此清晰沉着,虽然更温和,但因为一系列异质性元素的并置,使其更深刻和更有启发性。就像导演借洋洋之口说出的给「给人们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杨德昌不仅表现人物说的东西,也表现他们没有说的东西;不仅表现人们是什么样,还表现生活是什么样。他会站得离他的人物更远一些,更多地把他们看做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人。
比起《牯岭街》,《一一》中他的愤怒和讽刺,虽然少了,但更精确和克制,可惜这成为他最后一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