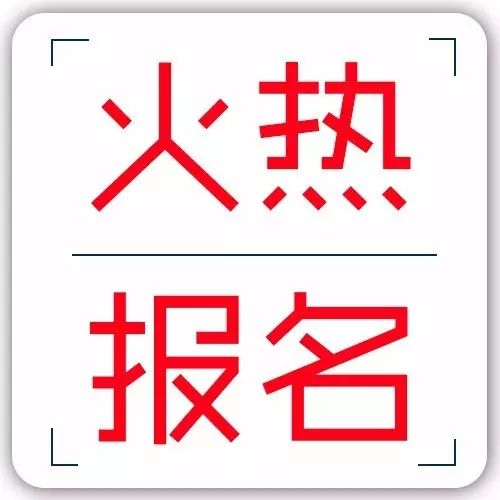《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
文︱薛冰清
1855年,美国《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记者詹姆斯·米勒·麦金写道,在奴隶制终结之时,他希望那些逃奴和帮助逃奴的人的故事能够激起全体美国人的自豪之情:
这些精彩绝伦的故事……此刻就在美国人民眼前发生,终有一天,它们会得到公正的评价。尽管现在人们觉得这些故事不值一提,只是狂热废奴主义者的事情,但总有一天,这些令人崇敬的英勇作为,这些高尚无私的自我牺牲,这些坚忍不拔的受苦殉道,这些至善至美的神意安排,这些命悬一线的逃亡和骇人听闻的冒险,将会成为这个国家最广为流传的文学主题,后世来者,将为之歌,为之哭,为之屈膝致敬,为之义愤填膺。(方纳:《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22页,下文所引原文均来自此书。)

[美]埃里克·方纳:《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焦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69元。
一百六十年后,当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在其著作《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中摘引这则史料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会预见到,一年以后,一本同样以“地下铁路”为题材的小说会横扫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等各大榜单,令这段美国往事再度成为热议的焦点。

[美]科尔森·怀特黑德:《地下铁道》,康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9.8元。
不管是方纳的学术著作还是怀特黑德的畅销小说,它们都可以视作自《汤姆叔叔的小屋》以来有关逃奴这一“文学主题”的一部分,而“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无疑是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篇章。地下铁路是美国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帮助黑人奴隶摆脱奴役、逃往北部自由州和加拿大的秘密交通网络,这一网络由变动不居的线路和接应站点连缀而成,难以计数的普通人投身其中。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这条“铁路”就已经浮现于公众的视野,关于它的神话则几乎同时开始。参与过地下铁路的人们纷纷撰写和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口述史的收集和整理工作逐步展开,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诗歌、戏剧和艺术作品接连问世。不过,如同历史学家戴维·布莱特对内战记忆的研究一样,关于地下铁路的描述和记忆也是分裂的,白人废奴主义者和黑人废奴主义者、逃奴各说各话,甚而相互攻讦责难。
这种分裂的叙事也体现在后世学者的论述当中。十九世纪末,地下铁路开始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在威尔伯·西伯特等人的笔下,白人废奴主义者成为不顾自身安危,有组织、有计划地营救黑奴于水火的英雄。到了1961年,拉里·加拉着意强调普通黑人的能动性,认为是逃奴自己解放了自己,而“那种井然有序、渡人自由的交通系统完全是个神话”(11页)。这一修正性的结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了学者们的看法。近年来,相关研究更多地转向了地方层面并进入了公共史学领域。经过数代学者的史料发掘和倾心钻研,地下铁路似乎已然题无剩义,几无“秘史”可言。但在方纳看来,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仍有诸多晦暗不清之处,值得“重新思考”。《自由之路》一书不单要撇清文学作品里的种种迷思和想象,更要弥合不同历史叙事之间的裂隙。

埃里克·方纳
不过,方纳无意撰述一部完备的地下铁路全史或通史,也不是选取某个种植园或小城镇作微观剖析。他指出,地下铁路并非以往想象中的那般规模庞大、组织严密,“而是许多地方网络的串连”,“囊括了形形色色致力于废止奴隶制的个人、意见团体和运动”(13、17页)。方纳选择以纽约市为中心展开叙述,兼及东北部地区。他首先梳理了内战前纽约市与奴隶制的微妙关系,综合考察了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和社会氛围。尽管纽约州在1827年废除了奴隶制,但纽约市在经济上和南部棉业、制糖业联系紧密,政治上由同情蓄奴州的民主党人把持要津,法律上也一再确认奴隶主有权追回作为“财产”的奴隶。和素有反奴隶制传统的波士顿、费城不同,纽约可谓一座反废奴主义气氛浓厚的堡垒。
恰恰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大卫·拉格尔斯等人领导的“纽约市警戒会”等团体纷纷成立,承担起了接收、隐匿和转运南方逃奴的重任。由于这些活动大多非法,相关记录难以存留,这也导致在先前的地下铁路研究中,几乎难以寻觅到纽约市的影子。借助于《全国反奴隶制标准报》编辑悉尼·霍华德·盖伊留存的《逃奴手记》等史料,作者阐微抉幽,重现了纽约市在东北部地下铁路网络中的“节点”和“枢纽”地位。该市废奴主义者的积极活动激励了北方各地的类似组织,也使得纽约市成为连接诺福克、华盛顿、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上州、新英格兰乃至加拿大的这一“城际通道”的重要中转站。鉴于以往的著述偏重于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俄亥俄河谷地带,方纳的研究可谓填补了东海岸地下铁路拼图的重要一环。

悉尼·霍华德·盖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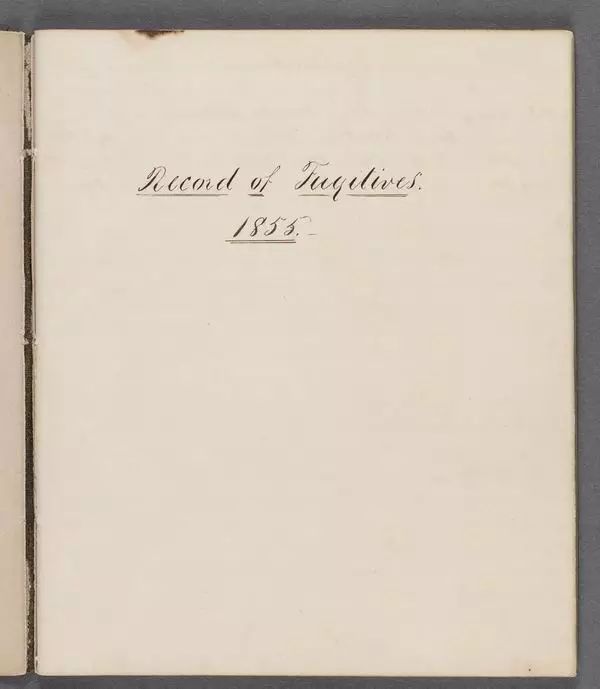
《逃奴手记》
地下铁路是一个由白人废奴主义者构建的高效网络,还是黑人极少得到救助的“历史虚构”?方纳认为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均有可议之处。当时纽约市的几个重要的废奴主义组织都由白人和黑人共同组成,后者往往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对于奴隶的最终解放,这些团体有着相似的愿景,联络互动频仍。用他的话说,“逃奴救助组织是内战前跨种族合作的罕例,它还罕见地把城市底层黑人与富裕白人联系了起来”(16页)。不过,由于具体策略的分歧、资金纠纷和个人恩怨等多重因素,它们在架构上又处于各自为战、甚至彼此指摘的分裂状态。如纽约市的主要废奴主义组织就分为两派,即支持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和刘易斯·塔潘领导的“美国和外国反奴隶制协会”。
长期以来,人们对地下铁路的另一种刻板印象是,“铁道员们”行事诡秘,外人知之甚少,这也常常是文学作品所极力渲染的内容。而在《自由之路》一书中,废奴主义者的许多活动不仅称不上秘而不宣,反而是完全公开的。他们依靠人脉协助黑奴逃往北方,延聘律师应对逃奴的司法诉讼,筹集资金帮奴隶赎身,并长期向立法机构请愿以保障黑人的权利。为了传播废奴主义思想,影响公共舆论,进而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资助,他们创办报纸,出版小册子、传单和年报,举办演讲和募款集会。不少北方的政客巨贾都公开支持这些活动,特别是由玛丽亚·韦斯顿·查普曼等女性组织的义卖活动,一度颇具声势。尤有甚者,废奴主义者还会付诸“直接行动”,用冲击法庭和警局、灌醉狱卒等手段强行带走逃奴。南方奴隶主雇用捕手追捕逃奴、“拐子社”绑架北方自由黑人和废奴主义者掩护逃奴远遁的猫鼠游戏,时常在纽约市的港口、车站和旅馆上演。1850年的《逃奴法案》通过后,废奴运动面临的处境更为凶险,这些公开的斗争也愈演愈烈。通过与更大的反奴隶制的历史语境相结合,《自由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地下铁路”这一概念的内涵。地下铁路不仅仅是帮助黑奴逃亡的通道,更是黑人与白人合作,运用道德、政治和法律手段对抗奴隶制、争取自由和公义的一系列活动。
在这些惊心动魄的抗争中,废奴主义者的言行常常得到史家的关注,而那些获得救助的逃奴的心声,则往往付之阙如。尽管少数青史留名的著名逃奴(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哈里雅特·雅各布斯)留下了他们的回忆,但读者依然要问:那些成百上千的普通逃奴来自哪里?他们为什么要逃跑,逃跑的方式是什么?在逃亡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什么?由于史料的匮乏,过去这些空白的填补大多只能寄望于小说家的想象。值得庆幸的是,盖伊的《逃奴手记》记载了1855-1856年间两百多位逃奴的地域来源、逃亡动机和方式(包括即将登上二十美元纸币的哈里雅特·塔布曼的事迹)。方纳将这份尘封已久的手稿和威廉·斯蒂尔等人的经典史料排比参照,尽可能地还原了逃奴历尽煎熬的追寻自由之旅:他们多数来自梅森-迪克森线附近的马里兰、特拉华等地,也不乏佐治亚等南部腹地;逃离种植园的最大动机是无法忍受残酷的体罚,也有出于被转卖的担忧;他们在很多时候是集体逃亡,而不是独自上路;他们会乔装打扮,借火车、汽船和马车亡命天涯,甚至将自己装箱邮寄(“箱中人”亨利·布朗)。在潜行暗渡的逃亡路上,他们固然得到了盖伊及其黑人助手路易·拿破仑等“地下铁道员”的倾力支援,但更多的帮助来自那些普通人,包括同情逃奴的南部白人、信仰坚定的贵格派教徒、身为海员和码头工人的自由黑人、富有正义感的律师和法官、把运送逃奴当作生意的船主,等等。正是这些在传统史书上籍籍无名的个体,共同铺就了这条变换不定、又无处不在的自由之路。

哈里雅特·塔布曼
总之,在纽约市与地下铁路体系、地下铁路组织的构成和活动、奴隶逃亡的动机和方式等问题上,《自由之路》一书提供给读者诸多新知新见,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地下铁路的具体运作方式。方纳运用语境主义的方法,成功地消解了关于地下铁路的种种迷思和误解,平衡了不同历史记忆之间的张力,书写了一个“黑皮肤与白皮肤的美国人携起手来,为正义的事业并肩前进”的感人故事(13页)。该书的成功,不仅在于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对旧史料的再解读,更得益于将这些材料编织起来的叙事方式。作者娴熟而老道地运用叙事史手法,以一个个或令人揪心、或使人振奋的生动案例串联全书。传统叙事性历史与“新美国历史”的结合,不仅将政治辩论、经济体制、社会舆论、意识形态等被人为割裂的历史汇于一篇,也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和人文关怀。
当然,作为研究美国内战和重建的大家,方纳绝不满足于讲一个精彩的故事,而是试图揭示这个故事的意义。《自由之路》的终章回到了所有研究十九世纪美国历史的学者都绕不开的老问题:内战到底为何爆发?奴隶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究竟是谁解放了奴隶?换言之,该书虽则聚焦于纽约市的地下铁路,实则关照的是内战的起源与性质这一宏大问题。方纳认为,尽管内战前逃奴的绝对数量有限,却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围绕奴隶制而产生的全国性政治危机中的一个焦点,是“内战的关键催化剂”(第6页)。废奴主义者的宣传营造了一种公共舆论氛围,唤醒了数百万同情逃奴、遵从内心良知的北方人民。逃奴数量的不断攀升令种植园主损失惨重,点燃了南方领导人的怒火,也让北方的共和党人分歧加深,不得不直面奴役与自由的悖论。
林肯对逃奴态度的转变,或许可以视作这种社会氛围下的一个案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为了维护党内团结,林肯对逃奴问题采取了一种较为回避和暧昧的姿态,即承认南方有追回逃奴的宪法权利,但主张修改1850年逃奴法。内战爆发之初,林肯仍抱有和南方和解的幻想,一度令联邦军队返还逃奴。到1861年底,蜂拥而至的逃奴和汹涌的民意最终让林肯宣布:所有到达联邦军队占领区的逃奴将自动获得解放。(更为详细的讨论可参阅方纳:《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在这里,方纳再次“狡黠”地捏合了以往相冲突的历史解释:谁解放了奴隶?不管是“伟大的解放者”林肯,还是“自己解放自己”的逃奴,抑或是对逃奴施以援手的普通人,作为无数历史当事人中的个体,他们都以某种形式参与并推动了这一伟大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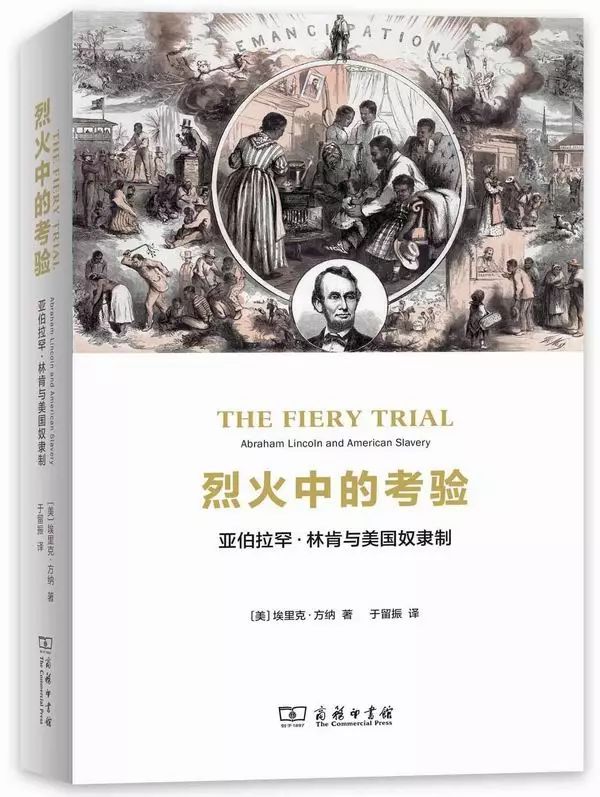
[美]埃里克·方纳:《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于留振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78元。
《自由之路》的另一重“野心”是,不仅仅要与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话,也要成为普通读者的案头常备。相较于方纳的其他大部头作品,《自由之路》可谓一本具有公共史学色彩的“大家小书”。方纳以满怀同情的笔触,书写了大历史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与怀特黑德冷峻克制的行文相比,作为历史学家的方纳反而有时显得更为直率和饱含情感。小说《地下铁道》给读者们留下了一个悬念:主人公科拉究竟会不会寻觅到她的应许之地?而在《自由之路》的结尾,许多历经千辛万苦的逃奴终于享受到了自由的片刻欢欣。这个令人稍加宽慰的结局,给奴隶制的黑暗历史,也给这个因种族关系而再度焦虑不已的国度,增添了一丝暖色。
作为一本译著,《自由之路》的中文版很好还原了方纳清晰晓畅,不乏生动活泼的文风,读来毫无艰涩之感。不过,中国读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理解这段历史及其意义,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美国的现实语境中,有关种族问题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屡见不鲜;而对没有相关历史经验的中国读者来说,要理解已经成为过去的美国奴隶制,则无疑需要突破巨大的文化隔膜。当然,这种跨越时空之幕的对话并非没有先例。1901年,林纾“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着手翻译《黑奴吁天录》,以期“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该书曾让青年鲁迅等人感喟不已,并被改编为话剧。而在冷战正酣的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黑人激进思想家杜波依斯的《约翰·布朗》《黑人的灵魂》等作品被译介到中国,风行一时。在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也不再声援“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当下,我们或许可以用一种更加富有“同情之理解”的心态,来面对“地下铁路”这份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

林纾译《黑奴吁天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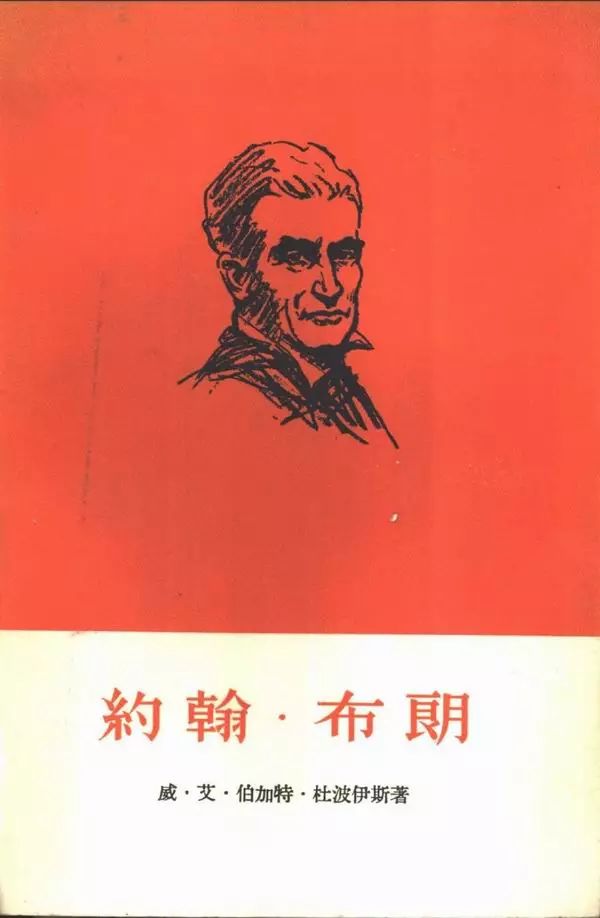
杜波伊斯:《约翰·布朗》
薛冰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