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TITUTE
|BAU学社|媒介论与空间论的会通
文|
马塞尔·布劳耶/
译|
PLUS/
责编|
BAU+

院外以纪念日为契机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
马塞尔·布劳耶可能是包豪斯年轻一代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大体也可以分为两段:早期作为家具设计师,移民美国之后作为建筑师。在他去世后几个星期MOMA开幕的布劳耶作品展中,策展
却仅限于突出布劳耶1920-1940年代的家具设计,而将他后期的建筑作品排除在外。人们对布劳耶的印象或许也大多来源于此,其中的原因部分地受制于当时后现代思潮崛起的时代大背景。然而,随着本世纪初大量的布劳耶档案整理工作逐步完成,又引发了学者们重新对这样一位现代主义运动的形式赋予者的研究。
本次推送的是布劳耶发表于1934年的文章,根据翻译文字的来源(Translated from the Dutch by Charlotte Benton, Tim Benton, et al.),很有可能出自他在荷兰的讲座。彼时的布劳耶离开包豪斯的教职并独立执业四年有余,但从理念上来看,仍承袭着包豪斯时期的教学架构,此外他又试图以自身的实践转向,
对新建筑的意识形态进行更为深入的考查。
在这篇文章中,布劳耶明确地指出了新建筑的三大
基本动力和方法:
全面和平衡的改进;清晰直接地面对问题与形式;
用对比创造出审美满足。所谓的“新建筑”并不是时新的“新”形式,而是在这种
形式中所体现的解决方案,只要整体上的模式还存在,那么“新建筑”应该根据情况的需要,持续十年、二十年或一百年。
布劳耶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工业标准化的转型期,所以为了满足当时代的需要,有必要以
科学原则和逻辑分析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家族传统和习惯势力。
由此反倒联结起了这两者共同的特点:非个人化特征,沿着典型的、理性的路线发展的趋势,不受过往各种时髦的影响。
由此,在布劳耶看来,需要破除的是新建筑所谓“新”的意识形态神话:
“原创”是指
根据理念彻底地解决相关的难题,“个性化”则是处理最复杂以及直接相关问题的强度和应用程度,而“想象力”表现为如何将形式的秩序施加于现实世界的韧性。在当时的语境中(尤其是考虑到1932年苏维埃宫竞赛的结果导致的苏联与CIAM的决裂),布劳耶还有意识地将建筑与他认为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革命”一词做出了区分,并相信只要关注
心理生理、协调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建筑同样也能带来与政治无关的物质上的进步。
院外在编辑中配了布劳耶在这篇文章前后创作的一些建筑物的图片,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布劳耶的设计实践充分地展现了他自己坚守的立场:
新建筑并不是以直接的工程结构为美,而是考虑如何将技术文明化;新建筑要避免某种形式成为时髦的风格并在不同的尺度上任意缩放;新建筑应当以对比的方法容纳各种新元素的相继卷入,保持它们完整的个性,建立一种持久实验的平衡;总之,新建筑并不是人工的装点和修饰以此掩饰新时代的矛盾,恰恰相反,要以这种持续不断的对比作为毅力的检验标准。
暂且不论布劳耶自己的创作实现到怎样的程度,他在近百年前例举的这些原则,如果放到当下的时代,这个建筑与城市规划的模式有可能已经发生了整体的调整,甚至似乎时时都在发生变化的时代,对于我们如何判定并研讨何谓真正意义上的“新”,比如但不限于参数化、算法化、网红化等等问题,仍有所启示。由此,本文并不是重申当年建筑的“新立场”,而是试图将当年那一立场所处的情境拉回当下的“新力场”。
院外还将推送与马塞尔·布劳耶后期建筑创作相关的论文。

Marcel BREUER|1902年
5月22日
-1981年
7月1日


马塞尔·布劳耶|
Marcel BREUER

要是放在过去,我一直就反对许多有关
新建筑
的理论研究,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工作就是建造,只要拿出我们的建筑物,它们自己已经足够把问题说清楚了。除此之外,当我意识到这些理论与提出这些理论的人之间往往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时,我不免也会有些愕然。所有理论研究的危险在于,如果一个人的论证过于深入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把现实的世界抛在脑后。现代运动的有一些原则已被广泛采用,但由于它们是被分开来用的,失去了与整个运动目标任何的协调关系,因而它们也已经受到了损害。由此,当务之急是要对新建筑的意识形态进行更为深入的考查。
现代主义运动的主角们一直忙于他们各自设计的分类和发展。这就意味着进一步的宣传都留给了机会、工业广告和技术期刊。结果是,很多事情都被歪曲了,都被忽视了。
现代术语热衷于那些掷地有声的口号,而其中的每一个口号都只服务于某些孤立的细节。这些异质的部分与它们统一的整体之间仍旧缺乏关联。现代运动的先驱们现如今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非常广泛的智识基础,这与他们自己的工作是一致的,而年轻的一代却仍旧把自己局限于僵化的形式。建筑是一个惊人的多方面的综合体,一旦离开了技术领域,任何一个概念都会变得含含混混、层层叠叠。
那么,
新建筑
的基本动力和方法是什么呢?
首要的是,
它
要实现全面和平衡的改进,而且是不带任何形式的先入之见,特别是传统的先入之见。
其次,它能够以清晰、透明的方式将自己与特定的任务、问题或形式直接展开客观的接触。
再次,它通过对比和运用各种元素的形式,创造出审美上的满足感。

Harnischmacher House
, Wiesbaden, Germany
|
Marcel Breuer
|1932


(1)
让那些喜欢从一个流派或风格的原则过渡到另一个流派或风格的原则或风格的人,也可以采用这些原则,只要他们愿意的话。
我们相信的是,我们自己所感知、所经历、所思考、并证明和计算出来的。
说到这一点,我想岔开去先讨论一下传统主义。我所说的传统,并不是指对那些不久前才过去的事物的无意识依赖。需要强调的是,那些被称为现代建筑师的人,他们对真正的民族艺术、对古老的农舍、对伟大时代的艺术杰作,有着最真挚的钦佩和热爱。举例来说,我们在旅行时,最感兴趣的是寻找那些人们的日常活动保持不变的地方。
最令人欣慰的事情莫过于
发现一种创造性的手工艺,这种手工艺是由父辈们一代又一代地发展和传承下来的,它们没有上个世纪建筑的虚伪浮华和空洞虚荣。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但不是为了模仿。对我们来说,想要按照民族传统或旧世界的风格来建造是不够的,也是不真诚的。现代世界的八小时工作日、电灯、中央供暖、供水、轮船,或者任何的技术方法,都不存在它们的传统。人们
可以对整个时代大加挞伐,对那些在现代生活的漩涡中失去了心理上均衡感的男男女女,人们可以对他们表示同情,
或者与他们保持距离,或者希望他们能改头换面——但我认为,用传统的屋檐和雨棚来装饰他们的家对他们并没有丝毫的帮助。恰恰相反,那只会扩大表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使他们更加远离理念的均衡,而理念的均衡正是或应当是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最终目的。
或许,将乡土建筑或民族艺术的某些方面与现代主义运动相提并论,似乎是有些自相矛盾。不过,有趣的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形式都是非个人化特征的;还有就是,它们都沿着典型的、
理性的路线发展的趋势,
不受过往各种时髦的影响。也许正是这些特点,使得真正的农民艺术如此打动我们——尽管它所引起的同情纯粹是柏拉图式的。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农民劳作的坚实、无意识的美、令人信服的品质和合理性的来源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原因就在于它的无意识的、因而也是真正的传统性质。一个地区只有那么几种传统的工艺,使用那么几种特定的颜色。
粗略地说,同样的东西,或者同样的东西的变体,一直都在那儿被制造出来。即便是那些变体,也遵循着有规律的、反复出现的节奏。正是由于这些变体通过地方和家族的联系得以传承,毫无间断,这才决定了它们的发展,并最终使它们成为标准化的类型形式。
至少在一个方面上,我们的现代努力有类似之处:我们寻求的也是典型的、规范的东西;那不是偶然的,而是确定的特别形式。这些规范的设计不是为了满足
上个时代的需要,
而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
。因此,我们不仅要利用到工匠的工具,而且还要用现代的工业机械,自然而然地实现它们。
如果考察一下工业的标准化,人们就会发现它是一门“艺术”,是传统发展的代表,而传统发展是反复探索同一个问题的结果。有所改变的是我们用的方法:我们采用的是科学原则和逻辑分析,而不是家族传统和习惯势力。
我不想由此带来什么误解。我决不是说农民艺术和现代运动实际上有任何的联系。我只是想说明某些趋势之间的相似性而已,这些趋势已经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两者各自的相对完美。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承认,有许多古老的农庄比许多所谓的“现代”房屋更能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总之,认为现代主义运动蔑视传统艺术或民族艺术那是不正确的。只不过我们对
传统艺术或民族艺术这
两者的同情,并不会让我们想把它们其中的任何一种作为媒介,用来达到当今完全不同的目的。

Gane Pavilion, Bristol, England
|
Marcel Breuer
|
1936


我想把
新建筑
的“不偏不倚”的一面与所谓的新、原创、个性、想象力、革命性等等的词汇剥离开来。我们都容易受到“新”这个词的影响。社会通过授予专利来表达对任何新事物的尊重。国际专利法就是基于两项原则:“技术改进”和“新颖性”。因此,新颖成为一种强大的商业武器。但现代运动对“新”真正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新、追求意想不到、追求改变,就像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的去追求不偏不倚的观点一样?我想,我们可以断然否定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要创造新的东西,而是要创造合适的、正确的、相对完美的事物。
现代运动中的“新”必须被看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不像
女性的时装那样是
目的本身。我们的目标和信念是,
新建筑
形式中所体现的解决方案应该根据情况的需要,持续十年、二十年或一百年,这是可能的——只要模式还是那些模式,这种情况在时装界是无法想象的。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并不惧怕新的事物,但新颖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追求的是明确和真实的事物,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
我们已经厌倦了建筑中一切与时髦有关的东西;我们发现所有刻意创新的形式都令人厌倦,而所有基于个人偏好或倾向的形式也同样毫无意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简单的考量,那就是我们不可能像更换领带那样,频繁地更换我们的建筑或家具。
如果“原创”、“个性化”或“富有想象力”指的是艺术的任性、快乐的思想,或者特立独行的天才闪现,那么我必须回答说,
新建筑
的目标并不是原创、个性化或想象力。在这里,术语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我们的理念,现代建筑如果能够彻底地解决相关的难题,那么它就是“
原创”的
。而我们所说的“个性化”,指的是处理最复杂,或者直接相关问题的强度或应用程度。所谓的“富有想象力”不再表现为遥远的智力冒险中,而是表现为将形式的秩序施加于现实世界的韧性。
客观地面对问题的能力,也让我们看到了现代运动中所谓“革命”的一面。我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会有些迟疑,因为最近它已经被各种政党接纳了,而且在一些国家,它实际上已经被当作一种基本的公民美德灌输给了学校的孩子们。事实上,革命现如今几乎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制度。我认为,在这场运动的最初,革命只不过是一种
前所未闻的原则,那就是
把自己的客观观点付诸实践。我们的革命态度既不是自我安慰,也不是宣传家的夸夸其谈,而是
我们工作独立性的内在回响,
以及尽可能的外在回响。尽管“革命”这个词已经得到了体面的认可,但却让我们颇为不安:因为这个词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
当然,政治
就像在生活中一样,也
在建筑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把政治与建筑的任何一种不同的功能都相提并论的话,那将是错误的,是把一般带向了特殊:
建筑上技术和经济的潜力与它的倡导者的政治观点无关。由此可见,建筑上审美的潜力也与他们的政治观点无关;同样,特定的建筑师解决特定功能问题的力度也与他们的政治观点无关。
首先,政治与建筑在问题的性质上是重叠的;其次,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手段上也是重叠的。但这种联系绝不是确定无疑的。例如,即便知道斯大林和苏维埃宫竞赛的推动者是共产主义者,那又怎样?他们的论点与任何思想原始的资本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或者仅仅是保守的、热衷于更粗糙的栓塞形式的汽车制造商的论点如出一辙。尽管生活和思想各不相同,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有它非常重要的政治层面,而这一层面又决定了它的性质。因此,建筑师满足于分析和解决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来自于它们的心理生理、协调和技术经济等方面。我相信,这类工作能够带来与政治无关的物质上的进步。

Hagerty House, Cohassett MA
|
Marcel Breuer and Walter Gropius
|
1938


(2)
现代运动的第二大动力是追求清晰,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直接”。这两个词丝毫都没有浪漫倾向的暗示。它们并没要求我们把心思放在衣袖上,或者放在长长的横条窗上。
这种“清晰”的特殊诠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就像公开展示构造的愿望常常会导致违反结构的原则,或者天真幼稚地过度强调结构的原则。以这种精神诠释的“清晰”导致了一个满眼“螺丝钉”和“智识暴露癖”的令人不舒服的世界。只要有一点天真的良好意愿,
著名的由内而外的“外化”原则就能创造出一个完美的荒野。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清晰”原则
在建筑的技术和经济领域,表现为
强调结构的规律和实际的功能;而在美学领域,则表现为简洁的放弃一切不合理的形式。
新建筑
可以比作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晶体结构。它的形式符合人类的规律和功能,这与自然界或有机体的规律和功能有所不同。在过于直接的概念中,我们的这种新建筑是人类住所的“容器”,是他们生活的轨道。我们的建筑是否可以用“冰冷”、“坚硬”、“空洞”、“极端逻辑化”、“缺乏想象力,每个细节都机械化”这类的描述来识别吗?难道我们的目标是以家庭生活的机械化取代办公室和工厂的机械化吗?有这种想法的人,要么只看到了现代建筑中最糟糕的例子,要么没有机会住在最好的建筑中,也没有机会仔细地观察。他的想法或许还有些混乱。他说“人性”时,是指华而不实吗?他唤起“舒适”时,是指棕色的墙纸吗?他要求的“平和”,是指空洞的伪装吗?总之,他把我们从未有过的意图算在了我们头上。
现代运动的起源并非技术,因为技术早在人们想到它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了。
新建筑
所做的是如何将技术文明化。它的真正起源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日益增长的意识。然而,事实证明,要想清楚地阐述新建筑的智识基础和审美,远比在实际应用中确立它的逻辑要难得多。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功能性的厨房设备,更容易让那些
吹毛求疵的人接受
我们的理念;结果,他们往往会与我们的审美相协调。这种方法很简便,因此导致某些现代建筑师在广播技术进步方面相互竞争,并且依赖于由一系列数字支持的理论推导。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建筑采取了一种刻意的统计态度,而这种态度沦为了另一场竞争,看谁能在剥夺建筑任何审美的时刻方面走得最远。于是,工程师被认为是真正的设计师,所有技术上有效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美的。
我认为不妨可以将此看作已经走到了尽头的趋势。工程结构并不一定因为是工程结构的就一定是美的,尽管往往可能因为它们的建造者在形式方面具有明显的天赋,所以它们才是美观的,或者是作为科学传统的结果,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令人满意的工业形式——规范,标准。当然,在面对技术问题时,工程方法的实际客观性也大有可为。与上个世纪的许多建筑设计相比,工程师负责设计的那些至少是能用的。
为了给事物正名,
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想当然地以为工程学的成就是美的。
总之:对我们来说,清晰意味着明确表达建筑物的目的,真诚表达建筑物的结构。人们可以把这种真诚看作是一种道德义务,但我认为,对于设计师来说,这首先是一种毅力的考验,从而为他的成就奠定成功的印记;而这种成就感是非常基本的本能。在我们对简洁的崇拜中,我看不到任何清教主义,相反,我们热衷于以较少的花费获得更大的效果;通过智慧和对自己主要资源的安排,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一些事物,从而获得满足感。我所说的“无中生有”,指的是从一面平整的白墙上赢得色彩、可塑性和生动性。
在
新建筑
中,理性主义在哪里结束,艺术从哪里开始?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是如何确定的?即便我尝试,也无法找到这条边界。建筑似乎只有在对我们的感官产生影响时才值得注意,而我们的感官对合理化的过程并不陌生。这种效果,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称之为“美”,不管它是由工程师,还是由艺术家创造的,不管它是所谓思辨研究的结果,还是所谓直觉生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不关心这些方法之间的区别,但我非常关心我在完成的建筑物中是否感到自在。
我们不需要外来的形式美,不需要装饰的美,也不需要激发未经设计的结构元素带来的美;甚至不需要在
某些尺度上
任意放大,那纯粹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时髦。我们对那些被贴上象征主义、立体主义、新柏拉图主义或“构成主义”标签的建筑毫无兴趣。我们知道,建筑的基本要素和决定要素可以是完全理性的,而这种理性丝毫不会影响建筑物的美丑问题。每个做过规划、设计和施工的人都知道:
(a)尽管有逻辑意志,但协调的决定性冲动往往是通过无法控制的条件反射产生的。
(b)
即便用最客观的逻辑方法探讨某个问题,在每一种情况下
几乎
都必须在不同的组合中做出最终的选择,差不多可以说这种选择并不是合乎逻辑的。
(c)
真正有灵感的构筑物所具有的令人信服的震撼力,是一种近乎激情的顽强毅力的结晶,而这种激情超越了单纯的逻辑。
(3)
现在,我要谈谈现代运动的第三大主导动力:从未间断的元素之间的关系——对比。它的目标是非图示的设计。谁要是认为我们偏爱平屋顶,我们就会把咖啡壶做成平顶的;谁要是认为我们的建筑物是立方体形式的,我们的照明装置就会与之呼应;谁要是认为我们的指导原则就是在所有的这些事物之间建立统一和某种和谐关系,并将它称为某种“风格”,那么他就完全误解了我们的目标。在
新建筑
中,并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硬性和快捷的公式。只要你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相同的形式,您就可以肯定这是由于对类似的问题采用了类似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一个橱柜开始像一栋房子,一栋房子看起来像地毯的图案,而地毯的图案看起来又像床头灯,那么你就可以肯定,它不是我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作品。我们力图让所有不同的元素都能有明确的设计,将它们并排排列,而不是人工地修饰它们。这些元素因为不同的结构而获得了不同的形式。它们完整的个性是为了建立一种平衡,在我看来,这种平衡比纯粹表面的“和谐”更为重要,那种“和谐”可以通过采用形式或结构上的共同点来实现。我们拒绝接受传统的“风格”概念,首先是因为它否定了真诚而恰当的设计;其次,是因为外观差异之间的联系产生了我们认为是现代生活特征的那种对比。比如,建筑和自然、人的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空隙和实体、闪亮的金属和柔软的材料、植物这样的生物与墙壁的鲜明素面,以及学科中的标准化与实验的自由等等。这种对比已经成为了生活的必需品。它们是我们选择方向的现实保证。不加改变地保持这种极端的能力,也就是保持它们的对比程度,是衡量我们的毅力的真正标准。

Chamberlain Cottage, Wayland MA
|
Marcel Breuer and Walter Gropius
|
1941


▶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
|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1890-1939: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of Original Articles.
|1975

▶ 配图
1932
|
Harnischmacher House
这栋住宅体现了包豪斯初步课程的影响。重点专注于纹理、形式、材料和感知模式的对比研究,以制定出一种无需构图(compsition)的制作(making)方法。布劳耶从这些教学中获得了对比(contrasts)的强鉴赏力,在他整个设计生涯中都突出使用开放和封闭,嵌入和投射等手法。
1936
|
Gane Pavilion
二战态势白热化后,布劳耶搬到了较为平静的英国。他适应周围的环境,采用了当地乡土气息浓厚的粗石墙。将英格兰乡村的质朴与现代主义理念中的轻盈结合在一起,后来在他美国的住宅设计中也有所体现。
1938
|
Hagerty House
布劳耶在美国的作品继续探索乡土设计的真实性与日益增长的现代主义推动力之间的重要关系。早期的住宅都是与格罗皮乌斯共同创作的。布劳耶采用了轻质的美国气球框架结构,再加上厚重的石墙结合挑空和悬臂形式的现代主义特征。
1941
|
Chamberlain Cottage
这栋小屋
只有一个大房间,一个厨房和浴室,但在布劳耶看来,它
代表了美国原始木制建筑的现代转型。
这是他与格罗皮乌斯合作设计的最后一座独栋住宅。设计上非常简约,营造出极大的温暖感和质感,也没有美国住宅设计中典型的分层。通过质感极简的设计方法,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方式改造木质框架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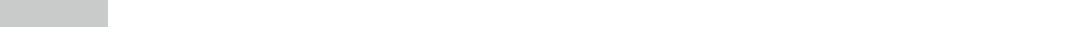

▶
院外
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
BAU学社
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
星丛共通体
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
回声·EG
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
批评·家
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
BLOOM绽
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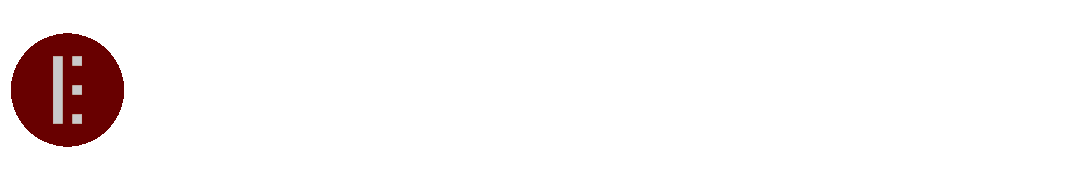

▶
院外计划
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
汇集、
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
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
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
这一目标。

▶
BAU学社
|
学社 ▶
设计史?艺术史?思想史!
|
情境对话中的“理念”
|
包豪斯流
|
历史转承中的“演练”
|
包豪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