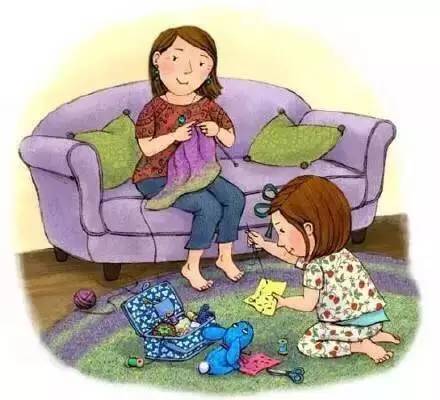正文
在我的旅行清单上,有那么几个听来浪漫却不太容易完成的项目,比如走遍印度29个邦、去婆罗洲寻找红色榴莲、在水果季重走丝绸之路等等。
而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算是最触手可及的一项了。
选在夏天去西伯利亚,纯粹是对自己的耐寒程度没有信心,往背包里塞了一条棉衣和一个保温杯后,才安心登上飞机。
时间有限,无法把远东城市海参崴作为起点,只好投机取巧地选择直飞西伯利亚腹地,再登上一路向西的火车。
西伯利亚天生具有遗世独立的气质。
2010年,一位叫西尔万•泰松的法国记者看透了都市生活的假象,于是带着一箱子书和十八罐辣椒酱,搬到贝加尔湖畔的小木屋里,独自度过六个月,还写了本书,叫做《在西伯利亚森林中》。
他常把小木屋的世界与此前生活的巴黎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
归隐等于反抗,隐居生活使人的雄心缩减到可能的比例之内。
比如一会儿得钓到鲑鱼,才有今天的晚餐。
这是外人给西伯利亚贴上的新标签,原始、粗犷,人们从源头汲取能量,森林里盛产的蜂蜜和鸡油菌能在国际市场上卖出好价钱。它还是新贵们彰显旅行品味的小众目的地、完美的隐居之地,历史太容易被抹杀和遗忘了。
电影《穿越西伯利亚》中,一位曾被关过劳动营的老人说,
“如果你想了解美国,就去看书;如果你想了解俄罗斯,就得拿把铲子,他们都被埋在这里,科学家、传教士、诗人,上帝是不存在的,西伯利亚也不存在。”
去西伯利亚之前,或者索性就在火车上,读一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你的旅程也许会更加沉重,但也更丰满。
当下的中国,高铁神话正渗透到各个角落,城市里则是无缝对接的共享单车和网约车,人们再经不起多一秒钟的等待,儿时的绿皮火车,也定格成了周云蓬的书名留存在记忆里。
为什么要来西伯利亚呢?或许只是潜意识想寻找可以被感知的慢时间。
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
俄罗斯的第一程火车,就差点没赶上。
午餐吃得太开心、电子书也看得太入迷,不小心就把Kindle忘在了餐厅。直到收拾好行李准备去火车站,才发现完蛋,还要插播一段“飞速狂奔领取失物”的情节。
我买了最低等级的卧铺,对面是一位中亚长相的年轻小伙,额前飘着几簇油腻腻的齐刘海,像生意人,但貌似生意也不太顺利。
分辨火车上乘客的经济状况,有个很简单直观的办法,每人都会带着一大包干粮上车,隔壁下铺的格子衫胖大叔,从袋子里变出了一只
烤鸡、莳萝腌的黄瓜和土豆
。
而我对面的中亚小伙,则掏出了一只搪瓷杯子,倒入瓶装
碳酸水
,细细品味起来。
在我们相处的24小时中,他一共吃了三顿饭和一次下午茶,内容全都是一根
火腿肠加黑面包
,饭后甜点是
两颗糖
。
从雷打不动两颗糖的克制中,小伙子才得以在如此容易发胖的俄罗斯幸存下来。
帮我扛行李的格子衫胖大叔,或许已到了对形象自暴自弃的年纪,吃掉半只烤鸡后,他把剩下的包起来,然后掏出一块巨大的甜饼,趁我在拍窗外晚霞的时候,不容分说地塞了小半块到我面前。
中亚小伙也不示弱,掏出四颗糖送给我——他的两顿饭后甜点。
语言不通的一个好处是,无谓的扭捏和客气,都没有发生的土壤,相对无言只求心意相通。
我只好照单全收,连一个俄语的谢谢都说不出来。
中途火车停在一个小站,几乎大半男人都迅速下车,抽烟、散步、活动筋骨、月台上挤着不少包着头巾卖烤鱼的村妇。在格子衫大叔的协助下,我买到了一条烤鱼,一袋莳萝土豆和黄瓜。
朝西的火车在追赶时差,下午6点过后,窗外的一万亿株白桦都披上金色光芒,接下来是漫天晚霞。
从未见过如此纯粹的粉紫色晚霞,翻滚在地平线的尽头,无边无际的天空和白云、电线杆、草垛、树林,看似单调重复,却莫名令人安心。
在我居住的地方,那个被称为魔都的大城市,所有人都在无所不能地追求创新和变化,一成不变是可耻的,心中没有宏伟蓝图的人,甚至没有立足之地。
也许,在送我一块甜饼、一根火腿肠的人里面,有着被埋葬的诗人和科学家的后代。
此刻,这些人正进行着穿越西伯利亚的壮旅,只需在几天几夜的时间里和自己战斗,像胖大叔和中亚小伙那样,看望远隔几千公里的亲人,或是去谈一桩希望渺茫的生意。
当他们望着窗外时,眼底都好像有看不到尽头的深邃。
叶卡捷琳堡——喀山
这趟火车旅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也是我第二次经由陆路,穿越欧亚两大洲,上一次是在伊斯坦布尔。
“在俄罗斯,不管什么场合,只要出现一个伏特加酒瓶,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世界。”
日籍俄语同传米原万里小姐如此写道。
一点错都没有。
同车厢的三位大叔,等不及火车开动,就从包里掏出小瓶装的伏特加。
初次见面的他们,仿佛一起闯荡江湖几十年的老朋友,一人打开电脑播放电影,一人准备下酒菜(无非又是巨大的火腿肠),另一人倒酒。
自然也不会放过我。“喝一点喝一点。”
“我真的不会喝,喝了会晕倒。”语言完全讲不通,我急了,只好双手合掌放在耳边,歪着头做了个睡觉的姿势。
接着赶紧拿出包里的枸杞、红枣等小零食,算分享给大家下酒(好奇怪的下酒菜啊)。
车厢的酒气让人疲惫,但最心累的是长时间无效沟通。俄罗斯人有股莫名的倔强,他们似乎认为,只要反反复复地同我说俄语,我就能听懂。
无可奈何,只好跑去餐车,打算吃一顿时间跨度堪比Fine Dining的晚餐,至少耳根子能清净一下。
点了牛肉薯条和红菜汤,环境尽管简陋,但至少还有打着领结、身穿西装小马甲的侍者服务,没想到我同车厢的老头也跑过来了,俨然已是醉汉的模样。
啪地在我对面坐下来,摇头晃脑的冲我胡言乱语,那距离已经令人非常不舒服了。马甲侍者小哥也司空见惯,马上冲过来礼貌地问我,“他打扰到您了么?”
“是的,当然,我只想一个人待着,而且不认识他。”
侍者冲我眨眨眼睛,眼神饱含着希望我理解的歉意,对着醉老头一通劝说,半拉半扯把他挪到其他桌子。
结果老头又走回来,几番拉锯之后,我也心烦意乱,被酒鬼骚扰真是最无奈的。而且我们座位在同一车厢,回去还得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
俄罗斯人嗜酒是全世界出了名的,伏特加堪称俄罗斯国酒,大多数男人甚至把伏特加看作自己的“第一个妻子”。
不管来到哪个城市,总能在路边发现零碎的空酒瓶,如果大清早就看到有人双眼迷离地呆坐在地上,不必害怕和惊慌,只是个醉鬼,绕道走就行。
然而在火车这样的封闭空间,酒鬼无疑是最大公害,没有之一。
喀山——莫斯科
坐火车的档次循序渐进,这趟换成了封闭式的二等车厢,四人间。半夜上车,迷迷糊糊就睡了。
翌日醒来,发现同屋是一位胖胖的俄罗斯妇女,带着两个年轻小姑娘,会说英文,能跟我顺畅地交流。仅凭这一点,就能明显感知到车厢等级与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
有趣的是,语言没有障碍,很多时候并不能加快互相了解的速度。
受过高等教育、眼界开阔的人,反而对陌生的旅人没有太大好奇心。
出于礼貌,或出于教养也好,你们不可能再手舞足蹈地去试图表达自己了。
记得我在印度钦奈遇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去机场短短20分钟路程,他大概问了我100个的问题。
“中国、香港和日本,哪里比较好玩?”
“你们通常开车还是坐火车去旅行?”
他说,“我每次拉到外国客人,都会问他们国家的事情。我很想了解外面的事情,不是通过网络或者新闻,而是通过活生生的人。”
但对于坐一等车厢、头等舱旅行的人来说,外面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莫斯科——圣彼得堡
莫斯科的火车站密集,光市内就有大大小小十几个车站,9个正在使用中,而且命名方式也很有趣,通往哪里就叫什么火车站。
比如喀山火车站,是前往喀山的;基辅火车站,前往乌克兰;我下一站要去圣彼得堡,很简单,那么就是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旧称)火车站。
从莫斯科开始往欧洲方向走,会讲英文的人越来越多,城市气质更接近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孤独感更加强烈。
因为离得近,两地之间设有快速列车,类似于高铁,只需要3个半小时,对于动不动要坐几天几夜火车的俄罗斯来说,简直是过家家的距离。
8月的圣彼得堡阴雨连绵,下火车前,我穿上初冬的夹绒外套,一边想念喀山的阳光,一边瑟瑟发抖等候巴士。
我的火车之旅,也到尽头了。
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坐火车”的举动也愈加趋向于功能性。
坐在时速超过250公里/小时的高铁上,观赏风景成为了奢侈品,刚刚对远处田野上颇有地方特色民居产生兴趣,还没来得及仔细看,列车就把风景甩在了身后。
我们被速度剥夺了看风景的权利,被密封的玻璃阻隔了新鲜空气,所以只好在狭小的座位上玩手机、看剧、回邮件,忍受熊孩子们在ipad上大声公放《小猪佩奇》。
而那些慢悠悠、臭烘烘的绿皮火车,眨眼间变成不合时宜的落后产物,因此还落上了一丝复古的文艺情调。我甚至不能确定,它们是否仍旧存在。
但对于广袤而荒凉的西伯利亚来说,东西近万公里的长度足以让任何速度黯然失色。
西伯利亚的火车之旅,注定是缓慢的。
猜你可能会喜欢
公众号:叶酱的孤独星球(yejiangd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