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二十二年前的今天,邓丽君猝然离世。
这一天,许多人屋顶上的月亮不见了,有人怅然若失,有人失声痛哭,一代人失去了他们的精神初恋。
第二天,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国际频道)报道了“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昨日在泰国清迈病逝”的消息,这是大陆最高级别的媒体第一次对邓丽君进行报道。
二十天以后,葬礼在台北举行。国民党秘书长许水德、“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主持葬礼,“总统府”资政郝伯村、“行政院长”连战、“国防部长”蒋仲苓、台湾省长宋楚瑜、台北市长陈水扁亲自进香,邓丽君的灵柩上,覆盖着中华民国国旗和中国国民党党旗。为了及时报道葬礼全程,超过三百位中外记者,凌晨三点就开始守候在殡仪馆外……
在台湾岛内,这是自一九七五年蒋介石过世后最大规模的葬礼。在此之前,人们根本无法想象,一位演艺人员可以如此备极哀荣。
然而,某种程度上说,这只是另一个“邓丽君时代”的序曲。

02
在整个大中华文化圈,人们对邓丽君的怀念,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她生命的结束而终止。对于那些已经把她的歌声与自己的人生紧密纠缠的歌迷来说,对邓丽君的缅怀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从来不曾被时光冲淡的内心恒久的暖意。
二〇一三年,在邓丽君去世十八年后,在“摩天伦”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拜好莱坞的特技团队全息影像技术所赐,邓丽君“复活”了两百一十秒,与周杰伦深情隔空对唱。就为了这二百一十秒,四十五名特技师前后奋战了两个多月,耗资新台币一亿元。
两年以后,“如果能许一个愿”邓丽君逝世20周年虚拟人演唱会举行,在台北小巨蛋举行。依靠“虚拟影像重建”和“裸眼3D投影”技术,歌迷仿佛回到二十年前的旧时光。
整个华语乐坛,身后二十年还能被人如此怀念拥戴的艺人,邓丽君大概是唯一一个。

03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林青霞和邢李原的婚礼在旧金山举行。新娘说,“我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当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林青霞接到邓丽君打来的电话,她赶忙问“你在哪儿啊?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林青霞说了一大堆,邓丽君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在清迈,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送给你。”
那林青霞和邓丽君最后一次的通话。
其实,这对“宝岛双姝”的交往并不深,可是林青霞说她对邓丽君欣赏的程度是,“
如果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决不介意。
”

04
实际上,即使林青霞,在大陆也不曾像邓丽君那样受到过近乎狂热的喜爱,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
八十年代初等待着邓丽君的,是一个大国封闭荒芜后的求新和求知欲。而她则为处在微妙的历史节点上的大陆人,为如饥似渴地需要正常女性美的大陆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
作家韩松落说,在邓丽君的形象里,隐藏着一个中国梦。她出身贫寒,但始终在为成为一个典雅女性而努力,始终在对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进行自觉沿袭、认真模仿。
七八十年代台湾的社会结构下,倡导的是一种质朴有力的审美,正是这种取向,培育出了一个邓丽君,她那种干净的、甜润的、精心雕琢的、咬字和气息均体现着极大克制的声音,也是对她所在时代的最好回应。
她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标准中国女性的形象,温润、明媚、柔韧,时髦得适度,所以很难过时。这两个形象汇合出的邓丽君,作为一个女性共相,嵌入了整个时代的形象之中,完美、毫无瑕疵。
女性可以成长,可以逐步成为一个理想女性,并因其人格价值而得到肯定,这正是大陆女性在至少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敢想也未曾想象过的。邓丽君显示了这种可能性。

05
作家王鸿谅说,如果要寻访邓丽君,你恐怕需要准备一张世界地图——她生于台湾,葬于台湾,却几乎在全世界留下人生的轨迹: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法国、泰国……所有这些地方,都埋藏着她快乐或者不快乐的记忆。这些或长或短的异乡时光,就像硬币的两面,她是实至名归的国际化歌者,却也是始终漂泊的异乡过客。
在时代的大幕面前,个人永远是渺小而软弱的苇草。邓丽君一生的艺术生涯,都笼罩在冷战的铁幕之下,终其一生,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是对她演艺事业最为重要的三个国家和地区。而这三者之间,恰恰有着极其错综纠缠的历史恩仇。
邓丽君去日本发展,不仅不被曾为抗日军人父亲谅解,也同样受到海峡两岸民族情绪的影响,一九七九年的“护照风波”,有一度令她在日本和台湾“腹背受敌”。
据母亲赵素桂说,邓丽君生前最大的遗憾不是没有嫁人,而是始终没有机会到从未曾去过的老家河北邯郸看一看。她曾经梦想来大陆演出,而且是“在天安门广场,不收门票,就唱给大家听”,在那个时代听起来,这个愿望就像梦呓一般不切实际。

06
一九八〇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举行了一次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专家认为,邓丽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是精神文明的大毒草。会上被批判得最激烈的,是《何日君再来》。
专家们认为,“
《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但它是首黄色歌曲;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调情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是舞场中舞女劝客人喝酒时唱的……这是对血泪现实的掩盖,是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生活的歌颂,是以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现在还喜欢《何日君再来》的同志要认真想一下:是‘好花不常开’,还是应该用我们双手去创造永不凋谢的花朵。
”
然而,活生生的历史现实却是,姑且不论数以亿万计的歌迷,一大批迄今活跃在中国文化一线的歌唱明星们,都把邓丽君奉为他们心目中不可逾越的经典,因为那是改革开放之后,闯入他们文化记忆里的第一缕不一样的声音。
很多邓丽君的模仿者都格外提到她的“气息”,比如田震、王菲、齐秦、刘欢、程琳、成方圆、那英,包括海峡对岸的罗大佑、蔡琴……他们都悉心研究过她独特的曲风和发声方法,称她为“气功大师”。
在歌手崔健看来,邓丽君之所以能够“摇滚了全中国”,是“因为她的歌并不是软绵绵的,她的歌里有真正的个性”。
“
没有人能超越她的地位和影响,她是一个启蒙者……远远超过流行歌曲或是一个流行歌星带给社会的影响。她用她的歌声甚至改变了大的社会思维,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她的歌彻底改变了我们,说她是五百年出一个也不为过。
”导演甲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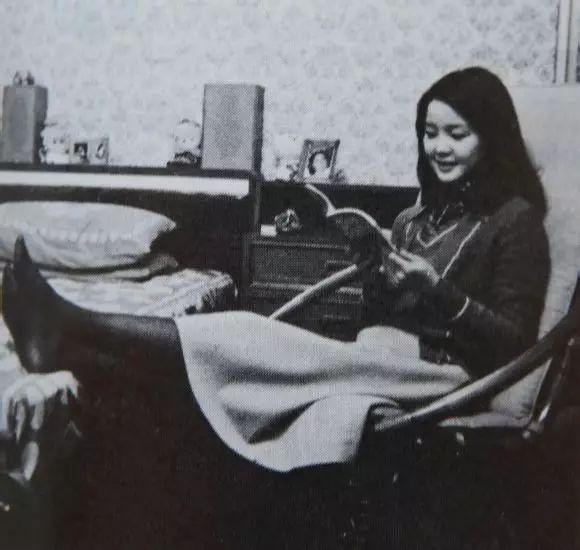
0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丽君对大陆人来说是一本流行音乐、大众文化的启蒙教材,台湾流行音乐兴起、香港华语电影新潮、内地“文革”结束封闭的国门打开,邓丽君恰好是那个做好了一切准备去接受改变的人。她用歌声牵引着大陆民众面对开放的世界和重新以人性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