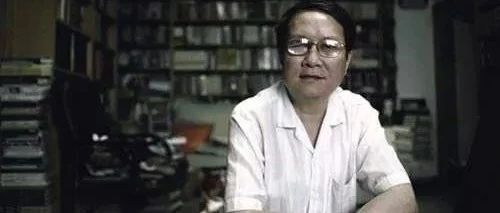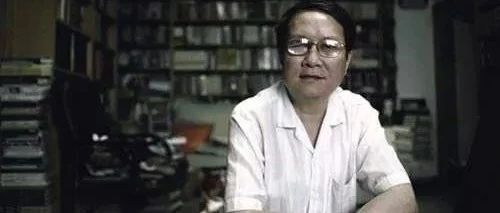奥托·昆泽里《DieSchonheitsgaleri Suzy》,75×62.5cm,1984年
首饰早已不仅是身体的装饰,也不仅是昔日眼里财富与地位的象征,不仅是精雕细琢的工艺。「我
们知道的越多,对生命的了解就越少。
」
被称为荷兰艺术概念首饰先驱的Ruudt Peters这样说。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有生命温度的作品,不止是首饰。
不妨斟上一壶茉莉香片,听听背后光阴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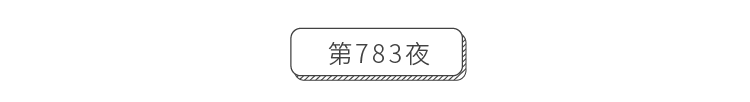
早在上世纪中叶,出生于1928年的德国金匠(Hermann junger),在一板一眼的金工劳作中就了解到:这些精确的横平竖直应该是属于机器的,而不是人的义务,人应该是一种鲜活的存在——有血有肉,有情有梦。
赫曼·荣格
1958年作品
于是,在
一隅安静的
金工室,他逐渐抛弃了传统饰品的繁复华丽,而是打破常规,将人的思想放入作品,给冷冰冰的金银注入生命,包豪斯和后现代的美感,无数汹涌着的情绪和想法,尽在期间。
后来他的徒弟,1948年出生于瑞士苏黎世的艺术家,如今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客座教师奥托·昆泽里(Otto Künzli)进一步
打破了首饰的界限
,他说,「黄金可能足以象征一切,太阳、无限、神圣,但是澳洲的原住民却聪慧地说出:你不能吃它。但它总是从黑暗中来,从石头、山峦中显现,代表着光芒.....」

奥托·昆泽里
1984年
作品《DieSchonheitsgaleri Suzy》
从黄金宝石到树脂、木块,他用令人惊喜的颜色、触觉与肌理,诙谐幽默地表达了对规则的突破,将情绪、人生与荒诞幽默推向极致,开创了当代艺术首饰的先河。
在他看来,首饰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有着生命与情感的体
验,同时也有着自主的审美
。
「用一个带有一丝欺骗感的简单审美,这个用墨条制成的吊坠就展示出了朝生暮死、传统、永恒和优雅。然而它又是脆弱的:即使最小的雨,也能让它溶解,最后成为某个穿戴者身上的一幅抽象毛笔画。
」
奥托·昆泽里
1980
年作品,《烟灰墨块》吊坠
他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Ring for Two》(两个人的戒指)中,他将两个人之间无形的距离变成可见;
奥托·昆泽里1980年作品
《Ring for Two》
比如用48件已被戴过的结婚戒指创作而成的项链,叙事性远远超过它的形式感——48对爱人分别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本身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
奥托·昆泽里1985年作品
突破的道路上不止他们。被称为荷兰艺术概念首饰先驱的Ruudt Peters也在作品中注入灵魂与生命体验,认为「所有的首饰都是相互关联的,是由事件的流动过程和各种灵感共同产生的
」。

Ruudt Peters2015年作品《IAM》
再往后,还有设计师Dukno Yoon“会动的首饰”,将机械结构与运动方式融入到首饰设计当中,首饰与手指结合化身为飞翔的小鸟,与佩戴形成了亲密的互动关系。冰冷的机械,也注入了柔和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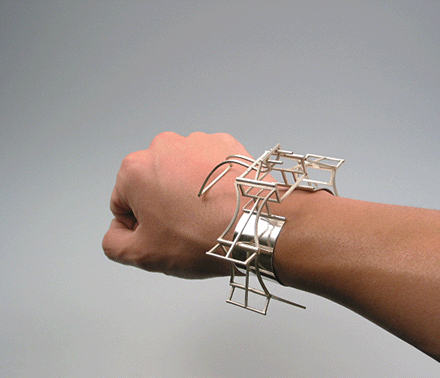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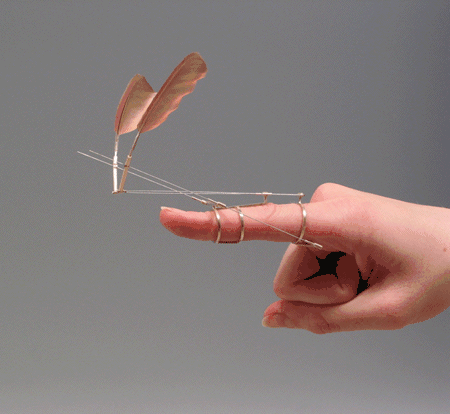
Dukno Yoon“会动的首饰”系列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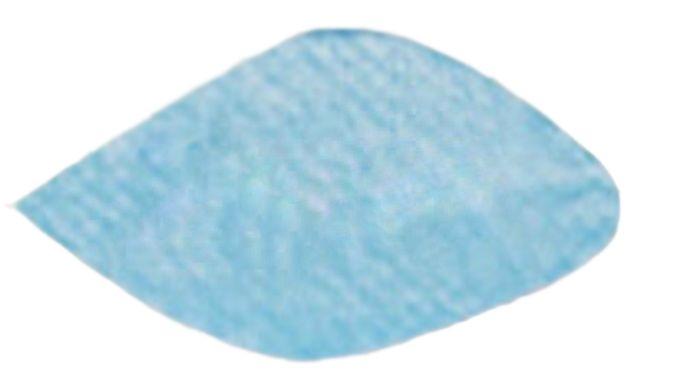
的确,首饰终日与人体摩挲,感受肌肤温度,本身就和人本身有很深的联系,冥冥中承载着生命与情感——
当首饰变成了对生命、时光的体验与记录,这样的创作,在一向「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中国,表达形式应该同样甚至更加动人。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首饰艺术还是传统的形式为主,开荒与转机
要从2004年
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作品《对话与独白》说起。
这组饰品以银为基本材料的手工精铸而成,结合了巴洛克珍珠(即不规则形状珍珠),弯曲不规则的造型更接近自然中的生物,带有温暖柔软的意味,传达出生命和情绪的美感,和前文的大师们异曲同工。
这组作品的作者——中央美术学院首饰专业的创始人滕菲老师,在自传《光阴集》说,「金属向来给人的感觉是冰冷、机械、锋利,而在我的作品中,我试图让它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来,小心地保留了指纹的印迹.......」,从而把首饰变成联结个体生命与思考轨迹、精神需求的载体。正是这种想法,渗透在她所做的“国礼”中,带给各国的女性元首和第一夫人们。
滕菲“飞花摘叶”系列作品,从左到右分别赠予时任俄罗斯第一夫人梅德韦杰娃、巴西女总统罗赛芙、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
同样是雅致而温润的银质曲线搭配巴洛克珍珠,同样是指纹的痕迹和弯曲造型,梅花的姿态浑然天成,对生命自然情感的探索表达同时自带东方式的典雅含蓄之美。
滕菲“飞花摘叶”系
列作品,从左到右分别赠予时任葡萄牙总统席尔瓦夫人 法国总理菲永夫人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夫人
然而提起滕菲,不应只是中国当代首饰艺术的奠基人,国礼的设计者,央美首饰专业创办者这些华丽的名头,也不应是学版画出身、在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留学时转而爱上首饰艺术的才女,而是一个真正生活过的人,对待生命与时光,日出与日落有着极为深刻细腻的体验。
1993年,滕菲(右)于柏林联展现场
这个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女子把自己的生命体验比作“天梯”,在梯子里埋存有许多与自己生活休戚相关的小东西。「如一根儿时的蜡笔、一颗彩色的玻璃球、一枚少先队队徽、一辆小汽车、青年时代的一块表......一捧茶叶和一片集成电路板……我在想,人生的痕迹可能就是这些在无意间留下,却又在搬家时被我们从落满尘土的一角发掘出来的东西。拾起东西,置于掌心,任凭思绪游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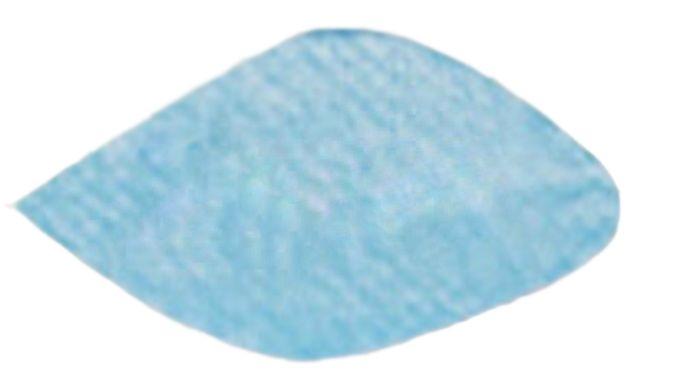
也正是这种细腻的生命情感体验,有了她带给我们的那个夏天,光阴荏苒中暗香浮动。《
那个夏天
》指的是1988年的夏天,那时候滕菲
初为人母
。很多年后她为自己设计制作了这一款首饰,银色的choker紧紧围绕脖子,带着一大块如血般殷红的漆雕——形状来源于剖腹产的疤痕。
从身体与个人体验出发,探索生命与自然、时间、光阴的关系,让外在的首饰与个体内里的精神共生,这正是滕菲对首饰艺术的理念。
她把人生时空的忧切情怀统一在和谐浑厚的首饰设计意象中,正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
」
后来的作品《梅香》更体现这种精神,深刻表现了由人事代谢而对古今往来的自我觉醒式的探索追求:苍老遒劲的梅树已经是「竹篱茅舍自甘心」,却砥砺重生,抽出来一枝新芽,似有疏影横斜,暗香浮动。
「小心守候岁月,‘变化’却还是不知不觉附着于身,人的经脉、骨骼、肌肤、精力都被时间作用着,就像生活的改变一样的抽象,其过程是肉眼看不见的,而结果却往往触目惊心。
」酷爱老庄学说的滕菲如
是说。在这样的基础上,她制作了光阴系列,把光斑拍摄的形态提取出来,做成项链。

而
这件项链也只是个工具,交给不同的人去抛洒、把玩,最后定一个形态,每个人都可以
有一片属于自己、量身定制的光阴,用手作皮带背在身
上:「其实阳光是你永远不能收纳下来的,而通过这样一种转化方式,你就捕捉到、收纳了一片属于你自己的光阴,你背着它,就可以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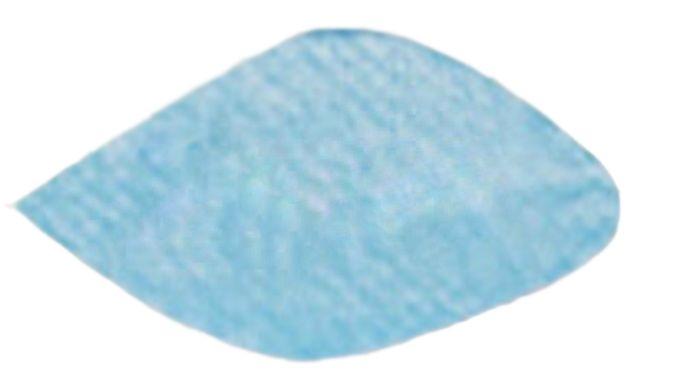
在《光阴》之后,滕菲老师受Lens的邀请,再次用了捕捉光斑、凝聚时光的灵感,为雷克萨斯设计了这款镂空胸针《光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