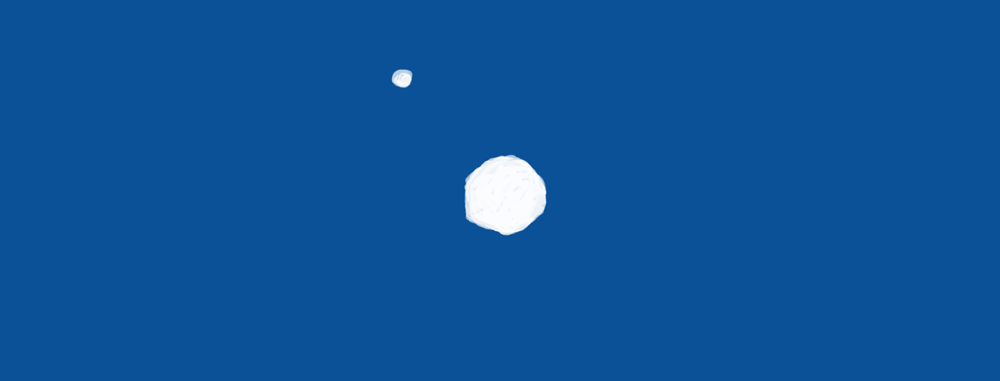
他是不同国度,不同文化间的漫游者,是学者,也是诗人。作为皇帝,他欲为基督教夺回圣地,但教皇却视他为妖魔。
很少有君主像腓特烈二世这样,身上被贴了各种标签。他就像戏剧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轮换着各种面具。他是“阿普利亚的男孩”,因为他来自西西里,幼年多灾多难。他是诗人,自己写诗,资助西西里的诗人群体。他是鹰隼爱好者,喜爱研究鸟类,热衷驯隼狩猎。他是风流情种,有很多情人。他是“救赎者”,因为他参加十字军,与埃及苏丹谈判,兵不血刃拿下圣城耶路撒冷。他又是“敌基督”,因为他行为放荡,宽容异教,与教宗争权。他是“暴君”,因为他对待敌人残酷无情,给帝国带来西西里的专制作风。尼采称他为“反教会者”,这或许是尼采自己内心的投射。
布克哈特称他“王座上的第一个现代人”,并不是赞美他,而是批评他的专制作风破坏了古老的封建传统。
1943年7月10日,美英部队执行了代号为“哈士奇”的行动计划,在西西里岛南部海岸登陆。盟军迅速挺进。7月
22日,在登陆两天后,他们攻下巴勒莫。德军经墨西拿海峡撤回意大利本土。完全撤离巴勒莫前,德军接到赫尔曼·戈林的一项奇怪命令:将存放有皇帝腓特烈二世及其家人骸骨的石棺从巴勒莫运走。他是想将其运往德国吗?莫非是要让腓特烈回归故国?
石棺没能运走。
博学的英国军官或许不会认为这事有何非同寻常之处。彼时人们正在讨论德国人是否生性残暴,而英国的历史学家们则提出了各种匪夷所思的证据以肯定这一点。同样,腓特烈二世也被作为证据之一。1942年伦敦的历史学家福西·约翰·科布·赫恩肖发表《13世纪的希特勒》(A Thirteenth Centurry Hitler)一文,文中通过六件所谓的类似事例譬如阴险、残暴、杀害人质,将阿道夫·希特勒的性格特征转嫁到腓特烈二世头上,这样一来就将后者与那名身着褐衫的独裁者相提并论了。赫恩肖也同样在腓特烈身边发现了一名恩斯特·罗姆:皇帝多年的亲信和大文书长维尼亚的彼得罗。
同样,能够以相反的方式将皇帝腓特烈二世与阿道夫·希特勒做比较:在赫恩肖发表其比较成果的同年,纳粹历史学家卡尔•伊普瑟在盟军登陆西西里岛之前出版了《德意战斗同盟第二年》,这是一部关于腓特烈二世的著作,其中作者在同样的背景下正面评价了这位西西里人。前言一开始写道:“腓特烈一生都在为帝国的伟业斗争和操劳,昔日和现今的欧洲命运都掌控在帝国的手中。”伊普瑟坚持“根据出身、外表和成就来看,皇帝腓特烈二世正是欧洲北部的德意志人”,其结论就是:“长久以来他都是一个外人,但如今他的人民理解他,他完全是我们中的一员。阿道夫·希特勒保卫了他的功绩,并将它发扬光大。”因此,希特勒所称的“德意志历史上最伟大领袖人物”理应“魂归帝国”。作为“德意志”皇帝,他的肉身自然也应回到故乡,决不能留在奸诈的罗曼人那里。
与此同时,希特勒本人也将腓特烈二世视为西西里人,正如他1942年4月在一次圆桌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但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腓特烈二世的暴政。这一点一直萦绕在德皇威廉二世脑海中。1905年意大利之行期间参观蒙特城堡时,陛下叹息道:“若是我也能像他那样将人鞭打和斩首,那么我也能取得更多成就。”
△威廉二世
不是只有德国人才会将腓特烈二世看作领袖人物、英雄般的君王、理想中的统治者。艺术史学家阿图尔·哈泽洛夫及助手马丁·瓦克纳格尔在20世纪初曾骑着骡子,用相机记录了意大利南部施陶芬王朝时期的建筑与艺术品,在与当地人谈话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腓特烈二世及其子曼弗雷德在当地被视意大利黄金时代的象征性人物。施陶芬王朝时期的意大利南部并非欠发达地区,恰恰相反,当时它在意大利及地中海地区扮演了核心角色。
在20世纪的意大利,人们的这种观念与对腓特烈的追思并没有减退,反而变得更强烈。多年担任罗马德国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阿诺尔德·埃施曾谈到一个颇具参考意义的插曲。1998年,为了测定腓特烈的 DNA,人们曾打开巴勒莫的棺椁,从这位皇帝的遗骸中取了一些尸骨样本。而这一事件的参与者眼里闪着光,不知为何又叹息着,说道,现在可能会克隆腓特烈二世了,如果复活这位统治者,南部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个国家的政客一直致力将这位西西里统治者的形象塑造为多元文化的传奇帝王,这位帝王将地中海自古以来应得的地位交还给了地中海。此外,根据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观点,他统一了欧洲,并且“是从这里而非从柏林开始”。
将自己的期望投射到腓特烈二世身上,这可不仅仅是当代独有的现象。早在中世纪时期,就能听到关于这位帝王极矛盾的声音,这些观点一直到今天仍被援引。其中大部分评价来自编年史,这些编年史作者试图用有意义的方式整理出连续的历史,向自己同时代的读者解释这些历史,使其易于理解。英国本笃会修士巴黎的马修在其《大编年史》(Chronica Maiora)里记叙1250年历史的部分中,谈到这位帝王之死时称,
腓特烈二世是“世界奇迹和改变世界的神奇之人”(stupor quoque mundi et immutator mirabilis)。
马修认为腓特烈是“地上最伟大的君主”(principum mundi maximus)。后世最爱援引的对腓特烈的评价“世界奇迹”,正是出自这一早期文献。但是在中世纪人的理解中,对奇迹的描述还伴随着敬畏。其他统治者,如“狮心王”理查一世和教宗格里高利九世,也同样被称为“世界奇迹”。但这一称谓只在腓特烈身上固定下来。
腓特烈二世是十三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出色的统治者之一。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西里王国的国王,罗马人的国王,他也是耶路撒冷的国王,他被后世的人们称为中世纪的凯撒。
他出生在意大利的西西里,父亲是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母亲是西西里王国的女继承人康斯坦丝,腓特烈二世是他们的独子。
腓特烈与亨利六世只在施洗中见过一面,亨利六世赋予他FEDERICO RUGGERO的名称:意寓将继承祖父红胡子(FEDERICO I)和外公罗杰二世(RUGGERO)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丰功伟绩,成为西西里与日尔曼两地之王。
△康斯坦丝
不久,亨利六世去世,在丈夫去世一年后,康斯坦丝也走到生命的尽头,她于1198年9月27日去世,她在去世前请求强大的教皇英诺森三世保护这个年幼的国王。因而这位年轻的国王是在教皇的监护下成长起来的,被称为“神父哺育的国王”,德国人则喜欢称他为“阿普利亚的孩子”。
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施陶芬家族的传统,并不意味着腓特烈会自动以其父辈或祖辈的政治行动为准绳。在整个统治期内,腓特烈都是在立足南部的基础上关注着罗马帝国,他的政治决策都服务于西西里王国。即使腓特烈涉足德意志,那首先也是为了使西西里免遭未来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的威胁,或者为其在意大利的政治活动赢得空间。这位统治者本人的在场就能证实这一点:腓特烈活了56岁,却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待过十年。
△亨利六世
大体而言,腓特烈二世的西西里中心主义政策意味着与祖父“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统治理念及实践彻底决裂,而后者是从北部出发推行其意大利政策的。从南部立场看待腓特烈二世,能够揭示整个13世纪不同的秩序关系。伴随着1198年德意志王国的双重选举以及随之而来的夺位之战,传统的帝王统治时代走向终结。德国传统学界普遍认为,随着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或其子康拉德四世1254年离世而产生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其实这道裂痕在双重选举产生的两位国王——施瓦本的菲利普和皇帝奥托四世——去世时就已经出现。在构建施陶芬家族皇权时代的统一性时,人们强调作为关联框架和解读框架的家庭纽带,此时这种统一性构建已被颠覆,走向反面。若是人们仔细探究接下来统治者的出身和社会关系,则这种深重的割裂就会变得更为清晰。腓特烈在西西里的统治更应被理解为一个外族国王统治时代的开端,这一时代后来由罗马-德意志国王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和对手康沃尔的理查延续。如果寻根问底,皇帝奥托四世就已经属于这一行列了,他成长于英国官廷,并拥有普瓦图伯爵和阿基坦公爵头衔。如此说来,13世纪差不多就是一个由坐在罗马-德意志王座上的外来君主统治的世纪了?
此外,皇帝和教宗对帝国制度的设想起初不断膨胀,随后又立刻破灭,这是由腓特烈统治其前半段的这个世纪的显著特征。腓特烈二世的统治是建立世界皇权最后一次失败的尝试。他利用了南部王国西西里的经济优势,意图以此为据点,吸纳一种前现代的国家政权形式。反之,从施陶芬王朝传统来看,这种世界皇权为自己披上了一层职位和传统的光环,并且以救赎史的特征作为装饰。可是,世界帝王的理念最终因欧洲存在教宗和教会、意大利城邦、民族国家及诸侯等多种统治势力而没能实现。但是无论是皇帝腓特烈,还是付出极大代价惨胜腓特烈二世的教宗,他们努力寻求在帝国内无可比拟的地位,最终都遭遇了失败。
皇帝腓特烈二世及其家族的陨落最终终结了罗马帝国的帝王理念。那么是否如约翰内斯·弗里德所言,腓特烈是真正的皇权掘墓人?他是否曾以这样一种身份被人铭记?不管怎样,一个由腓特烈二世构建的世界皇权神话,曾长久搅乱人们的渴望与希冀。
《
最后的世界帝王: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传
》
奥拉夫·B. 拉德(Olaf B. Rader),德国历史学家,1961年生,曾在洪堡大学学习历史学和档案学,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巴登-巴登的西南德广播电视台任制片人,1992年起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日耳曼历史文献处任助理研究员,又任洪堡大学编外讲师,教授文化史,其著作有《坟墓与统治》等。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是传奇的帝王,本书展现了他复杂多面的一生。他生于西西里,先为西西里国王,后成为德意志国王,进而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位。他颇有统治手腕,重视法律,颁行《梅尔菲宪章》;经营建设西西里的堡垒防御网络,参加十字军战争;与苏丹谈判,兵不血刃拿下耶路撒冷。他多才多艺,爱好文学,资助西西里诗人群体;喜好研究鸟类,热衷驯隼狩猎。
在这些历史细节的基础上,本书论述了腓特烈二世的统治是建立“世界皇权”的最后一次尝试。他死后,虽然神圣罗马帝国走向分裂,但世界帝王的理念变成了特殊的政治遗产,影响了之后的德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