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
作者 | 李渔 编辑:学妹


《平凡的世界》剧照
儿子跑路之后,孙老师变卖了自己名下所有的财产,可是债务还差500多万。欠款的许多钱都来自朋友和同事,他一辈子骄傲,老了却颜面尽失,再也无心经营他的文学。
七十年代末,那时的留岗村,天空湛蓝,一条清澈的小河在平坦而广阔的田野上蜿蜒,一直延伸到远处如白象群般的山脉。
村子恢复了千百年来的容貌:拖着爬犁的黄牛,蒙眼拉碾盘的黑驴,在田间地头,老人蹲着唑旱烟,泥地上穿开裆裤的孩子们用力地抽陀螺。爸爸说,那时他们那些青年人,成天幻想的事情就是,买一辆有大横杠的自行车,把穿着红棉袄的漂亮女孩载回家。
在高大山脉守护下的家乡,贫穷而闭塞,父辈们不仅买不起自行车,连安心上学都是奢望。放下书和笔,他们在田里弓着腰割麦子,在河滩上卖力地推运一车车石子,赚来的钱,用于贴补家用。
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孙国生都不用做,他始终坐在教室里,心无旁骛地读书、看黑板。在远近乡邻,他已经小有名气,被称作是“文学家”,他写的文章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有不菲的稿费。
时间再往前回溯十年,一群穿绿军装、戴红袖箍的知青来到留岗村。
这群来自北京的青年人,整日地在田间地头跳舞唱歌,对耕作一无所知,吃农民种出的粮食,说话油腔滑调,还有人偷盗。
老人们抱怨,这群不学好的孩子,把村子里的风气都带歪了。孙国生却喜欢往知青堆里钻,他帮知青们搬运喂猪用的草料,背着篓筐给他们收拾砍下的干柴,甚至知青们去地里偷红薯时,他就站在陇上给他们放哨。
孙国生喜欢听这群陌生的男女聊天,讲北京城里的奇闻轶事:工业区,长安街,王府井,摩肩接踵的人流,高耸入云的烟囱,彻夜不息的热闹喧嚣。与安宁的留岗村相比,北京是个奇幻的世界,令孙国生憧憬、向往。
夜晚的留岗村,黑暗笼罩,寂静安宁,村人与鸡犬都已入眠,孙国生跟知青们则围坐在篝火旁,开始读书,《林海雪原》,《青春万岁》,托尔斯泰,高尔基,跳动的文字音韵衬着明亮的焰火,偶尔,木柴燃烧爆裂,发出清脆的劈啪声。他们写诗,谈论理想与现实。孙国生看到,那些失恋的女孩子,用袖子悄悄拭去眼泪,那些莫名忧愁的男孩,在傍晚昏暗的天色里,叼着烟卷一言不发。
孙国生也爱上了诗歌,开始在废纸上作诗与写故事。他将习作拿给知青们看,得到了他们耐心的指教。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知青们对这个农村男孩的毅力与才气感到惊奇,他们说:“国生,以后你能当个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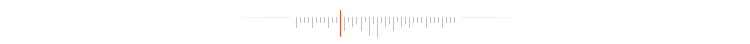
后来,知青们陆续离开,孙国生依然坚持写作。
父亲说,孙国生想方设法地从镇上、从县城里弄来报纸、杂志,走路、吃饭手里都拿个东西,低着头,专注地看。学生们整天琢磨的是毕业以后去哪家工厂当工人,唯独孙国生,琢磨的是哪里可以发表文章。
后来,孙国生的文章果然在地方的报纸上发表了。八十年代的农村,写了东西能见报,在人们眼里,就如同文曲星下凡,人们惊叹:“孙国生可了不得,以后那是要去当县太爷啦。”
孙国生不屑于村人们的见识,他宣称,自己的目标是,考大学,去北京,当作家。
这样的话,别人说来,会被人当天方夜谭,但孙国生说出来就不会,因为他写文章换来的都是真金白银,大家最信服的就是钱。一时间,村里有点儿文化的人都附和着说:“他要当不成作家那才意外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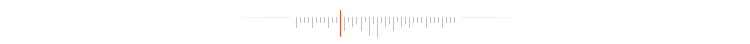
1980年,孙国生第一次参加高考,因为英语太差,没有考上。第二年再来,依然是英语不过关。接连的失败之后,当初的附和赞赏,渐渐被冷嘲热讽替代,老人们搬着板凳,坐在街边嗑着瓜子,将孙国生当成打趣的谈资:
“唉呀,老孙家的孩子还读书呐?”
“可不是嘛,啥岁数了还不参加工作,说要当啥作家。那大作家是人就能当啊,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
“要不说呢,龙生龙凤生凤,咱们这村子里能出大学生,那太阳不得打西边出来。”
父亲那段时间经常看到孙国生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对着几棵枯树、几只白鹅发呆。父亲和朋友们推着自行车,上班下班路过小桥,看到他,远远地大喊打招呼:“国生,什么时候去北京啊?”孙国生只是转过头来笑笑,对着他们挥挥手,也不说话。
孙国生后来没再考大学,他背上行囊,坐着马车去了县城,成功通过县城中学的招聘,成了一名教师。这时,村里的老人们又开朝儿孙们念叨:“多学学好,你看人家老孙家国生,现在都吃皇粮啦!”
自此,我便与孙国生产生了关系,因为他除了是我爸的同学,还是我妈的同事,也是我的老师。
等我第一次见到孙老师时,他早已经不是父亲口中那个清瘦的文学青年模样,红色的衬衫与油亮的背头,与他高大的身形,让学生在背地里都叫他“骆驼”——那是港片《古惑仔》里一个黑帮老大的名字。
这位嬉皮士打扮的语文老师,对学生们的古文背诵有着严厉的要求,课堂上若是背不出来,会被直接发配到教室最后一排罚站。妈妈说,从孙老师刚刚到县城中学时开始,他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八十年代的北方偏僻县城,学校的硬件条件还很差,教学楼只是几排低矮的平房,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全都挤在里面;煤渣铺的操场,冬天的烈风吹来,扬起漫天飘飞的灰尘,经常迷了眼睛;围墙的角落里,几栋老旧落破的房子,就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学校没有暖气,老师们在办公室烧煤炉取暖,每日早上,先往炉子里放上蜂窝煤,再将碎木头、废纸和碎煤渣塞进炉门,用报纸点火。孙老师点火时却从不烧报纸,而只用废弃的卷子——在他看来,用登满锦绣文章的报纸取暖,无异于焚琴煮鹤——他的报纸被整齐地叠好,集成厚厚一摞,放在桌脚边。
孙老师依然像当年在农村时那样,痴迷地热爱阅读,午间休息,其他老师都在办公室聊天拉家常,他则总是独自坐到窗边,在斜射进来的阳光下专注地读书看报。他时而圈圈点点,时而抬头冥想,遇到喜欢的文字,就拿出美工刀与胶水制作剪报,经年累月,贴满剪报的笔记本已经塞满一抽屉。孙老师将这些剪报视若宝贝,自己写作时,时常拿出来翻阅、参考一番。
县城有许多诗社、文学社,大大小小,或官方或民间,文学爱好者包括农民、工人、老师,频繁的笔会常安排在静谧的礼堂或热闹的饭店。孙老师发表了很多文章,在这个小小的县城文学圈子里,颇有名气。
老师们用“作家”称呼孙老师,半是朋友间的戏谑,半是真诚的称赞。
“孙作家,周末去给我家孩子教教作文。”
“孙作家,你那有什么书么给我看看。”
“不敢当,不敢当!”孙老师谦虚地客套,也不拒绝朋友的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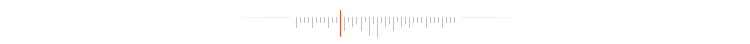
隔三差五,校长就将孙老师叫到办公室聊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在聊什么。
可是过了没多久,县城的报纸、杂志上就出现了校长署名的文章。母亲说,他们看到文章的第一反应是:“一看文笔,一看语气,那必定是孙国生写的无疑。”
办公室里开始有窃窃私语:“你说老孙这马屁拍的!我看下次评选的时候,他这教研组组长没跑了!”
可孙老师非但没当上教研组组长,连个班主任都没混上,更惨的是,第二年,他被下放去了乡镇。校长公布消息时说的是:“到基层锻炼,广大乡村更需要孙国生这样的人材!”孙老师面色铁青,一言不发,只能默默收拾行李。
妈妈说,本来,北京有个学校青睐孙老师,按照当时的人事制度,有地方要还不行,得原有的单位肯放人,校长跟孙老师打过包票,会帮他摆平教育局和人事科,条件是:孙老师帮校长写东西。
本来是一桩普通的笔墨交易,但孙老师却和校长闹得不欢而散,大吵了一架。关于二人决裂的原因,小道消息是,当年教育局局长喜欢舞文弄墨,校长请孙老师代笔的文章颇得局长赏识,于是,校长想留下孙老师,继续争取领导的好感。校长还开出条件:教研组长,以及未来的副校长。
可孙老师的理想是去北京,进入最优秀的文学圈子,当作家。他甚至天真地威胁校长,若不同意,便将代笔的事情捅出去。没想到,事情没捅出去,却把自己捅到乡镇。
“老孙人是好人,还是太年轻了。”妈妈说起当时的孙老师,充满惋惜。
孙老师被下放的乡镇在县城以北,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中。
镇子位于半山腰,两排低矮的土房顺着公路延展,镇上不通公共汽车,进出都靠人力,骑自行车上坡,只能推着走。到了冬天,大雪封了山,山路凝冻,若是不小心跌倒了,可能直接滑出高峻的山崖。
镇上也没有自来水,只能用当年日本人留下的压水井取水。寒冷彻骨的冬天,孙老师要拎着铁皮水桶,踩着光滑的冰面,走上一里地,才到井边。手套沾水后,跟铁皮桶冻在一起,他怕扯坏手套,不敢硬拽,先是对着手套哈热气,不行的话再将刚接的冷水往上浇,湿透的手套整只冻硬,像石头,才能完整从手上拔下来。再回到狭小的宿舍时,没戴手套的那只手已被冻得通红,没了知觉,也不敢直接烤火,只能长时间地搓手,直到暖过来。
“那都是磨练,宝剑不磨不利,人不磨不成器。”后来回到县城的孙老师,在同事们聚餐时说。
对于这位被下放的语文老师来说,在闭塞的山区教书本身就是另一种折磨,孙老师在简陋的讲台上,讲鲁迅,讲柳宗元,讲知识改变命运,自己都觉得讽刺。
山里的孩子不好教,有时候,教室里就留下七八个学生。孙老师去家访,说明来意,希望家长加强对孩子的管教,家长抓过孩子就打,硕大的笤帚,碗口粗的把儿,上面箍着几圈铁丝,一笤帚下去,皮开肉绽。打完,家长们说:“您是老师,孩子不听话,您该打打,我们不心疼。”
孙老师自己也有孩子,当然下不了手。他觉得很难过、悲哀,知道在这个费尽艰辛才能去趟县城的小镇,大部分上学的孩子依然会走回祖辈的路:上学,辍学,种田,娶妻,生子,下一代出生,再循环。一想到这些,孙老师就觉得,工作没了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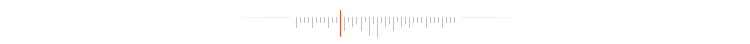
孙老师每周末回一次县城的家,骑自行车,走三个小时,在家里住一晚,又匆匆地回去——山里天黑得早,周日吃过午饭,就得返程。
孩子一天天长大,花钱的地方渐渐多起来。孙老师依然坚持写作,偶尔仍然有作品发表,只是微薄的稿费收入,对于一家三口的生活杯水车薪。孩子抱着孙老师的大腿说,幼儿园的孩子都有变形金刚,自己也想要;妻子抱怨物价涨得厉害,柴米油盐越来越贵,孩子要买衣服、买书,家里连肉都快吃不起了,“你倒好,自己跑到山里躲清净,日子没法过了!”言下之意,埋怨孙老师顶撞校长,连累家人。
面对家人的窘迫处境,孙老师也感到很惭愧。
孙老师后来告诉我父亲他“顿悟”的过程:一个深秋的夜晚,气温已转凉,他闲坐在门口,看着呼啸的北风吹打树枝、撕扯枯叶。他漫无目地舞动手中的电筒,微小的光斑在远处大山昏暗的轮廓里跳动,沉默的大山像头巨兽,威严地凝视这个渺小的人。
他想起了那些知青,他们充满才华,可仍然过着窘困的生活,为了吃饱饭,斯文扫地,东家偷个蛋,西家摸只鸡,夜里成群结队地去生产队仓库偷粮食。他想起那个教他写作的北京青年,接到回城通知时狂喜的模样。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
那天以后,孙老师开始四处走动找关系,熟识与不熟识的,都找了个遍。他拎着茅台来我家,想用用我家在教育局里的关系:“我想通了,我想调回县城。”
父亲说:“国生,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用不着拿东西,挺贵的酒,你拿回去!”
五年后,最终孙老师如愿以偿,回到县里一所初中教语文。
孙老师对我严厉,多少有父亲帮忙的缘故。
每次家长会,孙老师都会跟我父亲或者母亲单独说话,我在一旁却听得瑟瑟发抖。对于我父母客气的要求,孙老师同样说着客气话,笑眯眯地应承,但他说到做到。
语文课上,他总是站得笔直,左手拿教鞭,右手捧书,念着古文字句,在教室里来回踱步,他慢悠悠地转到我桌前,忽然把书本“啪”地一合,拿教鞭指着我:“来,把后边内容背一下。”那教鞭是竹子的,细长,泛油光,看得我心惊胆颤。悲剧的是,我通常的答不出来,只好默默走到教室后面罚站。我知道他会通知我父母,所以回家时也是胆战心惊。
父母倒也不打我,只是罚我抄课文,一遍又一遍,抄得我快要呕吐。
“我知道错了,肯定好好学习,别这么罚我了成么?”每当我这样抗议时,母亲就会向我翻起一个白眼:“你学学人家孙麦斯,你也是老师家的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
孙麦斯大我五岁,是孙老师的儿子,麦斯两个字,取自英语单词Math(数学)的发音。我妈说,孙老师觉得自己研究了半辈子语文,还是只能生活在小地方,说明学文最没用,倒不如好好学数学,以后搞金融,才能赚大钱。
为了儿子的教育,孙老师倾注了全部心血,找县城里最好的名师给孙麦斯轮流补课。我读初二那年,孙麦斯考上北京最有名的经济类院校,主攻金融学。
那一阵子,孙老师提到他儿子,就露出一副骄傲神情:“放心吧,老张,你孩子聪明着呢,以后比麦斯强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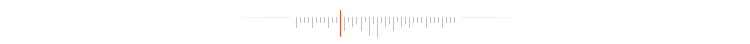
几年后,我只考上北京一所普通经济类院校,也读金融学,父母叮嘱我:“有空儿多联系联系孙老师他儿子,你们都是金融专业的。”。
联系孙麦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上大学时,他已经毕业,进了一家银行的总行,继续成为大人们嘴里的榜样:
“老孙他儿子本事了,现在一年五十多万啊。”
“老孙家又买房了,他儿子出钱买的,还给买了车,老孙那天天开的,可美了。”
“你看孙国生不显山不露水,教育儿子确实有能耐。”
后来,孙麦斯又辞职回小城创业,在城中心最好地段租下写字楼,挂投资公司的牌子,做融资,为中小企业放贷,事业“蒸蒸日上”。
于此同时,孙老师又开始写文章了,还注册了公号,经常发些小品文,诸如:
“乡村的夜,像是小姑娘的瞳,干净,透亮,时而缀满碎落的光,时而又成了望不到底的潭……”
“秋的美,在于漫山遍野的红,在于静怡不惊的水,在于眷恋枝头的黄叶,在于溢满田间的稻香……”
我妈是他的忠实拥趸,每天晚上,戴着老花镜,躺在沙发上,一字一句,大声读给我们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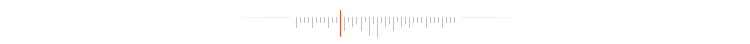
孙老师说,孙麦斯不光在北京买了房,还说要给他出书:“这臭小子就天天想着瞎花钱,我一老头子出书给谁看啊!”
说这话时,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摆弄车钥匙,听车上电子锁 “咔咔”的声响,别人就问起来:“诶呦,老孙你买车啦,什么车啊?”
孙老师摆摆手说:“咳,孩子买的,就一路虎。”
孙老师还爱上了文玩,腕上戴着光色润泽的珠子,手上两个核桃,捏得 “啪啪”直响。傍晚时分,他会准时出现在县城河边公园,慢慢悠悠踩着八字步,碰到熟人,就一脸热情地打招呼:
“诶呦,老李你也来啦,看看我这新入手的串儿!”
“正宗的海南黄花梨,你看这光,看这鬼脸!”
“两万多吧,没办法,谁叫喜欢这个呢。这对狮子头,三棱的,更贵。”
在一帮老头老太太惊叹的目光里,孙老师心满意足,揉着手上的珠子,挺着肚子,脸上挂着得意的笑,继续他的演讲:
“我跟你们讲,现在这社会,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从他年轻时候赚稿费,到教育儿子学金融,再到孙麦斯公司的理财产品,孙老师侃侃而谈,大家听得如痴如醉。
孙老师也找上我父母,让他们拿50万放到孙麦斯的公司吃利息,年息15%。他说,跟着他老孙,买卖稳赚不赔。
孙麦斯的公司维持了三年多,资金链就崩了。公司是他自己作垮的。
那时公司已经小有规模,吸收的资金越来越多,银行给的单子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投资需求。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几个本地大哥,瞄上地下赌场,他开始频频出入各种隐秘赌场,一来二去,赌场的市场没打开,自己倒染上了赌瘾。开始只是小赌,后来越玩越大,成夜成夜泡在赌桌上,一次下注就超过十万,再几十万。他甚至染上了毒品,从孙Math变成了孙Meth(冰毒)。不出半年,钱就花的一干二净,他的公司刚开始是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后来干脆公司大门紧锁。
孙麦斯找爹妈四处帮他融钱,老两口不知道自己儿子状况,以为有大生意,资金短缺,便发动了所有社会关系替他筹款,凑了一千多万。没想到拿到钱的孙麦斯,跑路了。
谁也找不到孙麦斯,讨债的人为了找孙老师,把学校给了堵了,孙老师又被学校劝退回家里。
儿子跑路之后,孙老师变卖了自己名下所有的财产,可是债务还差500多万——欠款的许多钱都来自朋友和同事,他一辈子骄傲,老了却颜面尽失。他再也无心经营他的文学,每日疲于应付上门讨债的人。
我爸最后一次见到孙老师,是在乡下的老房子。孙老师家的大铁门上被泼了血红色的油漆,房顶上生满杂草,房子年久失修,厢房塌了一半,老两口就住在危房里,室内空气阴暗潮湿,飘满霉味。
我爸说,他跟几个同学带了些吃的,来看孙老师夫妇,敲门,等了好一阵,孙老师才从铁门缝里探出头来,先是一愣,然后叹了口气。
“孙老师当时头发白完了。”我爸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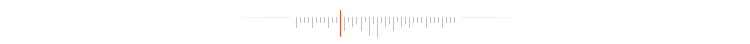
但我爸万万没想到,一个礼拜之后,孙老师夫妇就选择了自杀身亡。在一处小树林,晨跑的人发现了孙老师夫妇的尸体,两人蜷缩树下,身体像两张打开的弓。
两个人都是喝农药死的,瓶子丢在一旁,一滴不剩。孙老师穿着西服,白衬衫,蓝领带,老伴披着紫色皮草,仔仔细细画了妆容。两个人手挽着手,打扮得干干净净。
小树林身后是小小的山丘,河水在他们面前转了一个弯。
▍推荐阅读:
出租车司机说他有五套房,问同龄的我读博有什么用?
没错!大一挂了9科,如今我笑着毕业
“挖人大战”后,长江学者都在哪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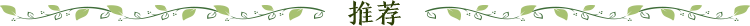
学术中国助您提升英文论文内涵及写作技巧,
让参加国际性研讨会的你得到更多有利的经验,
让您更有自信的介绍自己的研究
长按下方二维码查看详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