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国科学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华东理工大学徐汇校区和奉贤校区相距40公里,该校教授戴升通常会在学校班车上利用往返时间回复邮件。这两年,发件人中多了不少孩子,邮件内容稀奇古怪。
“我今年5岁,能够把元素周期表背下来了”“为什么氮这一章要介绍氨”“相对原子的质量和我查到的版本不一样”……若说这些邮件有什么相似之处,大概是里面都会有这样一句话:“我是《118化学元素》的忠实读者。”
《118化学元素》由“85后”戴升和他的“00后”学生张馨予合作完成。自2022年8月出版以来,该书已重印20余次,总印数超过40万册,多次在化学元素类图书全国月销、年销中排名第一。读者中既有学龄前儿童,也有退休的老者。
1月14日,戴升受邀参加一场冬令营活动,以这本书为切入点,和现场的中学生们分享中国文化和科技中蕴含的化学元素故事。
在讲座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寄语现场的同学们:“通过化学元素去了解世间万物,用科学知识去理解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不断扩宽自己的知识面,找到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领域。”

戴升
不设限的人生
如果在华东理工大学的校园里偶遇戴升,可能会把他当成一位学生。戴升身材颀长,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书生气。
他的办公室在费林加诺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是学校的地标建筑之一。在这座古典气派的大楼内,隐藏着精密和尖端的实验设备。
其中,戴升最熟悉的是位于一楼的电子显微镜中心。他的研究方向就是利用电子显微镜表征技术在原子尺度观察化学反应中催化剂的动态变化,进而解析其活性位点与反应机理,明确构效关系。
“催化”一词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催化剂在科研以及工业中也早已广泛应用,但人们并不清楚催化剂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催化过程也因此常被比喻为难以窥探的“黑匣子”。
“我们的研究是把传统宏观的实验过程搬到电子显微镜的空间里,直接观察‘黑匣子’里发生了什么。”戴升说,“这非常有意思。既能够解答科学问题,也能服务于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等工业应用。”
戴升无疑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科学家。目前他已经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共同)身份在Nature Materials、Nature Catalysis、JACS等期刊发表50余篇学术论文,部分研究成果已成功转化为产业化应用。
但作为一名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博士,戴升在确定研究方向时也经历过转型的“阵痛期”。
刚加入华东理工大学时,他主动将研究方向转向化学、材料、化工交叉的催化剂方向,期间学习了很多化学化工的知识。每当对某一个方向比较了解后,戴升又继续扩展新的领域。目前除了催化剂,他所在团队的研究方向还包括半导体材料、新能源等等。这意味着,他需要不断跳出已有舒适圈,扩展自己的知识面。
“我觉得人就是在不断尝试中挖掘自己的可能性。”戴升说道,“我小时候想当科学家,就努力往这个目标靠拢,最后发现做得还不错。如果结果并不如意,那就说明这并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也可以借此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
对于学生,戴升并不要求他们每天打卡,但鼓励他们多进行自由探索,主动学习不同领域的前沿知识。他常常和学生说:“技多不压身。掌握的技能越多,未来的舞台就越大。”

团队合照
让戴升欣慰的是,目前实验室的交叉学科氛围很浓厚。学生们愿意由科研课题这个“点”不断扩展知识“面”,相互之间也经常互相学习帮助。“他们最后获得的是化工学位,但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继续从事相关的行业。只要掌握了学习方法和技术,他们就能够有更多不同的选择。”戴升说道。
“中国特色”的元素周期表
当被问及来时路,戴升讲了一个故事。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占领了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尼尔斯·玻尔上了“黑名单”,被迫逃往国外。出发前收拾行李时,玻尔看着诺贝尔金质奖章陷入了沉思。如果把奖章带在身边,他一定会在过海关的时候被认出来;如果将其留在家中,这份荣耀的象征一定会被纳粹毁掉。
玻尔很快想到了办法,他把奖章带去实验室,配了一批王水,再把奖章放到溶液里溶解掉。若干年后回到祖国后,玻尔又利用化学反应,把金从王水中置换出来,并将之打造成与原来一样的奖章。
这个故事让戴升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了非常具象的理解。正是科普书中一个个神奇的科学知识,让少年时的戴升见识了一个和日常生活全然不同的“魔法”世界,由此在心底埋下了做科学家的种子。
往后多年间,在清华大学完成本科与博士的学习、出国深造再回国,戴升从一位科学知识的获取者变为发现者,对科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出口,将多年所学反哺社会。
终于,他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2022年元旦刚过,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一佼联系戴升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出版社正在策划出版一本有华东理工大学特色的科普读物,为70周年校庆献礼。“如果你的精力不够或者担心影响科研,可以直接拒绝,我们十分理解。”和戴升介绍完基本情况后,王一佼补充道。
“我的第一反应是,小时候看过的那么多科普故事,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戴升告诉《中国科学报》。
结合学校在化学化工方面的特色,戴升和出版社很快就达成一致,写一本化学相关的科普书。而元素周期表,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经过前期调研,戴升发现,中学生们在学习化学时,元素周期表让他们很是头疼。元素周期表是化学学习的基石,然而众多的生僻字却成了不少学生的“拦路虎”。同时,当前教材和科普读物中的知识点多源自国外,即便案例生动,但因涉及外国人物或场景,往往难以让学生产生共鸣。
以常温常压下唯一的液体金属汞为例。国内市面上有不少化学科普书是由日语翻译而来的,里面提到奈良大佛表面镀的是汞和黄金的合金。由于中国民众对奈良大佛了解不多,且鲜有机会实地接触,因此难以通过这个例子理解汞的特性。
“其实用汞和黄金作为合金去镀金,最早源于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古人就发明了鎏金技术,即把金和汞合金均匀地涂到青铜器表面,通过加热使汞挥发,留下金的薄层。”戴升解释,“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既不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阻碍了孩子们对科学知识的深入学习与理解。”
针对这些“痛点”问题,戴升在编写书时,特地做了一些设计。《118化学元素》整体是可爱的手账风格,穿插着生动的漫画和小提示,同时每个元素都用拼音进行标注,避免读者因为对字陌生而产生的畏难情绪。
更重要的是,书中特别设置了“化学元素与中国”板块,用贴近生活的例子拉进和读者的距离。如陶瓷的主要原料是硅酸盐、硝酸钾和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相关、锑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标准值是中国科学家测定的……
“让孩子们从小树立文化自信,熟悉中国的故事,也是我们国内科研工作者有义务做的事情。”戴升强调。

戴升在分享《118化学元素》创作的故事
出乎戴升意料的是,这一原本为中学生编写的书,最后竟然老少咸宜。除了文章开头给他写信的学龄前孩子们,也有不少退休的老人和他讨论书中细节。一位老年读者感慨“我家里就有青花瓷,但是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这也和化学有关系”。
这让戴升很是振奋。“很多人一听到化学,首先想到可能是有毒试剂、化工厂爆炸等等,因此有一些误解。《118化学元素》封面上有一句话,‘用元素重新认识万物’。我想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的。”
“只要认真去做,结果总是会好的”
《118化学元素》的成功,激励着戴升继续开展更多科普相关的工作。如今的他经常受邀参加中小学以及社区的讲座,以化学元素为起点,扩展背后的更多故事。戴升还在策划其他学科的科普书籍,其中,第二本关于物理的科普书籍也将很快面世。
同时,他还经常为来到费林加诺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电子显微镜中心体验的孩子们,耐心讲解电子显微镜的工作原理。

戴升在介绍实验室的工作
事实上,电镜中心本身便是一个绝佳的科普场所——还有什么比让孩子们亲眼见到神奇的微观世界更合适的方式呢?
“这是我从头参与搭建起来的。”说起这个,戴升颇为自豪。
2019年,戴升结束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博士后工作,加入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很快,他就接到了一个“大活”:参与电镜中心建设的工作。
戴升对电子显微镜十分熟悉,但要说从打地基开始从头搭建平台,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我告诉自己,没必要杞人忧天,脚踏实地把每一步都做好,结果一定会很好。”
这一年,戴升34岁。在组建实验室团队的同时,他经常戴着安全帽出现在工地上。他将之视为“升级版”的装修,带着“用户”思维参与其中。
别看电子显微镜是个“大块头”,实际上十分“娇气”:环境里湿度大了、温度高了、电压不稳定了,都会影响最终的成像效果。为此,戴升曾通宵测量环境中振动条件对电子显微镜的影响——学校旁边就是地铁站,需要考虑地铁经过时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戴升几乎把多年学习和工作的全部经验都用上了,并在此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从管理到工程,不一而足。而其中一些朴素的解决方法,也时常让他拍案叫绝。
他们曾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大楼内部设有台阶,而他们需要将一个重达一吨的电子显微镜主机安全运下。若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让仪器在台阶上磕磕绊绊地“下楼”,那么仪器即便被运到了目的地,也可能因受损而无法使用。
最后,戴升和工友们讨论再三后,想出了一个“低成本”的方案。他们搬了几千块砖,堆砌成一个和台阶一样高的平台,小心翼翼地把仪器放在平台上,四角再垫上千斤顶。一切准备就绪后,慢慢把千斤顶往下降,同时一层层地把砖撤下,就这样把仪器安然无恙地运到了指定位置。
在戴升和团队的通力合作之下,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需要返工的问题。2020年底,所有仪器完成验收。不久后,中心正式开始运行,服务于校内外的科研团队,由戴升负责日常的运维工作。短短几年间,已经有多项突破性成果在这个电镜中心诞生。

戴升在电镜中心指导学生
2024年12月2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公布并施行,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把科普放在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强调加强科普队伍建设。2022年以来,戴升做了不少科普工作。他经常受邀参加中小学以及社区的讲座,以化学元素为起点,扩展背后的更多故事。他的工作也变得越发忙碌了。他需要越发精打细算自己的时间——50%用于科研和实验室管理,25%用于教学,25%用于科普,跑步的时候想想科学问题,碎片时间记下一个科普知识点。辛苦,但乐在其中。“我是一个可以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的人。我喜欢我正在开展的每一项研究,并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前沿的科研成果。同时我也期待有一些孩子,因为看了我写的科普书而对科学开始感兴趣,最终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戴升说道。
编辑 | 方圆
排版 | 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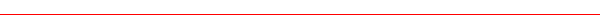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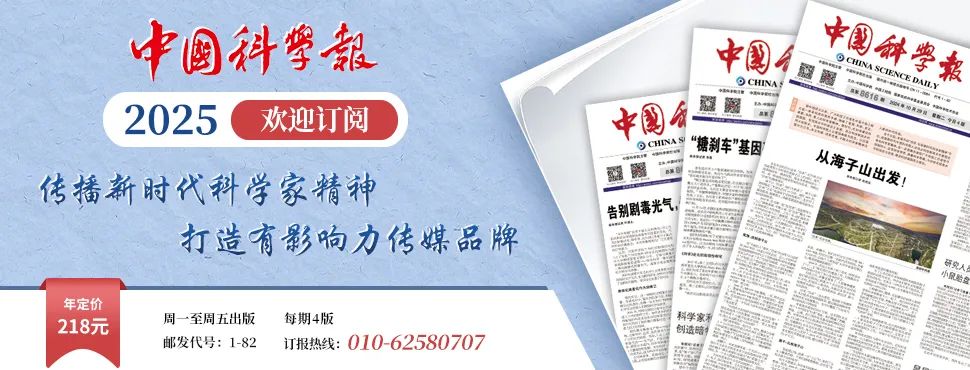
合作事宜:[email protected]
投稿事宜:[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