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76年,任何我们想要的都可以实现;2076年,转基因人类遍布全球;2076年,人造生命在地球上到处行走;2076年,人口崩溃,数千人迁移至火星;2076年,文明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
以上是著名的New Scientist杂志新做出的震撼人心的预测。尽管用了2万字长文来描述各种可能的人类画面,但这本权威科技杂志仍抱有足够的乐观和善意,并认为,
无论情况多么糟糕,到那时人类仍将是主宰。
然而,乐观的态度固然重要,但当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的技术以指数级不可控的速度发展时,50年后的事实或许远比我们想象中可怕的多!
人、社会、技术、文化、文明这几大关系将变得前所未有的凌乱和复杂。

早已不屑的“天命”和喧闹的技术表演
过去十几年,新兴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发展,让全球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
交媒体颠覆了人与媒介的关系,改变了信息乃至舆论潮水流动的方向;生物科技颠覆了“物竞天择”、“生老病死”的“顺应”理念;人工智能颠覆了人类“唯我独尊”的狂妄自大,甚至设想人和机器广泛共生。
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对“上帝”安排的天命如此不屑,人类极具渴望地希望“做出改变”,希冀“改变一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类最可依赖的便是“对技术创新的追逐”,技术成为最尖锐的工具。甚至有时,我们在“追逐”时,已经忘却了“为何要追逐”,只知道这是一条只要进来就难以停下的时空跑道。
人工智能领域的竞逐和厮杀,各大技术公司的极尽能事、争相布局和拼命追赶,以及大众对“人工智能战胜人类”的欢呼雀跃;马斯克呐喊的十年内将人类送上火星的伟大计划;每一次热潮技术概念的哄然兴起而又悄然放下;资本对技术的围猎……
我们似乎置身于一个万众舞台,木然看着舞台中央的各路拳击和选手们激昂的宣扬,宣扬“我们会拯救你”,但两手摊开的万众却茫然的问:
“为何要拯救我?我是否需要被拯救?”
那么,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和思维来考虑这个问题会怎样?比如“如果我们不需要你所谓的拯救,我们会怎样?会活的更不好吗?你的拯救一定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吗?”
也许这样的反问会让我们瞬间心底通透了。
为了创新而创新,那为何要创新?
对技术的疯狂追逐成为一种“兴奋剂”,我们过去十几年凭借这样的“动力”,利用新的技术工具对世界和人类生活做出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远远超过人类在过去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的时间里所做的努力和进步。
对技术的拼命追逐和技术由此造成的改变,已经带来了时间和空间最大程度的压缩,而在这种强程度的压缩中,人类原本还需要慢慢体验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整个物理空间、文化、生存状态、自我意识等等也将会快速被压缩。正如New Scientist最新的预测一样,
到2076年,一切都来的那么快,而相应的不可预知的问题、灾难也发生连锁反应,接踵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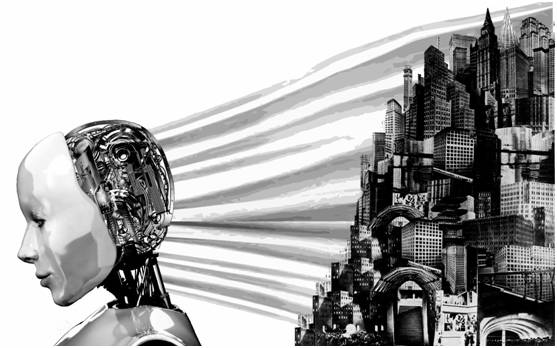
这种压缩究竟会带来什么?
所谓“尽人事,听天命”的传统文化,早已不能让人类静心顺应,人类在尝到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的甜头后,野心膨胀的难以克制。
总有一天,我们会为了技术创新而创新,而忘了创新到底为何,创新仅成为一种机械式的指令。
就像最大速度的汽车突然失灵,难以控制,我们只知道必须跑下去,停不下来。
这种压缩仍在继续,甚至压缩的程度会越来越强。如果科学家预测的技术奇点真的会发生,那么达到临界值时,
技术的不可控是否真的难以避免?
刘易斯·芒福德早在几十年前出版的那本有名的《技术与文明》中就提到,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当中,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和器皿总体来说都是他自身机能的延伸。
无独有偶,传播学家麦克卢汉也提出,媒介是人身体的延伸。这两位并不十分搭界的人物其实都是技术决定论者,
他们强调技术了与文化、媒介、人类之间的关系,却又反思,技术相应地会给文明带来的影响。
然而,他们可能都不曾预测和想到,技术和工具在过去十几年甚至过去几年的膨胀式快速发展中,已经超出了“机能延伸”的范畴,这种延伸甚至最终是人类难以掌控的。
何谓人还重要吗?人类是否会更加孤独?
尽管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大大延伸了人类机能,并且在某些领域可以帮助人类做出更好的判断。
不过,我们并不满足于此,
我们试图创造出智力更高、拥有人类情绪、理解人类语言、能与人类自然交流甚至终身相伴的人工智能顶级机器人。我们试图让机器人拥有人类面孔,变得越来越聪明,让他们具有意识,能够像人一样迭代成长,具有创造性能力,最终达到科幻影片里那样的高等水平。
如果机器人的智力超过人类还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么当机器人自身具有情感、情绪并且能感知外在情感和情绪时,
人和机器的定义和内涵可能发生重大改变。
另外一方面,当人类身体植入感应器跟踪健康状况、传输健康数据时,当人类身体越来越成为各种技术设备的界面时,人类身体便成了搜集信息和形成反馈回路的工具。
人的属性将会发生变化,何谓人,何谓机器,人机界限变得愈发模糊。
或许这些都是外在的表现和改变,而另一个精神层面的困顿正在发生。
我们希冀机器人能掌握更多人类独有的情感、情绪等属性,
其实质是希望我们能得到更多陪伴,解决现实中的孤独、社交关系问题。
然而,机器的陪伴是否真的能消除孤独,还是更加扩大了人类内心的孤独?
当然,先说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社交媒体让人们过分投入于线上社交关系,时间和精力极度分散。即便现实中两个人相邻而坐,但他们早已分属两个世界,并在智能设备上扮演着多样人生。
人们试图在智能设备上从虚拟的或永远难以相见的社交关系处寻求安慰,但却忘记现实中关系的互动和维系才能增加亲密感,是消除孤独的良药。
所以,当人们关掉智能设备,结束线上旅程时,世界又回到了孤独。
于是,
人们又迫不及待地希望打开设备连接线上关系,渴望打破失衡的心理状态,但这只会越来越加剧现实中的孤独感。
这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社会文化困局,我们患上机器上瘾症,我们的肉体生活在同一世界,但精神早已在各种智能设备上分崩离析。我们在一起,但我们又难以名状的孤独。
而这,仅仅才是智能设备的突飞猛进带来的。
那么,人类的这种孤独感会因未来智力机器人的陪伴而解决吗?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词“AlongTogether”(群体性孤独)来形容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交关系的影响。她对人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进行了长达15年的跟踪研究,她发现,当人试图依赖机器设备或机器人排忧解难时,说明他从现实社会关系中寻求不到安全感和满足感,甚至与现实社会中的关系格格不入,因此希望从跟机器人的亲密关系中寻求慰藉。
所以,当人们越是依赖智能机器人时,说明人越来越会陷入“孤独”。

正如电影《Her》中那样,一个男人处理不好现实生活问题后,意外遇到女智能机器人。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知己并沉浸其中,所以他觉得不再需要过多跟现实世界的人交流,可以避免许多争吵和麻烦。
然而,最终结果是,这位令人信赖的机器人并非他一人独有,而是成千上万其他男性的知己。
这种绝望和迷茫已让他再次沉入谷底深渊。
“欲盖弥彰”或许更能准确反映这种矛盾状态。于是问题又来了:
我们真的需要这种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大量普及存在吗?
如果不需要,那么我们为何拼命推进,意义在哪里,是否徒劳?
如果需要,那么人类自身问题该是多么严重?比如社交能力退化、自我人格健全等问题?
借助机器人是否反而让问题更加突出?
技术创造的“过度充裕”比贫穷更可怕!
技术进步让所有物质的生产都极高程度的自动化,这将大大减少物质生产的成本,让商品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丰富,甚至达到共产主义。
到那时,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如何消费如此多的东西?
我们将不再困扰于物质匮乏和贫穷,而是受困于物质极大丰富,这将成为人类面临的头号问题。
这样的“过度充裕”也很有可能给人类文化带来冲击。在物质匮乏时期,人类努力创新技术,发展技术,让技术工具为创造更多物质财富而拼命。人类文明从发明石器开始,也代表着人类开始学会用工具征服自然,改善生存环境。
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时代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在上千年甚至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形成了追逐文化、竞争文化、创新文化,而这一切更多时候是为了解决不完善的外部环境以及因匮乏带来的诸多问题。
所以,人类总是保有一腔热血,自觉承担着“改进工具”的责任,改进工具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生活更美好、物质更丰富。
然而,我们是否想过,
当各种新兴技术压缩式、指数级快速发展时,目标的实现时间也将会大大缩短,我们离
“过度充裕”
越来越近。
那么,当人类控制各种技术为我所用,解放人力,解放人脑,一切都顺手可得,此时的人类精神又会是怎样的?
我们是否会因“过度充裕”而产生“选择恐慌和焦虑”?或者麻木不仁地任凭机器安排?我们是否会“精神空虚”甚至“不思进取”?因为一切因匮乏环境而深深扎根的竞争、超越,在过度充裕、唾手可得的时代变得不合时宜,到那时,我们是否会产生一种更难以根治的“精神或心理疾病”?
同时,物质的极大丰富可能会进一步带来疾病的多样化发展。因为,起初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设计的人类基因是为了应对物质匮乏的环境,而当面对物质的极大丰富时,人类基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好?
上帝创造了人,人对上帝敬畏。人类创造了技术,但技术并不会敬畏人类。
或许现在才是最好的时代
,这个“最好”既相对于漫长的过往人类史,又相对于无法想象和预知的未来!
50年后的人类世界,你能想象吗?
本文作者常宁长期跟踪、关注并报道世界新兴科技发展及商业化进程;专注新媒体传播、受众和用户调查研究。
本栏目为DeepTech“社评专栏”,
探讨一切与技术有关的深层问题!
欢迎关注DT君的科幻电影公众号:


招聘
编辑、视觉设计、
视频策划及后期
地点:北京
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