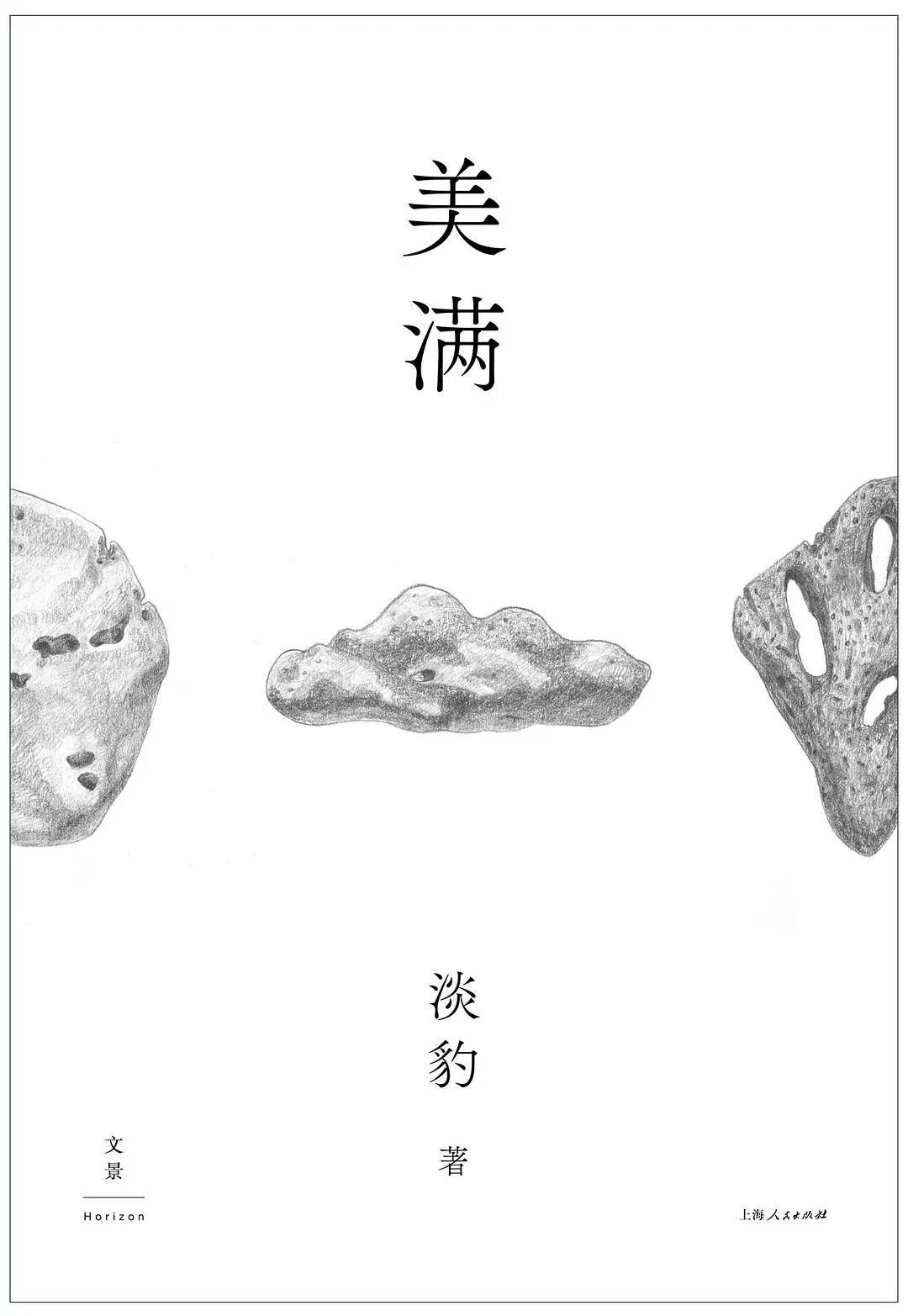
中国人信仰家庭,准确地说,信仰得体的家庭。美好生活必有妥帖的节奏,适龄结婚、按时生育,爸爸妈妈和孩子,这是宇宙正常运行的前提,一切人类活动的大型布景板。如果生活中有什么事值得写进小说,那一定是溢出了布景板的意外。
二十年前史诗式小说一度流行。一家人跨越几十年的悲欢离合,书写的对象是风云变幻、社会鼎革。家庭成员反而是不要紧的,只要排布匀称,以便承载大事件的重量。《美满》的写法则完全相反,没有意外、反常、动荡,不过是寻常生活一针针地编织。九个故事中,淡豹细密以至于执拗,小型探照灯向着布景板一寸一寸打过去,凝视、描述、评判。思虑一秒钟可以有多少次回转,淡豹就用多少篇幅记录。
寻常生活中自然也有大事发生。但对《美满》的作者来说,大事不过是故事的开头,后面跟着漫长的周而复始的仿佛永无休止的时间。《山河》写的是非婚生子。没有父亲的女儿在想象中勾勒父亲的存在,逐渐发现故事的真相,最终先后与想象中和现实中的父亲作别,重构、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理解了母亲二十几年来的人生。《父母》则以一起恶性校园伤人事件开头,讲述失去唯一的孩子之后,母亲如何重新发现属于自己的身体、空间和时间。淡豹的叙述有急促的节奏,但又带着某种疏离,像是对叙述的再叙述,总在定义与判断,不断发表小型演讲(正如《父母》的主人公“妈妈”)。
《美满》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生育。作者几乎在每一篇中大声质问生育的意义,又在每一篇中给出不同的答案。《女儿》中的生育是一道裂缝,隔断了他和她。在《养生》的结尾,生育则显现出某种救赎的微光,然而这答案给得如此不可靠,带着明显的犹疑。《山河》里的生育则更像是传统的循环,或答案未知的谜题。更多的时候,生育带来一种轰鸣的复杂回音,比如《过火》《父母》和《乱世佳人》。生育是家庭生活中盘旋的主题,或者家庭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或许因为这主题过于强大,以至于常常被处理得理所当然。淡豹带着好奇、也带着焦虑,重新对天经地义的生活方式提问,跌跌撞撞地展现着真相。
《美满》在尝试新文体上的雄心令人印象深刻。《养生》的开篇是令人极为不适的翻译腔,从句子结构到用词,简直可以一字字译回英文。接着是主人公的自言自语,另一种文体,独白滔滔不绝,与翻译腔形成微妙的互动。文体本身展示了主人公所处的空间与情感的夹缝。这尝试如此成功,营造出格外深沉的寂寞。《过火》则是另一种风格,情绪包在方言用词里,显得钝、也节制沉静。《女儿》据说是最为难读的一篇,但也可以说最能表现作者的语言风格。《女儿》所描述的,是一团模糊的混杂着气味、光线、图像的场景。故事的男主人公在半醉的一瞬中忆起往事,已反刍多次的情节闪现出全新的解读,往事重新呈现,主人公带着抗拒带着惊愕。淡豹把句子打碎,缀连起细小的、不稳定的感受。
小说的语言风格和描述的对象直接相关。与古典小说完全相反,淡豹最不在意的就是故事性。或许为此,小说在人物命名上刻意地漫不经心——另一种对传统小说写作方式的彻底抗拒。除了《过火》中的一家人有名有姓,其余都是代词,或者近似于代词,佳莉、佳明、李先生、李太太、爸爸、妈妈、我、她、他,没有名字,只有情绪、感受、关系。《美满》刻画的是海面上船身后长长的水痕,是后脑骨絮絮不休却没人能听见的声音。一个场景,一个判断,对判断做反思,对反思再做评论。淡豹像一个过于敏感的孩子,充沛饱满,能捕捉到空气中每一个信息素,对世间事充满不厌其烦又略欠节制的表达欲。
短篇小说的困难在于结构。作者抛开情节的限制,专注于念头和意图。这种表达方式若不加节制,就容易造成结构上的散漫。《乱世佳人》的三个部分中,“小李”一部分在结构上似乎必不可少,但表达上则拖沓无力。问题最为严重的,恐怕还是《你还记得在上州给我变魔术吗》,作者使用了冗长的独白、对话、插入的故事和一层又一层的嵌套,然而因为无法控制插入故事的节奏和关联性,显得虚弱冗长。
淡豹在结构上另一个大胆的尝试是不断插入其他文本。比如《女儿》中的惠蒂尔小镇,通过引入节外生枝的复杂描述引出小说的高潮。但更多时候,插入的文本突然而密集出现,并不太在乎照应与回响,让人怀疑它们真实的意义。《旅行家》和《你还记得在上州给我变魔术吗》中的引用尤为泛滥而支离,挑战着已经摇摇欲坠的结构。
淡豹在生活最平常处探索,也平淡、也荒诞,也离奇、也寻常。与其说淡豹的小说是对生活的转译,不如说她的故事与生活形成互文。大量可识别的现实中的细节,正是小说所描述的故事的注释,文本与生活相互说明。只是这互文偶尔失控,注释的重量压过文本,使读者疲累而失去线索。然而淡豹的尝试值得肯定。当我们想要讲述新的故事,就需要新的语言。在小说的后记里,淡豹说,“这些小说,里面出现‘黑头’五次,‘尼采’和‘阿尔都塞’各一次,‘鼻毛’两次,‘洗牙’两次,‘蒸脸’一次”。我注意到的是,九篇小说里,出现妊娠痒疹一次,盆底肌肉一次,妇科疾病一次,孕期失眠一次,还有飞机上反复跑洗手间的上了年纪的妇女,没有时间出轨的家庭主妇。淡豹若无其事地把这些细节放在故事的底色中,琐碎的肉体的痛苦,可见的不可见的焦灼。如果过去没有小说描述过它们,那么就该创造一种新的语言,重新塑造漂浮感与力量感,重新书写痛苦的形态。
在《乱世佳人》中,李先生临终前病房的窗外,电线杆吊着一轮黄澄澄的圆月亮。让人想起《倾城之恋》中浅水湾饭店窗外那被藤花挡了一半的月亮。或许是同一轮。然而月光照亮的不再是传奇,而是一对平凡夫妻。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