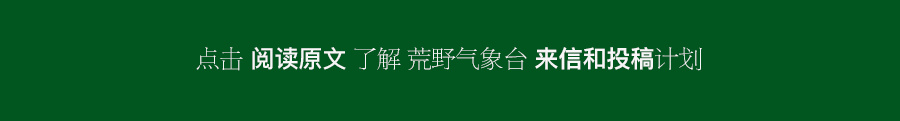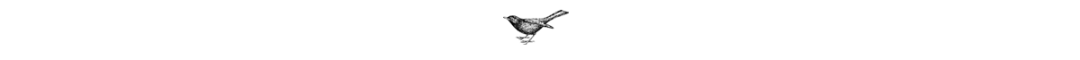台长:
先向荒野气象台问好!听说你们即将前往欧洲,我自己也要马上要开始新的旅程。新的旅程总是令人倍加期待,事实是,我早已迫不及待地选好了飞机上的座位。
说到选座这个事情,后来我发现,大家在挑选座位的时候,所花的心思并不比挑选航班的时候要少。这也能理解,是否能挑选到自己想要的座位,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的旅程是否顺心如意。
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千方百计地想要拿到靠窗的座位,以便欣赏万米高空上的壮观景色。即便是现在,我也常常坐在飞机尾端靠窗的位置,不但可以看风景,也能将头靠在机舱的内壁上,算是比旁边多了一份安稳。
 PHOTO - Josh Anon
PHOTO - Josh Anon
飞机陡然升空,升到万米,开始平稳飞行,窗下的滚滚白云似波涛起伏变化万千。没有一个确切的对照物,每小时可以飞行800公里的客机行驶在空中竟有种运动缓慢的感觉,一如轮船行驶在无边的海洋里,感受不到相对速度。海中尚有海鸟与鱼群,而万米空中则清净得有几分寂寥感。
有时要乘飞机飞越半个地球到美国或者加拿大,飞行时间有14个小时左右,很多人选择用这段时间来倒时差,保存好精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工作或旅行。但是在长途的飞行中硬熬过十几个小时总是心有不甘,想在在飞机上给自己找点事做,而这段时间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可以在高空鸟瞰极地风景。

由于地球不是一张平面,从北京飞往美国东部的航班会纵向穿越北冰洋。千里冰原在一个小小的椭圆形窗口展开,能够令万吨巨轮沉没的冰山此时如同纸张的褶皱,绵长的山脉在我们眼中变为细腻的纹路,令人忍不住想要轻轻地触摸,感受北极冰架的摩擦力。
在一次前往新泽西州的旅途中,凌晨时分,飞机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飞行,广袤的地球表面一半沉睡在深夜中,另一半则已经迎来了灿烂的朝阳。而极目望向远方,地平线已经弯成了圆弧,阳光洒在大气层中泛起金色的光晕,而那个犹抱琵琶的滚滚火球仅仅是冒了个头,就将刺眼的光线直射入机舱内,引起了正在小憩的乘客的一阵骚动。空乘此时走过来善意地提醒我关上窗户,我突然意识到整个机舱只有我拉开了窗板,匆匆关上后也不敢去直视身后幽怨的目光。

还有一次,在前往伦敦的飞行中,飞机穿过气流开始据烈地颠簸,这种感受在机尾处尤为强烈,窗外的云层也沸腾了,仿佛是积聚了巨大能量的水汽喷薄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机体,与此同时,我晕机了。一阵头晕目眩后,我强忍了数个小时的反胃感才终于熬到飞机降落——而坐在机尾的我又是最后一个才能出去的。
自那之后,我便更愿意选择坐在靠近机翼的地方,虽然要忍受引擎巨大的轰鸣声,但只要戴上降噪耳机,就可以享受难得的清净与平稳。在两侧机翼上方各有一处安全门,运气好的话可以抢到安全门后一排靠窗的座位,这里可以尽情地舒展自己修长的双腿,不用再忍受数小时的麻木,但与之对应的是窗外视野被巨大的机翼所遮挡,一路上只能与金属盖板互相陪伴。
凡事难以尽善尽美,靠窗的座位虽然坐享优越的风景,却也造成行动上的不便。有时候坐长途红眼航班,坐在靠窗的座位就意味着夜里去洗手间的时候得跨越旁边两位可能已经熟睡的乘客。

话说回来,机舱内,确切地说是经济舱内,最舒适的位置应该是第一排了。在一些航空公司的航班上,第一排的前面有一大片空间,足够两三个同行的朋友一起跳踢踏舞。而且这里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前方的天空,不像机尾一样只能向后看,这里没有机翼的遮挡,能够看到更远的地方。
而我至今仍未碰到过喜欢坐中间座位的人,一如在任何一种关系里面,没有人会喜欢被夹在中间。所谓选座的战争,一定程度上就是避免自己被分到中间座位之争。实际上,坐在中间也并不见得有任何实际的坏处,只是,人们总是天然向往更为优越的处境,尤其是当他们有所选择的时候。
虽然与充满未知的异国之旅相比,飞机上的时光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在选择机上的座位时却仍然有自己个性的想法,由此诞生的种种趣事无论是会变为日后的谈资还是社交网站上的照片,都是旅途中不可或缺的经历。
但如果不幸没有选择到理想的座位,那就多带一点糖果和巧克力安慰自己吧。
不知道荒野气象台的其他读者们坐飞机的时候喜欢选什么样的座位呢?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人和事?正好在这里,通过台长来问问大家。
墨西哥胖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