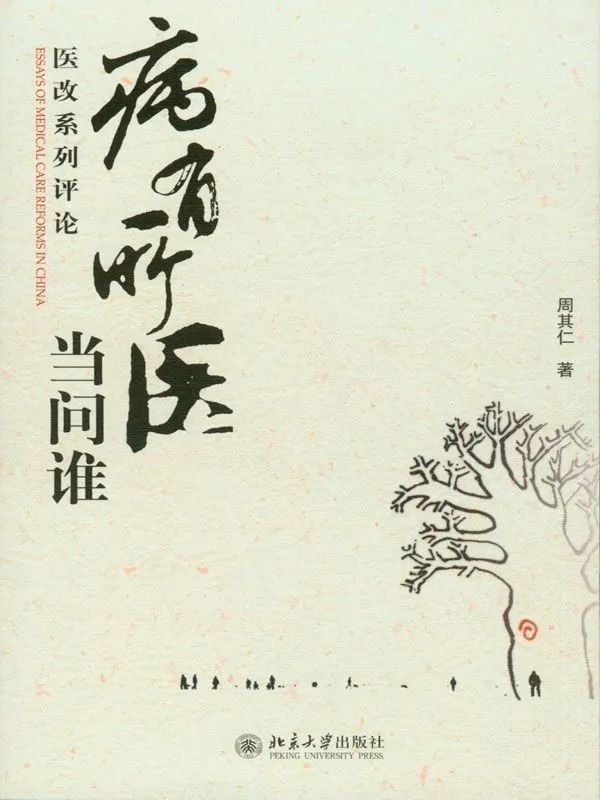
病有所医当问谁
作者:周其仁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8月1日
编者按:
2007年1月15日起,著名经济学家
周其仁
教授开始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医改系列评论,至2007年12月17日结束,共41篇。后于2008年8月结集成书《病有所医当问谁》出版。这本书纸质版已经不好买到,不过还可以在亚马逊购买Kindle电子版。我们也在这里转载当年文章,供您参考。
真理总是具体的 (1)
这算哪门子“市场化”?(2)
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3)
政府主导才是问题所在(4)
令人尴尬的“公立医院” (5)
医院甚于“招待所” (6)
医疗服务是开放最差的部门(7)
价格管制的重负(8)
“红包”是与非(9)
药的问题在哪里?(10)
国家药监局的教训(11)
相对价格至关紧要(12)
解读赤脚医生(13)
从赤医到乡医(14)
历史上的乡村医生(15)
农民缺医少药的原因(16)
全盘公费医疗是个梦(17)
不如人意的全盘公医(18)
批评里的教益(19)
重乡岂能轻城乎(20)
摆不平的城与乡(21)
不开放焉能兼顾城乡(22)
中医与西医的分叉(23)
行医资格的国家管制(24)
法外行医的空间(25)
需求膨胀与供给障碍(26)
管办合一是症结所在(27)
宿迁医改的普遍意义(28)
公共卫生是政府的首要责任(29)
“公用品”的消费与生产(30)
宿迁的医院改制(31)
医院本位论(32)
医院改制不容回避(33)
营利医院与非营利医院(34)
医疗服务的品质考核(35)
非营利医院以民办为优(36)
恻隐之心的经济学(37)
社保的初衷(38)
错得离谱的测算(39)
人人享受卫生保健的限制条件(40)
医改系列评论(结语)
医改的惟一关键是坚持改革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07年12月17日
本篇是医改系列评论的结语,主要说明一个意思,就是医改讲到底还是要坚持改革,因为只有坚持改革,才可能争取医改的成功。其实,已发表的40篇评论都围绕这一个中心下笔,在结语篇中特别集中强调一下,好让同意的和反对的朋友看个更明白。
有读者或问,为医改选定一个目标不是很重要吗?目标是纲,纲举目张,才能统领各项医改措施的落实,为什么不把“医改目标”看成医改的关键?我的看法,为中国医改确立一个目标固然重要,但是任何立意良好的目标,都要靠一套医疗服务体制,才能实际动员资源加以实现。目标定得再好,改革不到位,说了做不到,空中楼阁又有什么意思呢?
譬如上文讨论过的 “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本是世界卫生大会在30年前提出的全球目标。中国政府认同了这个目标,也把这个目标写入了历次政府文告。现在,2000年已经过去了7年,中国并没有做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再提“2010年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屡败屡战,精神可嘉。问题是届时再做不到,如何是好?干脆不设年限,一直喊下去,一直实现不了,于国于民,又何利之有哉?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也算不上始作俑者。我在评论里引用过发表于1958年9月的 《岈山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草案)》,白纸黑字宣布“公社实行公费医疗”。“章程”者,小宪法也,又经伟大领袖御笔亲批推广,立意当然伟大——“公费医疗”就是“看病不要钱”,应该是“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高境界!半个世纪过去了,你到那个公社所在地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可以作为对照的经验也有。1980年邓小平提出 “本世纪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翻两番”,到2000年硬就是实现了。为什么20年翻两番的目标可以实现?经验有两条,一是目标提得比较恰当,不是大而无当,怎样努力也做不到的;二是在农业、工业、商业、外贸、服务等产业部门,全面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和工作干劲,并转向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新体制。回头看得清楚,离开了经济体制改革,根本实现不了翻两番的目标。
医疗卫生的目标为什么屡次提出、屡次不中?关键就是没有好好改。早期是“政府包办”,后来经济发展,国家财力捉襟见肘,变成“包而不办”,然后就在全盘公医的框架里,搞一点“
医院创收”——就是市场准入不开放,行政垄断赚钱的“改革”。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部署卫生体制的改革,已经是1997年,离开“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只不过3年而已。1997年部署的医改到底又做到了多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看法是至今也没有全面推进。比如,对外对内开放、“管办分离”、公立医院改制、发展民营医院、松动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究竟实际做了多少?本系列评论初步盘查,结果发现迄今为止我国的 “医改”,根本还是一个“半拉子工程”,看起来“好像市场化过了头”,其实除了个别地区和个别环节,深层次的全面改革还没有开张。
据此我就无法同意,未来医改的基本内容就是“增加财政的卫生拨款”,并以政府大手拨款为前提,然后在“政府主导”路线下,重回“政府包办卫生医疗”的老路。有人认为过去是财力不足,所以“政府包办医疗卫生”才没有成功,现在和今后国力强大了,包办制就必定胜利。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无论国家财力多么雄厚,政府包办医疗服务体制都无法有效动员资源,无法满足人们在经济和收入增长条件下对医疗服务越来越多样、越来越高水平的需求。
甚至就连“合理增加财政对卫生的拨款”这样一个单一的目标,离开了牵动面甚广的制度改革,也不能切实兑现。这里,首先就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奠定公民纳税人对国家财力的支配方向、开支结构和增长的知情、代表委托、监督和决策参与的权力。没有这项改革,政府关于教育、卫生、民生的承诺,是难以兑现的。
更要紧的是,要在限制税收总比例的条件下,全盘考虑各项民生开销,如果像本系列评论指出过的那样,不降低其他政府开支却大幅度增加医疗和其他福利,那一定会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福利带来长远的负面影响。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过重的税负、财政赤字或多发票子,最后一定会给经济发展、就业增长以及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坚持改革的重要性还在于,任何以人民的名义——或者以低收入人群的名义——集中起来的“免费或低价的医疗服务”资源,并不能自动就变成人民或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没有相应的信息披露、监督和制衡的机制,许多听来美妙的体系,运转一段之后就难免老化和变味,成为少数人寻租、获取不公正待遇的“天堂”。以目前尚存在的“公费医疗”为例,行为扭曲严重,“过度医疗”严重,不但没有效率,也完全谈不到公平。未来的医改方案是不是认真部署改革这一块,人们有理由拭目以待。
本系列评论针对医改讨论中一种流行的思潮,坚持在分析上把医疗服务的不同需求与供给分开来进行处理。这是因为,流行思潮已把“公共卫生的公益性质”,不恰当地扩大为 “所有医疗卫生服务都具有公益性质”,而又把所有公益性服务,清一色地排除在“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体系之外。
我的看法针锋相对:只有公共卫生服务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益性服务,才需要明确政府的职责,并由政府运用合法强制力和税收资源来保证履行。即便如此,政府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向市场购买服务”的办法,组织市场提供公益性的公共卫生服务;只有当市场没有能力提供此种服务的时候,政府才必须亲力亲为,提供公共卫生服务。
至于不具备“公用品”性质的一般医疗服务,可以通过市场体制来供给。市场里涉及生命和健康的服务很多,也的确需要更为严谨恰当的监管,但没有经验和理论可以证明,凡涉及生命和健康的服务就一定要排除市场机制。在理念上,我不同意把涉及生命健康的服务与赢利性的市场活动对立起来。因为普遍的经验,其中也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生产服务领域的经验,证明只要坚持市场开放、竞争制约以及普遍的产权保障,营利性的市场活动才更显著而普遍地大幅度提升人民福利。约束下的赢利活动,对客户需求更在意、对成本节约更敏感,对服务品质和品牌更上心——这都有利于动员稀缺资源来增加医疗服务。
没有理由把一般医疗服务和药品生产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体系中排除出去。因为可以增加医疗服务的人力、物力、财力,没有一样不是稀缺的,没有一样不是在竞争的环境里被决定被动员的方向和强度。
举人力为例,一个年轻人可以学医也可以不学医,他或她可以好好学也可以不好好学,学成以后可以好好干,可以不好好干,正如一个医疗机构可以努力提供服务创牌子,也可以“等因奉此”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所有这些行为的“分叉”,取决于体制和特定体制决定的激励机制。体制和机制不对头,动人的口号天天喊,也没有用的。那样的日子中国人经验过,历历在目,没有反复“试验”的理由。
当下我国医疗服务最严重问题正是资源动员不足。我的系列评论用了很多篇幅陈述此情,为此很感谢编辑和读者朋友的耐心。可是临了,我还想提一句,为了防止医疗服务体制改革从“半拉子工程”变成“烂尾楼”,要不失时机地抓紧行业开放、管办分离、公立医院改制、民营机构准入和价格管制改革。
局部所见,不少最优秀的年轻人不愿意学医、医生和院长对自己的职业缺乏热爱和自豪、公立医院重新“行政化”并对经营亏损无所谓,民营机构和民间资本的预后不良和裹足不前——即使这些都不过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苗头,也值得为政者重视,因为中国整体的市场经济走势不可阻挡,任何一个行当的资源配置,无法脱离大背景而另搞一套的。
最后,济贫救困也离不开改革。从大处着眼,转型中国还有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提高人民收入的机会。譬如,政府至今严守的对农民土地非征用不准市场交易的体制,就不知道给我国的农民——也是地主——减少了多少万亿的财产性收入。从小处看,即使在给定的产权结构下,人民内部向来有济贫帮困的悠久传统。
问题是,这方面的体制也要选择对头,究竟是大政府、高税负、行政主导,还是对慈善行为减免税收、鼓励民间以多样化方式帮贫扶困?这在长远来看绝不是小事情。推进我国医疗服务的公平性,除了借鉴福利国家早期高度国家化、一体化、普遍性准则以外,还要对这些国家在福利病严重以后的改革经验给予同样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