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泽科尔·伊曼纽尔(Ezekiel J. Emanuel)是一位临床医学伦理教授,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副教务长。之前提到过,他写过一篇非常有个性的文章,题为《为什么我只想活到75岁》,实在让人侧目。

艾泽科尔·伊曼纽尔
他在文章中的观点是:“活得太久,是一种损失。它令我们就算不至于完全残废,但也步履蹒跚,老态龙钟,这种状态就算不比死亡更差,但无非风烛残年,所剩无多。它剥夺了我们的创造性以及为工作、社会和世界效力的能力。它改变了人们对我们的感觉、与我们的关系,以及最重要的,关于我们的记忆。在他们的印象中,我们不再活力充沛、忙碌充实,而是年老体弱、无能无用,甚至令人可怜。”
这位医学伦理专家还用统计数字来分析,为什么75岁是一个适于结束的年纪,他列举了众多理由。他也说明,随着科学进步,这个“适于结束的年纪”,会推迟到80或85岁。
他并不想抨击那些想要活得尽可能长久的人是错误的,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他说,他只想尝试描述自己一种“对幸福生活的观点”。他谈论的是,对自己寿命的期望,以及75岁后他希望接受什么程度的医疗保健。

这实在是太重要的一种声音了,在满世界都在期待返老还童或是重新谈论长生不老的21世纪。过了75岁,他说自己不需采取任何用以维持生命的干预。在长寿和永生的乐观主义之声中,这真的是一种不随流和主动选择的勇气。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我们需要先了解它。
“无论哪种疾病首先夺走我的生命,我都将随它而去。”他说,一旦活到75岁,他对自己采取的医疗保健方式将彻底改变。他不会主动终结他的生命,但也不会试图去延长它。今天,当医生们推荐一项检测或治疗,特别是那些会延长我们生命的检测和治疗时,他觉得有责任给自己一个不接受的理由。人们痴迷于运动健身、各种果汁、严格饮食、补充维他命和营养品……他觉得“这种对无休止延长生命的疯狂追求被误导了,也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100年前,著名内科教授奥斯勒的跨世纪教科书《医药的原理与实践》中有这么一段话:“肺炎或许被称作‘老年人之友’再合适不过了。患上这种疾病的老年人以一种急促、短暂、而且通常不是很痛苦的方式死去,这样他们不必去经历令其本人和亲友承受巨大痛苦的‘冰冷衰退期’。”

受此启发,他的理念是:
一旦活过了75岁,如果要去看医生,接受任何体检或治疗,就算再常规,就算没有痛苦,也得找个足够充分的理由才会去做,而这个理由不会是“延长寿命”。他会停止接受任何常规预防性检查、筛查或干涉。如果出现病痛或其他残疾,他只会接受姑息疗法。他不再考虑做什么结肠镜检查和其他癌症筛查,65岁时将接受最后一次结肠镜检查。
75岁之后,如果我患上了癌症,我将拒绝接受治疗。我同样也不会接受任何心脏压力试验,不需要起搏器和可植入微颤器,也不需要瓣膜置换术或者心脏搭桥手术。如果我患上了肺气肿或类似的疾病,频繁发作,总是要将我送进医院的话,我将会接受减缓窒息所带来的不适感所做出的治疗,但是我拒绝去医院。
那要是小病痛呢?流感疫苗就不用了。当然如果出现流感大流行,还没有活过完整人生的年轻一些的人应该接受疫苗或其他抗病毒药物。对抗肺炎或者皮肤、泌尿道感染的抗生素是个巨大的挑战。这些抗生素价格低廉、效果显著,因此我们很难拒绝它们。但奥斯勒提醒我们,与那些慢性疾病带来的衰退不同,这些感染带来的死亡不但迅速,痛苦也小的多。所以,我不会使用抗生素。
简而言之,不要对我采取任何用以维持生命的干预。无论哪种疾病首先夺走我的生命,我都将随它而去。

也许因为作者的医学背景,见过太多与疾病斗争的场面,医疗系统的文化常常围绕着那个微弱的可能性建立,那些临床医生们害怕自己对病人做得太少。但有时,对病人做得太多,也是同样可怕的错误。有人采访过一些老年科医生,他们常常面对老年病人,使用纷繁的医疗手段,与疾病做一场斗争。但当问到自己老了之后,是否也希望用同样纷繁的医疗手段时,他们的回答居然是:不用了,越简单越好!
这篇《为什么我只想活到75岁》发表出来,作者预料到很多希望长命百岁的人们将畏惧并反对他的观点。他揭开了一扇人们恐惧谈论和抉择的门帘,门帘之后是人生的终点。

他并非想说,想要活得尽可能长久是错误的,也不是谴责那些身心残疾仍想活着的人。他甚至都没有试图去说服别人同意他的说法。重点是,他是在尝试描述自己一种“对幸福生活的观点”。
你可以不接受他定义的75岁,但读完这篇文章,至少刺激我们也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对幸福生活的观点”,对自己的寿命的期望,在老年的下半场去接受什么程度的医疗。
我不是提倡将75岁作为完整、幸福生活的官方统计数据以节省资源、分配医疗护理,或是解决由平均寿命延长引发的公共政策问题。我只是在尝试描述我对幸福生活的观点,让我的朋友们和其他人思考他们该如何度过老年生活。
我希望他们能去思考,除了屈服于年龄的增长不知不觉带来的对活动和愿望的限制,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我觉得人们拒绝我的观点是很正常的。毕竟,进化的烙印让我们有着尽可能长久生存的动力,这也是自然的安排。因此,大部分人觉得将75岁作为终点是错误的。我们是永远乐观的美国人,我们对限制,特别是对强加在我们生命上的限制感到愤怒。我们确信自己属于例外。我也认为,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存在主义,人们都有理由对我的观点加以蔑视或排斥。
但是75岁为我定义了一个确切的时间点:2032年。它去除了试着活尽可能长久的模糊性。
这一具体数字,使人可以思考生命的终结,思考最深入的存在问题,思索想要为后代、环境留下些什么。“这最后的期限,也使得我们每个人问自己我们的消耗是否能与我们做出的贡献相当。特定的75这个数字,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忽视这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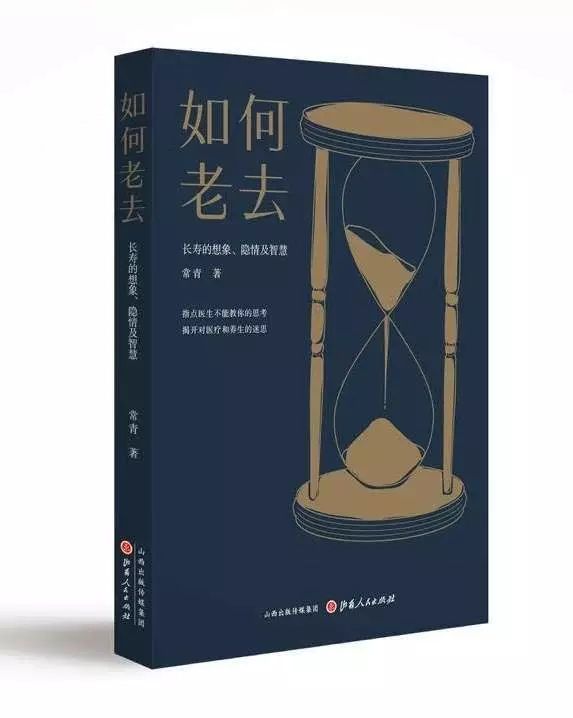 ▲
文章选自常青著《如何老去》
▲
文章选自常青著《如何老去》
(图片来自网络
)
⊙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转载请联系后台
。
点击以下封面图
一键下单新刊
「我们真的拥有亲密关系吗」

▼
点击阅读原文,
今日
生活市集
,发现更多好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