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中期,当赵宝刚、郑晓龙和尤小刚等人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为基地频出新作博得阵阵好评的时候,冯小刚却跌进了他事业的低谷。他和王朔成立了「好梦」公司,趁热打铁推出了几部影视作品。
但也许是受了王朔过分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的影响,他执导的电视剧《一地鸡毛》《月亮背面》和电影《我是你爸爸》都因为题材敏感或者包涵着强烈的负面情绪而遭到了禁播。

《我是你爸爸》(2000)
冯小刚也被扣上了「票房毒药」的帽子。他经过苦苦思考后,暂时放弃了批判现实主义式的带着尖锐嘲讽口吻的创作方向,重新开始借用「新北京话」所形成的语言魅力并转向了银幕喜剧的创作。
冯小刚再次借用了王朔《顽主》小说的故事形式以较低的成本拍摄了《甲方乙方》,并且第一次在宣传发行上套用了港台电影「贺岁片」的概念,影片大获成功。

《甲方乙方》(1997)
随后,他又以相同的方式接连推出了《不见不散》《没完没了》,每一部都在中国电影整体票房低迷的九十年代末商业大卖,他一扫此前的「霉运」,不但扬眉吐气,而且还成了拯救大陆电影票房成绩的灵药。
相比起冯小刚此前其他作品,在这三部影片中他暂时压抑了撩拨暗郁现实的反叛冲动,把温情亲民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他依然落脚在一些社会底层人民所关注的社会现实上,以对出国、暴发户、炫富、财富分配不均等热点问题的涉及开场,但口吻却从先前态度认真的「恶毒」嘲讽降格为没心没肺的温和调侃,以褒扬人性、塑造圆满、一团和气的皆大欢喜结局收场,实际起到了给社会市民阶层进行轻柔心理按摩的功效。

《不见不散》(1998)
北京话中指东说西、指桑骂槐、夹枪带棒、举重若轻的逻辑帮了冯小刚的大忙,让他可以一种看似完全「没正形」的口吻将一些揉杂着批判、讽刺、温情甚至是爱情的混合体以嬉笑的方式抛给观众,让他们开怀的同时也感到一丝甘甜和温暖。
这可以说是冯小刚获得票房成功的杀手锏,也是他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特点。这是为什么在随后的数年中无论他怎么转型,作品涉及了怎样严肃沉重而黑暗的历史和现实题材,都始终没办法把「搞笑喜剧制造者」这一顶他不太情愿戴在头上的帽子在观众顽固的印象中摘掉。
这样对冯小刚固执的「误解」一直延续到了2016年的今天——当《我不是潘金莲》上映时,许多人依然是抱着看银幕小品喜剧的期待走进影院,当然所收获的错愕反差也是不言而喻。

《我不是潘金莲》(2016)
在九十年代末新京味影视文化其实就已经走了下坡路,不厌其烦不着边际的贫嘴和调侃让全国观众尤其是南方观众感到麻木。而冯小刚几乎是靠一人之力重新将「京味儿」再次托上它在大众影视文化中的顶峰。
不过他也意识到这不是一条可持续走下去的道路。在以《大腕》最后一次消费「北京式调侃」后,他几乎全盘放弃了作品中的「北京化」倾向,转向了与类型电影接轨的形式化商业套路。

《大腕》(2001)
在这里还需提到的重要人物是背景经历复杂的叶京。同样出身于军队大院的他对曾经的大院子弟身份和经历所怀有的「执念」比姜文还要强烈,以至于他在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和电影《记得少年那首歌1969》中,反复围绕着军队大院和军队子弟的往昔经历做文章,几乎构筑了一幅大院子弟从满腔热血的少年到好勇斗狠的青年再到壮志未酬的中年的整体群像。
在这些作品中叶京不自觉地强烈体现出了大院子弟所特有的荣誉感、使命感甚至是优越感,但这也与2000年代北京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大院文化消解和溃散的整体时代氛围相脱节。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2006)
这是叶京的作品始终不能走入主流的主要原因。他甚至为了宣泄无法获得认同的失落感而创作和拍摄了电视剧《贻笑大方》,以喜剧化天马行空的方式嘲讽北京影视圈的追名逐利和寡廉鲜耻。这部无心插柳之作反而因为它极度夸张而荒诞不经的整体风格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一朵奇葩。

《贻笑大方》(2001)
2010年,姜文以一种诡奇的口吻拍摄了票房大卖的影片《让子弹飞》。它在表面上以痛快淋漓的态度讲述了一个黑吃黑土匪杀恶霸的民间传奇,但内在所包涵的却是一个带着反叛色彩的「异类」指导群众推翻压迫者的革命寓言。
他在影片中指点江山藐视群氓舍我其谁替天行道的高傲姿态再一次召回了那个似曾相识充满着优越感和叛逆意识的北京大院子弟灵魂,而这样的人物和他们的言行气概已经在中国银幕上消失已久。

《让子弹飞》(2010)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院文化在受众中影响力的消失和中国整体政治文化氛围的改变密切相关。一方面,大院和大院子弟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特权优势被网络时代的海量信息完全消解;另一方面,九零和零零后在文化上所关注的内容和他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大幅度变化,全面转向了虚拟化的快餐式交互互动。带着强烈意识形态特征和地域色彩的文化表达不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这不但让大院文化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直接导致了地域性强烈的北京文化和北京方言在银幕上失去了吸引力而逐渐退场落幕:在冯小刚的《大腕》之后,受到大众欢迎带着新京味文化色彩的影视作品几乎不见了。
我们依然能够从郭宝昌的《大宅门》或者邹静之的《五月槐花香》等电视剧中看到北京的存在,但它们更多的是跳过了大院文化的时代和精神内核,重新回到曾经被新中国革命者所批判和抛弃的旧时北京风物和文化中,对已经消逝的考古文化意义上的北京寄托一种想象式的怀念。

《大宅门》(2001)
对于消亡中的北京文化的描述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如果说1983年王好为拍摄的《夕照街》和1986年美籍华人王正方拍摄的《北京故事》依然对这种新旧交替的变化带着苦涩之中的期待,那么随后宁瀛在1993年拍摄的《找乐》和张扬在2001年拍摄的《洗澡》则赋予北京城风貌的改变某种悲观色彩。

《北京故事》(1986)
2002年陈凯歌的短片《百花深处》以一个精神病人在拆成废墟的四合院遗址上的回忆表达了北京传统失落后所留下的悲伤空白。而比利时导演Olivier Meys和中国独立电影人张亚璇2008年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前门前》则以一种冷静但又接近于绝望的视角记述了北京前门地区的消亡和老北京人面对这样的变化油然而生的无力和无奈感。

《百花深处》(2002)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或者新生与传统的矛盾冲突中,管虎为他2015年的影片《老炮儿》找到了灵感。他出身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世家,广义上可以算做对大院文化有记忆的最后一代人。
但是这一次他却不再计较六七十年代存在于干部子弟和市民阶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把二者本来对立的立场合二为一,共同面对他们都看不惯甚至不屑于与之为伍的新生代北京人。

《老炮儿》(2015)
管虎把表述意图隐藏在一个中年胡同串子的背后,以偶然遭遇的一个危机将龟缩在残存的旧北京系统中的主角逼出,迫使他去直面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的新生二代子弟。
有评论说影片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在北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他所遵循的那些「规矩」在北京市民阶层中从未有过,而这其实正是「歪打正着」地切中了导演管虎的意图——他以一个市民阶层的中年混子为外壳,却内在塞进了大院子弟的灵魂(影片对这样的身份重叠进行了多次暗示,包括那柄做为战利品的日本军刀、黄色军呢大衣以及主角哼唱的南斯拉夫革命战争电影《桥》的插曲),让他以一个有道德底线准则但又游离在现代社会边缘的被遗忘者形象对整个时代发起了唐吉柯德式的自杀式进攻。

《老炮儿》(2015)
在结尾当主角力竭倒在冰面上时,他所赢得的表面上是传统针对于现代的一份尊严,但内在却渗透着一丝大院文化之于时代潮流所顽固坚持的倔强不服。
《老炮儿》因为它的话题性而成为了2015年末的中国电影热点。
但它是否代表着京腔文化甚至是大院文化的某种复苏?这也许正像片中角色们所操着的北京口音:作为老一辈北京人,冯小刚张涵予等人依然操着字正腔圆正宗纯粹的南城和大院口音,而扮演后辈的李易锋等人却只能以让人尴尬的南腔北调假装「新北京人」。

对于北京文化——无论是旧式传统还是大院文化——留有记忆的人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凋零消逝。在以共通的类型特点替代地域性特征的今天,《老炮儿》完全无法像九十年代一样在影视圈掀起一股潮流,它只是银幕上一次京腔文化的回光返照,勾起了观众们对业已消失的过去的一丝猎奇式窥探。
等下一次再有人试图以电影的方式展现糅合着京腔京韵的北京文化时,他也许连能够正确发音吐字的老北京人也难以寻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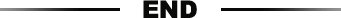
往期精彩内容
在他的电影世界里,性、金钱和死亡毫无愉悦可言
这个人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电影摄影师了
塔蒂演的于洛先生是现代社会的英雄 | 刘起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