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丨翁佳妍
作者丨翁佳妍
来源丨《品读》2018年第4期
从2003年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到2017年在互联网平台上腾讯推出的《和陌生人说话》,过去15年,陈晓楠一直在做一件事——和各种各样的普通人聊天,而这些“人”也让她变成了今天的自己。
那么,让我们听听陈晓楠这个普通人讲自己的故事——

发现
我刚去凤凰卫视时,想做一档谈话节目。后来跟随凤凰卫视做了一系列纪录片,我去了很多普通人去不了的地方,见到了许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人”。
在切尔诺贝利小城,一个人都没有,时间就跟定格在那儿一样。当年核电站爆炸36小时后,居民被要求2小时内撤走,没想到再也没回来。
靠近辐射中心方圆30公里的隔离区被圈起来了,门口有个很大的检测器,工作人员拿个黑色的大刷子在我们身上来回刷,挺吓人的。
我们很紧张,拍了两三个小时,抓起机器赶紧就想跑。
我随口问了一句:“这儿还有没有居民啊?”
向导说里面住着唯一的居民,一个80岁的老太太。我当时就想:我得去找她,我抑制不住想和她聊聊的冲动。

老太太一个人住在辐射区,两个儿子和丈夫都因为辐射得了癌症,死了。她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在后院开了一块地,种萝卜白菜。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走啊?”
她指着周围:“我在这儿出生的。我从哪儿来,就从哪儿走。你看这里多美啊。”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是很美,风和日丽,看不到辐射。她请我们喝了白兰地、吃了巧克力,她说,生命交给老天,不去想这个。
当这些新闻大事件中活生生的人站到你面前,就不只是一个标签,于是我想去找超越阶层、地域后,存在于人类的共通的东西。

失败
就是跟这些普通人聊天,让我知道要干什么了。2003年,我做了节目《冷暖人生》。
刚开始,我想既然是普通人访谈,故事就得炸裂,同时还想这访谈必须比别人的更深刻,心态像跟谁在掰腕子。
我们搞了一个华丽的摄影棚,我带着两个专家,想要开辟“中国首例三对一采访”,嘉宾席坐着一位拾荒的老人。
老人当时80多岁,在广州美院捡垃圾。他是个退伍的老兵,在家乡河南有一堆孩子。他觉得自己不能拖累孩子,得出来赚钱。于是,他从河南一路捡垃圾捡到广州,最后到了美院。
他有一张刀刻一样的脸,学生请他去做人体模特。我见到他时,他甚至已经会给学生指出画的问题了。
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去?”
他说:“我不回去,在这儿能吃上肉就是幸福。”

我把他请到了演播室,灯光一打,四五台摄像机对着他,我和两个专家围着他坐。我抛出了以前采访财富巨子那种问题,特华丽、带前缀、一下转几个弯:
“您经历了这个,后来经历了那个,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头蒙了,两分钟没说出话来。问什么都答:“啊,对啊,是这样。”
我急得不行,脑子里一把剪刀已经开始剪辑了,这句话能用,那一堆话没用。
后来又跟一个流浪歌手聊人生,他说着呢,我脑子里却在想,下个问题我该问什么啊?问不出来,我突然说:“停!我要上厕所。”当时我也是个有经验的主播啊!完全回到幼儿班状态。
开始的半年,我一直找不到和陌生人聊天的感觉,节目越做越差。凤凰卫视对我很宽容,看着我失败,但没人说什么。我快抑郁了,羡慕大街上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改变
特别做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只能扛着摄像机走出演播室,去生活里找人。第一期走出演播室的节目叫《花祭》,上世纪90年代深圳玩具厂发生大火,许多女工被烧死烧伤,10年后,我去她们的家乡重庆寻找她们。
女工们都来自重庆山沟里的一个小县城,要走3天3夜,才能到深圳。我们就沿着这条回乡路来到小县城。
迎面跑过来一个干瘦小老头,是在火灾中丧生的女孩小芳的父亲,怕我们不认识路,来接我们。
走着走着,他突然一指,路边是他的地,里面有女儿小芳的坟。我说在这儿坐一会儿吧。我们就在田埂上坐下了,很自然地聊起来。
10年前,小芳要结婚,不想去打工。可是弟弟结婚的钱还没有,父亲就劝她再打一年工,她很听话,去了,再也没回来。
我就这么听着,不忍心打断。他告诉我拿了3万抚恤金,揣身上,左一半右一半,“像揣着女儿的命”。他把小芳葬在自己家地里,干活能一直看着她。最后他叹息说:
“弟弟结婚是姐姐拿命换来的啊。”
聊着聊着,天就黑了。我好像跟他一起经历了一次丧女之痛。

那一刻,我突然就开窍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一下子找到了自己和《冷暖人生》的魂——跟他们聊天,我就把笔递到他手里,让他自己描画:那一天那一刻发生了什么。
三四个小时后,他进入回忆,往事会像拧水龙头一样,哗一下,就下来了。而我做的,就是坐在旁边听,陪他再走一遍,同时在心里惊叹命运的吊诡。
有时候采访完一个人,我一两天都生活在他的情境里。
很难说一次具体的聊天给了我什么改变,但不知不觉,我对周围人带上了最真诚的好奇:我和湘菜馆的大姐聊天,知道她有个留守在家的孩子;当快递小哥送来东西时,我就想,他跟妈妈打电话是什么样的。
看多了别人生命里的风浪,我对生活也有一种看开了的感觉:
“这就是生活,生活即苦,生活即乐。”
活着还是要任性一点。所以,2017年,我离开凤凰卫视的舒适区,去完全不熟悉的互联网领域。

共鸣
以前我老觉得关注互联网的只是一小撮年轻人,先不用理他们,他们还小。现在他们是“主流人群”,我需要了解他们在关心什么。
这代人还需要《冷暖人生》吗?这是我刚到腾讯时,心里最大的疑问。公司的年轻人说现在不流行30分钟的《冷暖人生》了。
碎片化时代,人们都在上下班地铁上看个几分钟,得短,得抓人注意力。
《和陌生人说话》每期15分钟,正谈在兴头上,就要朝陌生人甩出问卷:
“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你在北京哭过吗?”
我感觉自己多年的采访经验又需要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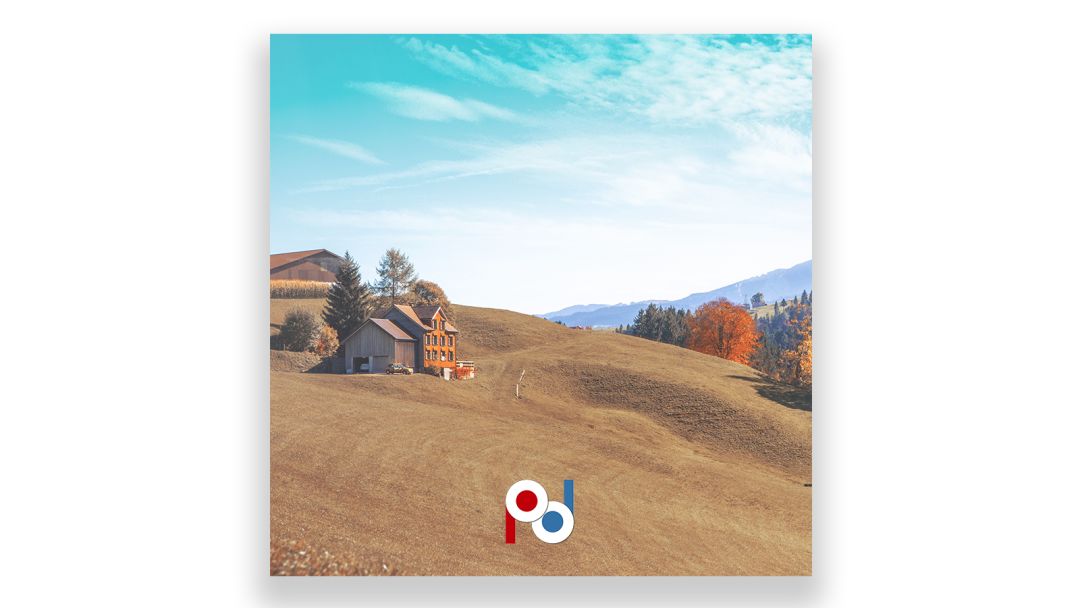
最近我和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的选手毛不易聊。一开始我也怯场,和20岁的小孩怎么聊啊?有代沟,又是聊唱歌这些我不懂的事。
我挺忐忑,于是一见面我就说开了:“我是个老阿姨,你千万不要让这次采访成为我事业的滑铁卢啊。”
毛不易乐了:“不会不会。”
我发现他不是不善言谈,是没有主动倾诉内心的欲望,但他是非常真实的人。
他告诉我自己写了《203》那首歌。他那时候正在医院实习,当男护士。
“小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不同的孩子,长大后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同,那种泯然众人的感觉,有点不甘心。”
我发现这代年轻人,“有趣”“不一样”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虽然看上去很懒很丧,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同的,在用自己的方式小小地抗争平庸的生活。聊完我挺高兴的,觉得自己跟年轻人的代沟其实没那么大,能产生共鸣。
我一直在好奇,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的内心是否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有次马东说:
“技术变化特别快,但人的生理结构可能是永恒的。”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就算是互联网时代,穿过猎奇外象,人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变化。微信发出去没人回的寂寞和收不到信的寂寞是一样的。
所以,我撕标签的愿望越来越强,我想寻找一个人在被贴上各种标签以外,能让多数人产生共鸣的地方。
那些陌生人故事中的复杂,那种五味杂陈的滋味,那种说不清对错的滋味,我想,大概就是人生。

作者:翁佳妍,来源丨《品读》2018年第4期 | 摘自《东西南北》2017年第24期

阅读 品读 全集,点击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