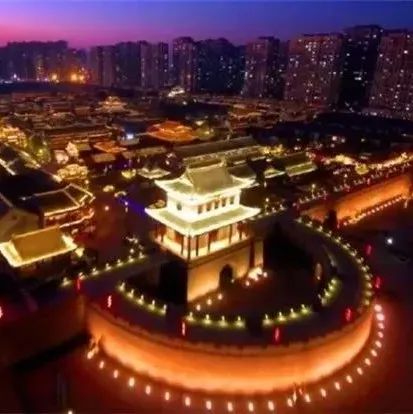奥匈帝国由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组成了一个由宪法驱动的代议制政府。另一方面,在共用一套货币的前提下,两国都是中欧自由贸易区的一员;贸易区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每十年由各成员国出面协商更改。这或许听起来令人费解:的确,就像许多人怀疑的那样,这样的安排使实际的协商过程极其曲折。考虑到匈牙利与奥地利在经济体量上的差距,协商的结果也很难称得上公平。作为一个紧凑的单一民族国家,匈牙利由上流社会的精英统治;但将近一半的匈牙利人不会说匈牙利语。另一方面,由奥地利人占据的内莱塔尼亚就相对统一得多,这得益于奥地利人独立的官僚体系和法律制度。在实践中,两国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多元而类联邦化的多国政体。即使德国人在开始阶段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奥匈帝国的自治区在20世纪初期也逐渐追赶了上来。
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碍于议会阻挠和自治区民族主义势力觉醒,20世纪初期的内莱塔尼亚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但帝国的执政制度,例如官僚体系,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匈牙利的政治局势也不甚稳定——其主体民族与维也纳皇室的关系也一直处在冲突的焦点。而在1908年吞并波黑后,奥匈王室在当地的执政手段甚至笼罩着殖民统治的影子。
即便如此,奥匈帝国对平民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容否认的。其经济增长率创下自1867年以来的新高,经济梯度甚至超过了现今的美国。另一方面,奥匈帝国的法律制度为社会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它的官僚体系也相对清廉。内莱塔尼亚的司法系统保证了一般人使用其母语的权利,这也间接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在帝国治下得以延续。虽然匈牙利的情况稍有不同,但其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如火如荼。内莱塔尼亚的民主化运动亦在进行着——自1907年开始,男性公民便可在联邦大选中投票。也正因如此,奥匈帝国在政治上逐渐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温床。但在政治领域之外,奥匈帝国也为各地区的文化中间派留出了空间——这使得1900年中欧的多元文化为今日的欧洲艺术和学术领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这一切都随着一战的爆发消失殆尽。奥匈帝国在1918年解体,随后被国民政府体系取而代之。但后者在1918至1945年间的无力使共产主义在二战后趁虚而入。同时,西欧国家在多国政体的框架下稳步重建——在借鉴了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执政框架后,欧洲联盟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更加先进的现代化民主政体。
对于今天的欧盟来说,虽然自帝国传承下来的的官僚体系依然存在,但前者对下属城镇的附着度并明显没有哈布斯堡那样高——当然,欧盟也没有必要效仿哈布斯堡或神圣罗马帝国那样在各地部署大量专员。欧盟本质上是一个联邦系统,这代表着主权的行使权依然保留在各国政府的手中;推行欧盟秩序的任务落在了地方官员的肩上,而非欧盟专员。另一方面,欧盟比帝国更为民主。与从未承认人民主权的帝国不同,欧洲议会代表由各民选政府自行选出;而欧洲议会也比当年的德意志议会承担了更多的实际功能。但欧盟和帝国都尊重各方代表的意愿,愿意通过多方协商和官僚体制解决问题。因此,它们在欧洲的成功都充分地体现了制度化体系对现代国家执政的重要性。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欧盟和旧帝国都通过自由贸易区为属地和成员国带来了好处。哈布斯堡各地区之间的高经济梯度使得大量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移居,例如捷克人和犹太人移居维也纳。这在维也纳人中掀起了反斯拉夫和反犹的浪潮,正如今日仇视穆斯林的欧洲人一样。
另外,因多国政体受益却急于否认这一先决条件的联盟成员国在欧盟和旧帝国中都有存在。就像离开哈布斯堡后经济发展停滞,丢失国土,被苏联占领的匈牙利一样,自从脱离欧洲联盟之后,英国的经济也大不如前。
当然,最为讽刺的是,欧盟和旧帝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放任本国民族认同感和民族主义的发展。通过国家现代化和语言细分等手段,哈布斯堡帝国鼓励了属国进一步发扬自身的文化属性。然而,对匈牙利民族群体的一再妥协最终损害了帝国自身的利益,为日后的分崩离析埋下了导火索。而帝国的官僚体系为族群政治的推手提供了双重保险:毕竟无论结局多么混乱,远在维也纳的王室总需要出来收拾残局。今日的欧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加盟国政府让布鲁塞尔为所有问题背黑锅的做法和当年匈牙利人一味指责维也纳别无二致。
综上所述,帝国的致命弱点在于其公民缺少对帝国身份的认同。帝国本身对多样化和国民的离心族群政治一再妥协,使得附属国国民在帝国内部出现分裂的前兆时完全没有维护政治共同体的意愿。这也是帝国模糊,复杂又多元的政治体制使然。今日的欧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时,我们很难运用一个统一且易懂的公式去形欧盟所面临的问题,更遑论使人们支持欧盟。但不容置疑的是,正是通过这样复杂且多元的政治制度维系着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才有了今天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繁荣。
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哈布斯堡帝国为今日的欧盟带来了其他王朝无法比拟的经验与教训。让我们期待这崭新的“帝国”不会在困难面前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