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理论
——理论化与整合性的案例选择策略
游宇 陈超
作者简介:
[1]
游宇,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2]陈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2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
2023/12/25
版块分类:
前沿文献(推送前知网下载量:786)
PDF全文:
点击链接<
一切为了理论——理论化与整合性的案例选择策略
>可下载PDF全文(有效期7天)。
摘要:
案例选择策略在理论生成和理论验证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同案例类型与理论化之间的关系值得展开讨论。基于不同的理论作用和受控比较的基本思维,可以归纳出三种主要的案例选择策略:第一种策略基于理论预期与现实案例的受控比较,用于选择最不可能案例或最可能案例;第二种策略通过求异或求同的受控比较设计,分别选择结果不同的最大相似案例或结果相同的最大差异案例;第三种策略综合了前两种策略的案例类型和比较思路,通过建构因果条件组合的类型学选择,既能支持理论生成又能进行理论验证的多样性案例,并以此作为跨案例比较与案例内分析的基础。在综合分析这三种策略的差异与共性的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如何将这些多元的案例选择策略整合为统一的分析框架。除了通过跨案例比较和条件验证型案例内分析构建理论外,这一框架还强调了一种案例内多阶段受控比较的机制分析思路,能够更有效地结合理论生成与理论验证。
关键词:
案例选择;理论生成;理论验证;比较方法;案例内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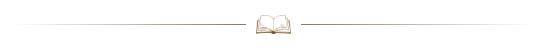
一 、引言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关系学者不仅要探究历史,更要寻找因果规律。[1]完整的因果分析过程往往包含两个紧密相关的部分:一是探寻因果关系的理论生成,二是厘清因果机制的理论验证。研究者在尝试发掘与论证可被观察和有规律的联系时,通常需要借助结构与过程分析进行理论生成与理论验证。在这一理论化过程中,研究者开展研究设计时首先要思考应该在何种时空范围内进行比较以及如何比较,而这些问题均涉及如何选择案例的情形。[2]
然而,研究者对于这些关键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相关研究也没有形成高度的方法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ethodology)。例如,在关于国际关系的定性研究中,围绕案例选择的一系列关键议题长期以来都没有达成共识,包括对案例的定义、案例选择范围的确定、比较研究的逻辑、研究是否旨在检验理论以及因果论断是基于特定条件还是特定机制等。同时,这些研究对于如何将案例选择策略应用于理论的生成和验证也鲜有系统的讨论。[3]
这种现状也说明,尽管在案例导向的质性研究中已有不少关于案例选择与理论建构的方法论讨论,[4]但相当一 部分研究者对于案例选择的方法论意义、案例选择与理论化之间的关系等核心议题仍缺乏重视,在研究设计中的方法论自觉也存在不足。在当前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下,如果研究者希望更有效地推动学科理论的发展,探索新的经验和因果机制,那么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将成为重要 选择。[5]因此,探讨如何将不同的案例选择策略融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以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便尤为重要。
本文主要基于理论化过程中的不同目标尝试讨论与整合现有的案例选择策略。不同的案例选择策略往往适用于理论化的不同环节:如在理论生成环节,选择何种案例来修正既有理论或提出新理论显得尤为重要;而在理论验证环节,为了检验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6]则需要运用特定案例进行跨案例比较或案例内分析。本文认为,案例选择策略可以通过联结理论生成与理论验证成为因果推断的关键桥梁,案例选择策略的核心目标是“为了理论”。[7]
基于不同的理论目标和受控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的基本思维,本文重点讨论三种案例选择策略。第一种策略主要基于理论预期与现实案例的反差,选择最不可能案例(least likely case)与最可能案例(most likely case),聚焦那些被既有文献所忽视的关键解释因素。第二种策略利用最大相似系统设计或最大差异系统设计,分别选择一组结果不同的最大相似案例(most similar cases)或结果相同的最大差异案例(most different cases)。第三种策略综合了前两种策略的案例类型与受控比较思路,主要通过建构因果条件组合的类型学,选择兼具理论生成与验证的理论支持型与理论反对型案例:基于第一种案例的跨案例比较与案例内分析可以联结理论生成与理论验证,通过对第二种案例的探索性分析则可以进行理论修正。基于不同案例类型的功能与理论化不同环节的需要,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整合不同案例选择策略的分析框架。

二 、基于理论化目标的案例选择策略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理论化是指将一系列现象、事实和观察结果抽象出来并用概念和理论框架加以解释和理解的过程。理论化可分为四个步骤:一是通过观察确定经验支持的事实;二是提炼概念,通过精确的概念界定研究范围,并运用这些概念分析观察到的现象,确保研究中概念的定义前后一致;三是建构理论,提出可被科学验证且可证伪的理论假设;四是通过经验证据进行理论验证。[8]
根据这一定义,理论化过程主要包括理论生成和理论验证两大核心阶段,而理论验证又可分为修正假说和验证假说两个分析环节。具体而言,理论生成是指基于既有数据和知识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并提出理论假说,为理解相关现象提供新的解释和视角;理论验证则是指利用经验数据和研究方法,修正和验证已有的理论框架和假说,确定其有效性和可靠性。[9]案例选择在假说的提出、修正和验证环节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见表1)。
表1 理论化的不同环节与案例选择

资料来源:笔者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制作,参见Ingo Rohlfing, Case Studies and Causal Inference: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p.11。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出新假说或修正现有假说等分析环节中,从概念到需要验证的理论假说之间还需要一个真正的理论化过程。这个过程涉及提出既具有一定抽象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和机制。换言之,理论假说的形成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需要通过理论与案例的相互作用实现。这需要对选定的案例进行探索性分析,从抽象的理论中提炼出可被经验事实证实或证伪的具体假说。[10]
因此,研究者在选择案例时应侧重那些有助于形成假说或深入理解特定现象的案例。在这一过程中,特定的理论目标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可以引导研究者确定哪些案例最适合其研究指向、哪些案例具有典型性或“反常性”以及哪些案例能够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例如,理论建构与机制甄别是当前社会科学案例研究的重要目标。它们可以帮助研究者确定某个案例是否满足特定条件或标准,进而选择最有助于支持/反驳理论假说的案例或能够最大化变量差异的案例。这些明确的理论目标确保了案例选择的系统性和目标导向,避免了随机或主观的选取。
例如,面对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难以解释国际关系中区域主义和区域认同兴起的理论困境,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选择将东南亚国家的互动和东盟的发展作为关键案例。他通过研究东南亚国家独特的互动方式(即以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为主要特征的“东盟方式”)及其影响东盟发展的过程,提出了“区域是想象的共同体和社会建构体”这一核心 观点。[11]实际上,作为有别于传统联盟理论的独特案例,东南亚国家的互动模式和东盟的发展历程一直是阿查亚发展或修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实证来源。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经典理论,更是通过基于建构主义的实证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主流建构主义理论。[12]
除选择既有理论难以解释的案例外,对特定案例进行比较也是生成理论的重要策略。例如,在探讨第一波现代化国家成败经验的相关研究中,黄振乾等的分析首先论证,除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四个西欧国家外,其他国家在1500—1699年难以成功实现现代化,即仅有这四国获得了现代化的“入场券”。[13]基于此,叶成城等通过对这四个西欧国家的详细案例比较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参与大西洋贸易、获取战争胜利及非专制攫取型制度等关键解释因素,并围绕这些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构建了一个解释第一波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成败的“因素+机制”分析框架。[14]
综上,研究者可以在理论化的不同阶段通过巧妙地选择案例以实现不同的理论化目标。[15]这引出了 两种基本的案例选择策略:一是选择那些既有理论难以解释或与理论预期相反的关键个案,二是通过采用最大相似系统的策略选择一组配对比较的案例。
具体来说,基于既有理论预期与实际案例结果之间的差异,研究者可以选择两类反理论的关键个案来形成新理论或削弱既有理论:一种是最不可能案例,即根据既有理论解释或推论,某个结果本不应该出现,但现实情况却与此相反;另一种是情况恰好相反的关键个案,即依据既有理论解释或推论,在某些条件下应会产生某种结果,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两种关键个案实际上都会促使研究者反思既有解释的理论边界,以此作为生成新理论的起点,此即前文提及的第一种案例选择策略。第二种案例选择策略是基于最大相似系统设计或最大差异系统设计形成一组可比的最大相似案例或最大差异案例,这一策略实际上也属于案例比较的设计方式。[16]
尽管上述两种案例选择策略在比较逻辑(与理论预期进行比较还是案例间的系统比较)、案例数量(个案还是案例组)以及理论化作用(旨在识别关键解释因素还是构建理论框架)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的核心思想都是作为案例研究方法科学化基础的受控比较,[17]这意味着两种案例选择策略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具有整合的可能性。同时,二者在方法论层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第一种策略侧重于选择与理论预期相反的关键个案,虽然包含了比较的思想,但并未进行系统性的比较论证;第二种策略则通常受制于案例相似度有限和难以排除竞争性解释等问题,削弱了理论的内部有效性。这也体现了在研究设计中整合不同案例选择策略的必要性。
本文重点讨论的第三种案例选择策略——基于因果条件组合来选择用于理论生成与验证的理论多样性案例——也由上述分析引出。建构因果条件组合类型学的主要目标是阐明因果关系,并根据不同理论作用的案例进一步修正理论与验证理论。其理论生成过程则基于对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与对案例的探索性分析,而理论验证过程往往需要借助案例内的因果机制分析。[18]这种案例选择策略首先通过限定因果领域从总体上框定研究案例,[19]然后根据理论框架建立因果条件与结果的类型学,将这些案例分为理论支持型案例与理论反对型案例。前者主要用于理论验证,可以被称为机制验证型案例;后者主要用于理论修正或优化,可以被称为条件验证型案例。这些理论多样性的案例为建构更为复杂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
表2总结了三种案例选择策略的核心原则、设计思路及其对理论化的作用。本文认为,第三种策略因其在展示更多针对理论化目标的案例类型、提供更为多元化的系统比较方式以及为机制甄别与验证提供更加系统化和有效的设计思路等方面更具潜力和优势,因此可以更有效地服务于理论化的不同环节与目标。
表2 以理论化为目标的案例选择策略

续表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其一,就多样化的案例类型和比较方法来看,第三种案例选择策略既可以呈现理论支持型或机制验证型案例,也可以呈现潜在的反例。一方面,研究者能够通过对支持理论的案例进行跨案例比较分析,强化理论生成或通过案例内部分析来验证理论机制;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能够通过将符合理论预期的典型案例(正向案例)与反例进行比较分析,探寻可能的关键解释因素并进行理论修正。可见,基于这一案例选择策略的分析路径很大程度上覆盖了前两种策略的案例类型和比较路径。
其二,尽管这三种案例选择方式均侧重论证理论框架中不同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第三种策略在机制甄别与验证方面具备更多样化的设计思路,在有效联结理论生成与理论验证上也具有更大潜力。
第一种和第二种案例选择策略对理论化的作用则较为有限。第一种案例选择策略的贡献主要在于提醒研究者重视那些被既有研究忽视的潜在解释因素,同时因为缺乏系统比较,其对机制甄别的作用主要在于选择那些能够帮助研究者理解特定现象的案例。第二种策略中的最大相似系统设计可以识别由关键因素的差异造成的不同结果,[20]有助于研究者优化理论建构以及确定哪些案例具有典型性、哪些案例能够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进而从预期的理论关系中推导因果机制。第三种策略对于机制甄别和验证的贡献更为全面:一方面,该策略通过跨案例比较分析强化了因果关系的建构或借助反例进行理论修正,为研究者有效获取用于识别机制的案例信息提供便利;另一方面,该策略可以通过案例内分析或案例内多阶段受控比较分析服务于理论机制的验证。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在第三种案例选择策略基础上尝试整合前两种策略,形成一个基于理论化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下文将结合既有研究对前两种案例选择策略进行简要讨论,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第三种案例选择策略与整合性研究设计。

三 、基于受控比较思维选择
关键个案或配对比较案例
受控比较是绝大部分科学化案例研究方法的基础。这种比较方法主要是指研究者通过控制或调整一组案例中的一个或多个变量,观察这些变化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进行比较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特定变量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上。第一种和第二种案例选择策略均基于受控比较思维,但由于比较对象与方式不同,因此其选择案例发挥的理论作用也大相径庭。
(一)基于理论预期与现实案例的受控比较选择关键个案
如果研究者对某个理论的有效性抱有强烈信心,那么某个案例的结果必须严密契合该理论的解释;反之,如果某个案例的结果与该理论的解释或推论完全相反,那么该案例可能就成为理论建构或理论修正的关键个案。[21]基于此,约翰·格林(John Gerring)阐释了严格意义上的关键个案和宽松意义上的关键个案。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一个案例的关键性在于能够被某个理论精确地解释;与此同时,没有其他理论能够解释该案例的事实,且这一理论是稳定不变的(invariant)或决定性的(deterministic);而从宽松意义来看,一个案例的关键性往往是因为它最有可能或最不可能符合某个理论的预测。[22]研究者往往从宽松意义上来理解关键个案,并随之引出两种变体即最不可能案例与最可能案例。[23]
尽管这两种关键个案存在重要差异(见表3),但本质上均是受控比较的产物,其逻辑都是通过观察基于理论预期的理想案例与现实案例在关键因素X上是否存在差异并产生了不同结果。
表3 关键案例的两种类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最不可能案例是指在既有解释预期中最不可能出现某个结果、实际上却因为我们关注的解释因素X而出现了该结果的案例。选择这样的案例旨在强调既有理论未发现的因素X,并着重增强新解释X的说服力。根据安德鲁·贝内特(Andrew Bennett)和科林·埃尔曼(Colin Elman)对国际关系领域案例研究方法的评述,这一案例选择策略在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24]例如,马修·伊万杰莉丝塔(Matthew Evangelista)的研究表明,尽管现实主义理论普遍预期跨国行动者在国家主导的安全问题上影响十分有限,但实际上美苏科学家的跨国联系确实对美苏国防和军备控制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苏联的反弹道导弹防御政策转变中,跨国行动者的角色和作用突显了新解释因素(跨国科学家的互信与交流)的重要性。[25]经由选择这一最不可能案例,伊万杰莉丝塔不仅挑战了传统理论对安全问题的解释,而且通过揭示未被既有理论所注意到的重要因素——跨国行动者在国际安全政策中的作用——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最可能案例则是指在所有既有解释中最可能出现某个结果,但由于我们感兴趣的特定解释X并没有出现该结果的案例。这类案例主要用于证伪,削弱既有解释的说服力。例如,在研究战争爆发因素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提出了转移视线战争理论。根据该理论,战争爆发的原因被部分归因于一国的国内动荡。[26]然而,傅泰林(M. Taylor Fravel)针对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和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研究发现,尽管两个案例中都出现了严重的国内动荡情况,发展方向却截然相反,可见国内动荡并非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27]换言之,该研究通过最可能案例证明了转移视线战争理论假说的局限性。
基于理论预期与现实案例的受控比较选择关键个案这一策略也被用于有关政治稳定与政治认同的研究中。阿伦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的研究即是一项经典示例。既有研究通常认为,政治动乱主要发生在社会构成高度异质化和存在认同冲突的地方。然而,荷兰的案例却展示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一方面,荷兰的社会构成可谓高度异质化,存在党派林立、政党与宗教紧密相关和社会严重分化等基本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与一般理论预期相反,荷兰持续保持了政治稳定。通过选择荷兰这一最可能案例,利普哈特发现基于“共识民主”而非多数表决下的“赢者通吃”原则所建构的多元民主制度对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荷兰同时也是研究议会与民众关系的一个最不可能案例:虽然荷兰第一议院并不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议员数量相对其人口规模来说也不成比例,甚至议员不具有领土代表性,但是民众对于第一议院及其议员却具有相对较高的信任度并长年未出现下降迹象。[28]鲁迪·安德威(Rudy Andeweg)从荷兰民众对议员的期待与议员对民众的回应两方面解释了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荷兰民众并不期望他们的议员过多投入选区工作,而是希望他们可以切实地回应民众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荷兰议员确实认真地对待与民众的互动,如投入大量时间与民众接触并回应有关公民不满的请愿等。[29]
综上,这两类关键案例主要关乎对既有理论的可证实性(confirmatory)或可证伪性(disconfirmatory):证实性的最不可能案例重点在于理论生成,即帮助研究者强化新解释的说服力;证伪性的最可能案例则更加强调理论修正,即通过削弱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协助研究者思考如何改进既有理论。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类案例均属于单案例分析,并未进行控制性比较的系统分析,因此难以直接形成因果关系或排除竞争性假设。
(二)基于最大相似或最大差异的受控比较选择一组案例
关键个案的选择策略更多是基于与既有理论解释的比较,即通过提出反例的方式挑战既有理论的解释,从而促进新知识的形成。这一逻辑蕴含了比较的思维,但没有进行系统性比较的论证。在此,我们将借鉴约翰·密尔(John S. Mill)的求异法和求同法设计思路,讨论如何基于受控比较选择最大相似案例或最大差异案例。
密尔方法实际上在案例选择与研究设计之间建立了紧密关联(见表4)。求异法属于最大相似的系统设计,其主要逻辑是:在其他条件一致时,导致结果不同的差异即为原因,也就是通过最小化差异解释不同结果。求同法则属于最大差异的系统设计,这一设计的核心思维是:在其他条件都存在极大差异的情况下,如果仍然能够得到相同结果,事物间的共性即为其原因,即通过最大化差异解释相似结 果。[30]
表4 基于最大相似设计与最大差异设计的案例选择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研究制作,参见Todd Landman and Edzia Carvalho, Issues and Methods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p.71。注:X表示关键前因条件(组合)出现,x则与之相反;Y表示结果发生,y则表示没有发生。
基于上述受控比较思路选择的最大相似案例意味着在一组(至少两个)案例中,只有一个条件(组合)不同而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且这种差异导致了结果的变化(发生或不发生)。这一选择策略来源于密尔的求异法,并经由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关于最相似体系方法和李普哈特关于比较方法的探讨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阐明。[31]
这一案例选择策略同样适用于在众多维度相似的案例之间识别关键差异,而且这一差异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结果。本文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法国西部旺代叛乱的研究为例,简要阐述其设计思路。[32]如表5所示,在这项探究地区叛乱程度高低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选择四个地区进行受控比较,这些案例在君主与贵族关系以及地理因素上均相同,而只有城市化与叛乱组织领导力这一条件组合不同,因此“高城市化+强领导力”很有可能是导致地区叛乱程度高的解释因素。[33]
表5 求异法与最大相似案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不过,最大相似案例的作用通常是验证性的:通过对比分析这一组案例,我们可以观察关键解释条件(或条件组合)的存在或缺失(如对比地区A与地区B、地区C或地区D),显示原因条件(如城市化+领导力)与结果的相关性,为后续的案例内分析提供理论验证的基础。[34]
这种受控比较的思维在定量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大样本定量分析中各种形式的匹配策略实际上与这一设计思路有着相似之处。例如,合成控制方法就是一个基于求异法比较思维设计的估计模型。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合成”一个适当的控制组,也就是在各方面都与受到干预的地区相似但并未受到干预的“合成控制地区”,以此作为处理组(即受到干预的地区)的反事实,进而估计某项干预条件的因果效应。[35]合成控制方法本质上是利用密尔方法在小样本比较研究中进行精确的因果推断,以定性思维扩展了定量研究的边界。例如,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塑造国家间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庞珣和陈冲的研究则利用合成控制法揭示了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即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导致双边外交立场接近的现象:在通过混合效应回归模型验证了这种效应的普遍性后,他们比较分析了真实的阿根廷与合成的“反事实阿根廷”,从而进行了更严格的因果效应识别,进一步检验了“赫希曼效应”并深化了对其因果机制的理解。[36]
然而,少案例比较研究是通过现实中的案例进行受控比较,但不能通过统计方法来合成“抽象”的比较案例。[37]此外,既有研究也揭示了这种研究设计在因果推断中的一些局限性:其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几乎很难找到两个只有条件X不同而其他因素都一样的案例,因而只能对变量进行近似的控制。其二,受控比较会限制案例选择的多样性。其三,随着解释变量的增加,受控比较的设计难度和案例数量也会成倍增加。其四,这种方法难以回应竞争性解释的挑战,即研究者忽视的差异可能削弱解释变量的因果解释能力。[38]由此可以看出,基于最大相似性的求异设计仍然只是一种相关性推断,研究者还需要通过综合使用多种案例研究的策略以增强其因果解释力。
与最大相似系统设计相反,最大差异系统设计的主要逻辑在于通过对各方面都差异巨大的案例进行比较,识别出可以解释相同结果的共性因素。[39]换言之,即使是在其他条件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如果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那么事物间的共性因素就可能是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因此,基于这一设计思路选择的最大差异案例是指那些只有一个条件相同、其他条件完全不同且出现相同结果的一组案例。
最大差异系统设计的案例选择和比较分析确实具有其优势。研究者可以在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仍保持较少的变量,并通过消除那些并不在所有案例中出现的“虚假”必要因素提炼出理论的关键启示。然而这种设计也有缺陷,可能使它比最大相似的系统设计的案例选择策略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它难以解决变量与结果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复杂性或一果多因问题,只能为理论生成提供比较有限的证据支持。[40]在这类案例研究中,如果只是简单地寻找少数因素的共性,研究者就难以通过严谨的因果推断得出正确结论。

四 、基于因果条件组合的
类型学选择理论多样性案例
进行分类或建构类型学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常见的比较方法之一。与定量研究中因子分析或聚类分析的基本逻辑类似,类型学的最主要作用在于将零散或杂乱无章的信息通过一定的逻辑进行降维或压缩,使人类世界显得不那么复杂。同时,研究者也可以通过将众多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要素聚合为几个更宏观的因果条件,从而使得理论更加简洁。
以解释为目标的类型学通常基于原因和结果的充分/必要条件组合进行理论建构,这一设计的应用也较为广泛。[41]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利用这种方法探究某种国际体系下的大国关系等重要理论命题。例如,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关于在双极结构下两个大国如何互动(冲突、制衡还是共治)以及大国与中小国如何维持关系等重要问题再度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通过分析春秋晋楚弭兵、宋辽争夺高丽、美苏冷战对峙和中美东亚竞争四个涉及古今中外的典型案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层层递进的理论解释,认为大国功能分异是引发大国差异化共治出现的重要前提,大国无战争是确保大国差异化共治能够得以稳定维持的必要条件,大国无战争和大国功能分异的条件组合则是大国出现稳定的差异化共治的充分条件。[42]此外,在探讨后发地区国家构建与发展这一问题时,戴维·瓦尔德纳(David Waldner)也提炼出精英联盟与国家建构的两种政治经济模式——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与发展型国家,并将其作为核心的中介变量在“国家—精英关系”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建立起了理论桥梁。[43]
从这些研究的设计思路和理论建构过程可以看出,以解释为目标的类型学旨在基于特定理论对多维度条件的逻辑组合进行分类。[44]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和加里·戈茨(Gary Goertz)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45]他们认为,研究者应该遵循预期理论的范围条件和可能性原则区分不同类型的案例,重点选择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进行因果推断,并排除那些结果不可能发生或既有理论适用范围之外的案例。[46]
本文根据相关研究构建了两个前因条件与结果的逻辑组合(三个变量均为二分类,即是否发生),并由此得到四种案例类型,而不同类型的案例对于理论化的作用也不相同(见表6)。
表6 基于两个前因条件建构的因果关系组合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研究制作,参见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 “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 Choosing Negative Cases Comparative Research, ” p.663。注:“是”代表这一条件X存在或结果Y发生,“否”则与之相反。括号中三个数字依次代表X1、X2与Y的状况是存在或发生与否,存在或发生标为1,反之为0。
第一类是正面案例,即完全符合研究者理论预期的典型案例。案例的典型性并不在于其能够复现总体的特征,而在于集中体现了某一类别现象的重要特性。对于建构理论与机制验证来说,这类案例正是研究者需要着重分析的对象。[47]
第二类是前因条件组合部分缺失(X1和X2的前因条件组合因其中之一没有出现)且结果也没有发生的负面案例(0,1,0或1,0,0)。这也是马奥尼和戈茨建议研究者应该根据可能性原则选择的另一类机制验证型案例。这类案例由于前因条件受到其他因素阻碍而无法完整呈现,导致结果也难以发生。
第三类是反例,即与研究者理论预期相反的异常案例。本文认为,不同类型的反例对研究者所预期的理论解释构成的挑战不尽相同。具体而言,反例的“异常性”主要体现为两类:一是前因条件组合部分或完全缺失但结果却发生的案例,即Ⅰ型反例,包括(0,1,1)、(1,0,1)与(0,0,1)三种情形;二是前因条件组合完整出现但结果却未出现的案例,即Ⅱ型反例(1,1,0)。Ⅰ型反例的理论作用与最不可能案例类似,其出现很可能表明存在使结果发生的新的原因条件,而选择这一类型的案例可以帮助研究者有效加强新解释的说服力,从而进行理论优化。[48]Ⅱ型反例则类似于最可能案例,其存在会削弱理论解释的说服力,从而提醒研究者需要修正现有理论。
第四类是无关案例(0,0,0)。这类案例的前因条件组合与结果都未出现。如果单独看待,无关案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因果推断,而在于确定范围条件,即通过与相关案例(包括正面案例、负面案例和反例)的比较确定理论解释的因果域。[49]然而本文认为,如果研究者可以将无关案例与其他案例类型进行案例内的受控比较分析,这样的研究设计仍有助于理论验证。
表7总结了上述讨论。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都符合研究者的理论预期:前者是由于前因条件组合完整出现,结果应该发生且实际上也确实发生的案例;后者则是由于前因条件组合并未完整出现,结果不应该发生实际上也没有发生的案例。两者都是支持理论的案例,可以选择它们作为理论验证的案例进行深入的案例内分析。[50]相应地,反例则对预期理论解释明显提出了挑战,因而属于理论反对型案例,可以选择作为条件验证的案例,通过对反例进行案例内分析有助于发现新的解释因素或修正既有解释。无关案例则需要与其他类型的案例结合起来进行案例内的受控比较分析,这样方能发挥对理论的潜在支持或反对作用。因此,本文将这类案例定义为“理论复杂型案例”。
表7 不同类型的案例及其理论作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综上,以解释为目标的类型学案例选择策略既能呈现更多样化的案例类型和多元化的系统比较方式,也为理论的生成和验证提供了更加系统和有效的设计思路。它基本上包含了前两种策略的案例类型和受控比较思路。

五 、基于多元案例
选择策略的整合研究设计
如前所述,基于因果条件组合类型学展示的不同类型案例在理论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这种案例选择策略至少有三方面效用:一是保证案例类型的完整性,即前因条件与结果的逻辑组合均可得到完整呈现;二是为不同理论化阶段的分析提供指引和备选案例,如选择机制验证型案例进行案例内分析或选择正面和反面案例比较分析以优化理论等;三是提醒研究者,如果存在异常案例或反例,则需要进行理论修正或重视其他竞争性解释。这些潜在作用进一步要求研究者从不同案例类型的功能出发,根据理论化不同阶段的需求进行综合性的案例研究设计,并将不同类型案例的跨案例比较与案例内分析有机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