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白话文和白话诗
文/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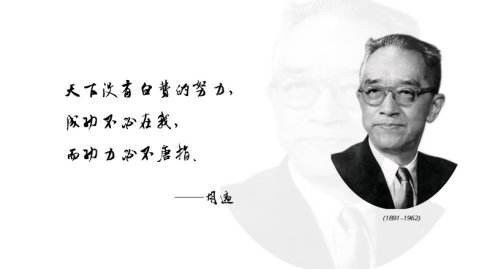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that we are back again"
--Iliad,xviii,I.125.
1917年3月8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日记中注明这句话来自《伊利亚特》第十八章第125行。但胡适不是直接从该书中摘录的。
日记中说,英国十九世纪的宗教改良运动未起时,其未来的领袖纽曼(Newman)、傅鲁得(Froude)、客白儿(Keble)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许。三人将其所作的宗教诗歌合为一集,纽曼取荷马诗中这句话题其上。其意若曰:“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日记中又说,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三个月后,胡适离开绮色佳(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起程回国。那一年,胡适年仅26岁。三个月前写在日记中的这个名句,有几分是年轻人的豪云干气,也可以说是胡适的自我期许。纵观胡适一生,谦逊的性格一直是其主要特征,这样的豪气,从何而来?
事实上,早在胡适回国之前,他的名字便通过《新青年》开始为国内的读者所熟知。1916年冬和1917年春,《新青年》杂志刊出了从胡适的学生日记中选出的大量摘录,还有他早期带有尝试色彩的白话诗以及他翻译的莫泊桑的小说。更为重要的是发表了胡适返国后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白话文运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和《历史的文学观念》。
第一篇发表于1917年1月,第二篇发表于四个月之后。
正是这两篇论文,让刚上任不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相中了胡适,独具慧眼地把这位未曾谋面的留学生延揽到了北大。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说: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如今来看,这实在没有什么新奇,甚至终其一生,在白话文作文的水平上,胡适最终也没有取得他那些时代同侪的成就,以至于李泽厚先生如此评价:“这个非常平淡的“八不主义”,却居然成为五四时期掀起巨浪狂风的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但“胡适是开风气者。开风气者经常自己并不成功,肤浅泛泛,却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
不过,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看法,而在当年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看来,胡适的这“八不”主义,值得大为钦佩。陈独秀将其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专门写跋文评论:“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当亲见其成,则大幸也。”在紧接着一期的2卷6号《新青年》上,又亲自撰写《文学革命论》,自称“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1924年8月,胡适在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写导言时,自信满满地回忆到“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胡适这话,是针对陈独秀半年多之前对白话文运动领袖地位的推辞,那一年,陈独秀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是说到:“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要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但是在当年,胡适对于白话文态度,反倒没有陈独秀坚决、彻底。
1917年4月9日,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长信中谈到白话文,仍然是学者谦逊的探讨态度:“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必为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而陈独秀的回答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匡正也。”
令人惊异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缘起竟是因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在1933年12月写成的《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对此有过详细的交待:
作为一名庚子赔款生,胡适每月都要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领取一笔生活津贴。负责邮寄津贴支票的公使馆秘书钟文鳌是一个基督教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很大影响,想利用他发支票的机会来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便印了一些宣传品,和每月的支票夹在一个信封寄给留学生们。他的小传单有种种花样,大致是这样的口气:
“不满二十五岁不得娶妻。”
“废除汉字,取用字母。”
“多种树,种树有益。”
支票是留学生们每月渴望的;可是钟文鳌先生的小传单未必都受他们的欢迎。留学生们往往拆开信,把支票抽出来,就把这个好人的传单抛在字纸篓里去。
1915年初的一个月里,胡适又接到他的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说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照胡适看来,这样一种出自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无权贬损文言之人的建议,伤了他的体面意识,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他,信上的大意是说:“你们这种不通汉字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胡适就后悔了。等了几天,钟文鳌先生没有回信来,他更觉得不应该这样“盛气凌人”。心想,这个问题不是一骂就可以完事的。自己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这件事,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不然,就应该受钟先生的训斥。
那一年恰好美国东部的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他就同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们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元任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
当时胡适并没有明确的改良中国文字的主张,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应当讨论。而这,也不过是胡适将学术兴趣转移到中国语文改革的第一步而已,真正的逼上梁山,则是在1915年,胡适与留学生朋友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人之间一场激烈的争论,胡适将那场争论称之为“革命的导火索”。
1915年,梅光迪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在倚色佳与一班朋友度过了暑假,将转于哈佛大学取跟随当时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白璧德继续深造。胡适写了一首长诗送行,其中有句: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不想,这首诗遭到了朋友们的挖苦,任叔永写诗回敬胡适说:“文学今革命,做歌送胡生”。
在朋友们一片冷嘲热讽中,胡适感到很孤立,那时的他,尽管认为当时文学的大病在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但还没敢把解决的答案想到白话文上去。恰恰是任叔永的一封反驳信,让胡适一下子茅塞顿开,在那封信中,任叔永说:“近来颇思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文字形式开启了胡适的思路,“文学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够表情达意?换成胡适的话说:“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者语言上的工具去代替另一个工具。”
自此,胡适认定了:
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者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法——这就是我的方案。
一个事实让胡适在一片讥讽中获得了胜利。周氏兄弟在1909年用文言翻译了一册《域外小说集》,这本小说曾经被胡适誉为“古文学末期”的“最高的作品”,但在十年之内只卖出了二十本,而1918年之后,鲁迅改用白话创作小说,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一跃成为新文学阵营中武艺最高的骁将,新文学天幕上最璀璨的一颗明星。难怪鲁迅会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
但最后的胜利还没有到来,胡适虽然在白话文的问题上说服了他的一班朋友,但是他们坚持不认为白话可以作诗。
胡适还必须在文学最重要或许也是最典雅最神圣的诗歌领域和他的朋友们展开一场较量。
1916年7月,还是那帮朋友们:任叔永、陈衡哲、梅光迪、杨杏佛。相约嘉湖游船,不想近岸时船翻了,祸不单行,又遇上了大雨,一行人十分狼狈。任叔永忽然诗兴大发,做了一首四言古诗,里面堂而皇之地出现“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之类的句子,尤其可笑的是,小小湖面上泛舟遇到风浪翻船,竟然用到了“亀掣鲸奔”、“冯夷所吞”这样的字句。胡适看了,忍不住去信批评:“诗中所用言字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二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又批评波浪覆舟一段“小题大做”,读者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是鄱阳洞庭,“故全段无一精彩”。
任叔永接受了后一个意见,但是“载”“言”之类的典雅的“诗的语言”却坚持不改。胡适的朋友们从根本上怀疑白话可以作诗,这个怀疑实际上否定了白话可做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
此时的胡适,已经意识到白话文革命“十仗中已经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了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因此打定主意“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