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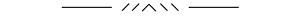
你真的读懂了吗?
文 | 闫红
▍一
《红楼梦》第一回,很有种大片即视感,镜头在几个场景间迅速切换,让人眼花缭乱。
首先是作者坐在他人生的角落里,一连串独白,然后转向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不得志的石头正在自怨自叹。一僧一道路过此处,将它夹带在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故事里,去看世间繁华,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有个访道求仙的空空道人路过青埂峰,看见这石头上已写满了字,就是我们所见的这部小说的原始状态。
这几个场景时间地点都不确切,是时空的无涯,突然,作者巨手一翻,忽然抓取出极其精准的定位:“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
像是一个陡然推近的长镜头,从魔幻转入现实,寻常巷陌里,甄士隐和贾雨村的一段交往,进入我们的视野。
甄士隐是姑苏人士,“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是当时社会里比较典型的中产阶级。他的活法,也是中产的逍遥滋润:“秉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般的人品”。
贾雨村来自胡州,虽然“也是诗书仕宦之族”,他后来自称与荣国府“同谱”,但“同谱”这个概念,大了去了。书中明白地说:“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点明他的一穷二白,是试图突破自身阶层的草根族。
贾雨村来到姑苏,淹蹇住了,“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他只得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
逍遥自在的中产阶级,与蓄势待发的草根族之间,阶层壁垒最容易打通
,没有深似海的朱门,甄士隐能看到贾雨村的才华志向,贾雨村在甄士隐面前虽然略有紧张感,但也还能保持一个读书人矜持的身段。

▲
87版《红楼梦》中的贾雨村
▍二
两人的交情就此而起,经常在一起谈谈说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时甄士隐将贾雨村约到家中,忽有更重要的“严老爷来拜”,甄士隐忙不迭地丢下贾雨村,去见那个更重要的“严老爷”,也可以窥见,
两人之间,终有一道隐形的阶层鸿沟。
使得两人关系变得相对黏着的,是甄士隐对于贾雨村的赞助,他赞赏贾雨村的才学和志向,建议他赴京一试,贾雨村提出自己困难之所在,甄士隐便叫小童去拿来五十两白银和一套冬衣,供他一路盘缠。
贾雨村收下银子和衣服,略谢一语,并不介怀,但五更天就打点了行装进京去了,要知道他和甄士隐三更天分的手,两个时辰就能出发,可见他多么高效,多么急迫地想要飞得更高。
贾雨村踏上了他的光明大道,甄士隐的命运却开始下坠。正月十五晚上女儿英莲被拐卖,三月十五隔壁庙里炸供敬佛不小心失了火,甄家被殃及,烧成了瓦砾场。他带了妻子家人去田庄上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难以安身”,他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去投奔岳父。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上,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岳父对他的到来并不欢迎,半哄半赚的,“些许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穑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得穷了下去”。
中产这个属性太不稳定,抗风险能力极差,一场灾难,就会引发致穷的多米诺骨牌
,甄士隐的人生顺流而下,坠入最底层,以至于“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当甄士隐终于对人生绝望,跟一僧一道远走高飞,他的妻子沦落到靠“日夜做些针线发卖”为生,贾雨村的辉煌才刚刚开始。在门口买线的丫鬟娇杏看见他被前呼后拥着坐在大轿子里,乌帽猩袍,隔着帘子,与她打了个照面。
此时甄士隐不知道在何方,这个丫鬟在买线,也是穿针引线,她串起了甄士隐的刚刚唱罢,与贾雨村的粉墨登场。在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恒久的富贵,秦可卿说了,“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你看他起高楼,你看他宴宾客,你看他楼塌了,但同时,让我们转眼看另外一个人,正在废墟之上,筑建自己的根基,世人来来往往,如过江之鲫,衰败与兴起,一刻也不停息。
▍三
甄士隐的命运里有贾家的缩影,虽然贾家是老牌贵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衰败得要缓慢得多,但只要压缩一下那过程,就是相同势态。
在一个中产的故事里,曹公更方便表达他对世道的怨气:善良慷慨的士绅沦为乞丐,穿破袄的腹黑青年换上蟒袍,尽管曹公写得极其克制,还是在寥寥数笔间,刻画出了尚未得志的贾雨村,那掩饰不住的可笑嘴脸。
比如甄士隐的丫鬟娇杏回头看了贾雨村几眼,他马上就认为这个姑娘对自己已钟情,年轻人自作多情并不可笑,滑稽的是,他以为她是个“巨眼英雄、风尘知己”。
所谓“巨眼英雄”是何人?隋唐时候的红拂也,她不是以美貌以痴情而彪炳史册的,她的过人之处,是善于识别还未发迹的英雄,因此为尚未崛起的野心家所情有独钟。
他们行走世间,等待挑选,机会尚未垂青,若能有一个女人确定他们前途远大,也行。与其说他们期待爱情,不如说他们期待命运能丢下一根签,暗示未来的光明,而一个“巨眼英雄”,正是命运无法告知谜底时,丢给他们的一根上上签。
娇杏的这一回顾,不过是陌生人本能的好奇,贾雨村却浮想联翩,以为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风尘知己”,这不但安慰了他客中寂寞,更是撞到了他的勃发的野心上。这种试图通过征服女人开启征服世界路途的心态,也有点像《红与黑》里的于连。

如果说这还情有可原,他对帮助他的甄士隐隐瞒真心,就有点过分。收了甄士隐的银子而并不诚惶诚恐,是他的稳重有气质,但听到甄士隐真诚地建议他在十九日这个良辰吉日买舟西上,他明明另有主意,却始终一字不曾吐露,谈笑自如,就透出他骨子里的一种冷硬,他跟谁都不会交心的。
他辜负了第一个于他有恩的人,只要天时地利人和凑得好,还会有一连串的辜负
,就是这种人,后来者居上,从“半路途上哪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平儿语),变成社会主流,这是曹公不便直说的尖锐。
曹公在书中屡发免责声明:“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可比。”跌过跟头的人,自然有这样一种小心,小心归小心,想要说的话,他还是要想办法说出来。
他以《好了歌解》感叹世事无常:“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
就在这转换过程中,上升者与下坠者,在某个节点,打一个照面。这种原本凌厉的交集,在曹公笔下,被写得如此温情,若不是贾雨村太不仗义,差点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了。
这符合现实情况,他们得遇其时。
对于当时的甄士隐,贾雨村还没有变成一个讨厌的人,对于当时的贾雨村,甄士隐还是一个有身份有价值的人。
后来贾雨村想见贾宝玉,贾宝玉对他深恶痛绝,只因他已经黑化,完成了由有志青年朝庸俗官吏的蜕变。可以想象,即使“神仙一般人品”的甄士隐未遭劫难,对那样一副面孔的贾雨村只怕兴趣也不大。
贾雨村对于下坠之后的甄士隐同样无感,说是要帮他找女儿,得知英莲的下落,他也并没有表示过过多的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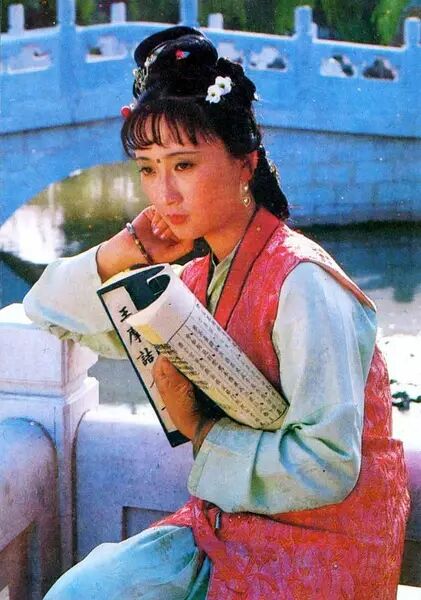
▲
8
7版《红楼梦》中的英莲
人和人常常是这样,交汇于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的时辰,互相看到对方的闪光,擦肩而过,别后经年,再见面时,物也非人也非,相对只觉得枯索。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