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照射的地中海海滩,孩子们在水边嬉戏,大人们在分享啤酒和食物,而玛丽·科克则陷入了漩涡般的海浪之中。她从未想过会在游泳时遭遇风浪,当她一次次被逆流推向深处、奋力前游却不能移动分毫时,恐惧包围了她。但仔细想想,她似乎没什么好恐惧的。
“没有环游世界,我不后悔;没有做成舞者、没有暴富、没有出名,我不后悔;没有孩子、没有伴侣、独自生活了大半辈子,因而能在被困于这片海中的时候了无牵挂,我也不后悔。”玛丽·科克想到,“我是个老女孩”这一认知让她能够平静地接受死亡,“我的离世不会改变任何人的生活。”
玛丽不着急回到水面,任由自己在浪中翻滚,再一次浮起时,她奋力抓住一块岩石,终于从海里脱险。她爬上海岸,回到没人等她的家里,独自清理伤口,睡觉,第二天依然会是普通的一天。
玛丽曾是一名记者,大学毕业后长期生活在巴黎,当过按字数计费的撰稿人,当过图书杂志的长期聘用记者,也当过拿着体面薪水的副主编,2019年出过一本介绍瑜伽历史和文化的书。在地中海遇险的这一年,玛丽43岁,刚被杂志社裁员,有了更多审视自我的时间,她结合自己的独身经历和对流行文化的观察完成《老女孩》这本书,中文版2025年1月上架。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女性选择不结婚、不生育的思考过程,以及成为老女孩将要面对的压力、挑战和境况。玛丽并不是在挑起性别对立,也没有提供一个解决结构性的性别困境的方法,只是在“Childless Cat Lady”(无孩爱猫女)成为一个争议性的称呼、在女性依然被视作要为低生育率负责的当下,清晰地发出另一种声音,同时也是在“Single Woman”(单身女性)成为文化热点时,清醒地罗列其中的利弊。
如同玛丽在书中所说,“它不是一份宣言,它不是要控诉你的生活、你的感情、你的性生活和你的家庭,告诉你需要打破它们带来的幻想和藩篱。这本书只是一个假设……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不勾选那道老师告诉我们的人生必选题,我们可以不与某人生活在一起或结成任何形式的伴侣,我们也可以不去做那份被描述为最伟大、最坚不可摧的母职。我们可以在这些必选题之外建立自我,找到为自己和他人建立结构的其他方式,我们可以在别处找到不同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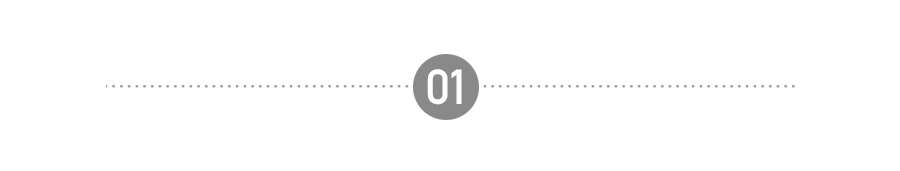
爱情的反面
翻开《老女孩》时正在乘坐高铁,邻座的大爷与我聊了一会儿天,得知我的年龄和婚恋情况后,突然问我需不需要他儿子给我介绍单位刚入职的博士。那个瞬间我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之中,好半天才想出一句礼貌的回绝。大爷的提议在一个默认的前提下产生——“所有人都应该结婚”,你很难用三言两语去打破这个观念,提议又是出于善意,你没法摆出针锋相对的姿态。
类似的情景玛丽·科克也遇到过很多次,对单身人士的批评更多以所谓“善意”的话语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有人因为我单身而替我担忧,不愿承认我的生活同样值得,或者不断告诉我母爱才是最高形式的爱。这种歧视主要表现为对我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轻视,以及反复强调我错过了某些极其重要的东西。”
“老女孩”这一词语曾伴随着强烈的社会耻辱感。更早以前,单身女性几乎是不容于世的异常存在。玛丽在书中写到中世纪的隐居女,在女性禁止独身的中世纪,如果女性不想结婚,或者不想和丈夫生活在一起,除了进修道院,只能把自己监禁在狭小的塔楼里度过余生,把自己与世界、他人以及能让她的存在合法化的男人全部隔绝开来。
如今,对女性独身的歧视以另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展开,渗透着社会观念的流行文化将真爱至上的价值观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裹挟住每一个人。玛丽总结:“我们都受到那些关于绝对爱情的伟大叙事以及浪漫喜剧的深刻影响,这些故事使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注定会经历一场伟大的爱情,最终安定下来,无论我们是否心存犹豫或经历过失败。”即便是在男女主角分别为离婚律师和职业骗婚者的电影《真情假爱》中,见识过婚姻的不堪和自私的两人最终还是毫无保留地相信和爱上了对方。
与之相对应的是,银幕上老女孩的形象总是消极的——穿戴破旧的羊毛衫、软塌塌的帽子,眼神刻薄、话语尖酸、身形干枯,一股颓败之气。“她们要么是路人甲,要么是次要角色。她是尖酸刻薄的老姨妈,是穿着手织毛衣的办公室同事,是女主人公略微不合群的好朋友,是公园里和鸽子说话的疯女人,是楼宇里的邻居。”玛丽写道,老女孩只在一种情况下能成为真正的主角——当她们只是临时老女孩时,而故事则会围绕她如何改变自身,寻找到真爱。
这些敏锐的评论让我想起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刺猬的优雅》。54岁的独居女人荷妮是一栋公寓的门房,她身材矮胖、不修边幅,而新搬来的日本绅士却透过荷妮的外表看到了她的学识、涵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在荷妮逐渐卸下伪装、准备迎接爱情时,她出车祸死了。现在想来,荷妮是为数不多的“老女孩”主角,她初始的形象恰恰就符合人们对老女孩的偏见,而她的闪光点要靠一个给予她爱情的男性才能展现出来。

▲电影 《刺猬的优雅》 剧照
流行文化越是美化爱情,现实越需要勇气去选择超越爱情的生活。在2024年国内以单身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中,《热辣滚烫》中的杜乐莹在遭受背叛和欺辱、承受住拳击的苦训后,才有了拒绝前男友的自强;在《出走的决心》里,咏梅饰演的50岁中年女人,在为家人奉献了大半辈子且长期忍受丈夫的贬低后,终于决定为自己而活。历经磨难后的独立似乎才是可以接受的,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更轻盈地作出选择呢?
玛丽只是在多个失望的约会后,萌生了暂时退出爱情游戏的想法,给自己喘口气的时间。可是单身带来的时间和自由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满足,因而保持了这种状态。“我们可以选择退出男人的世界,可以不组建家庭。这并不是一条殉道者之路,相反,这可能是一条解放之路。这条路也可能带来幸福、充实、完整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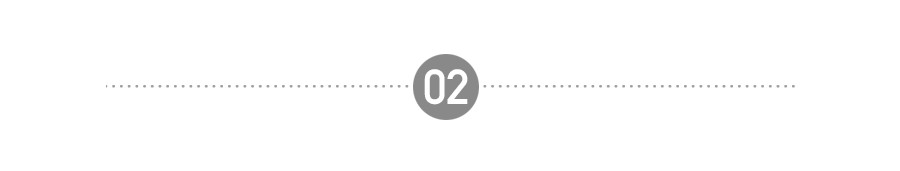
赌博,以自由为代价
退出爱情的世界后,玛丽察觉到生活最大的变化是时间变多了,她不再花费时间去思索关于另一半的事情,例如“做什么会让他高兴呢”“他为什么会那么说呢”,她也不必在工作之余处理伴侣和孩子的日常事务,得以从琐事中抽离。
在玛丽看来,结婚像是一场豪赌,明知道中头奖的机会微乎其微,大家却仍然会参与其中,心怀希望,幻想自己能成为那些幸运儿中的一员。然而婚姻意味着你必须与伴侣共享一切,床、房子、财务等等,而共享恰恰成为限制女性自由和个人追求的桎梏。“因为在这种所谓的平等分享理念下,我们很容易看出,最终总是女性为了维持伴侣关系的和谐,牺牲自己的职业、个人、智识或情感上的抱负。”
婚姻中的性别不平等能够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学研究以及统计数据中得到佐证。例如,女性在财务上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2020年世界妇女:趋势和数据》报告显示,全球只有不到50%的处于工作年龄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一数字在过去的25年里几乎没有变化。女性承担了大量的无偿家务,养育子女和照料老人的责任也通常落在女性身上,这限制了她们的经济潜力,很难积累个人资产或实现经济独立。
玛丽注意到婚姻的另一种常被忽略的隐性“压迫”——不得不接受来自伴侣的“监视”,“对方会期待知道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花钱做了什么。即便在一段看似愉快的关系中,这种监视也被视为(婚姻)契约的一部分。”而一旦我们将自己置于他人的“监视”之下,也就意味着将自己时刻暴露在他人的评判之下,你的状态不仅仅事关个人,形象、情绪、兴趣、习惯……你的改变都将被对方用缔结契约时的状态来比较,你失去了改变的自由,或许会因此错失全新的自己。
玛丽着重阐述女性可能在婚姻中被剥夺的这两点可以归纳为财务自由和空间自由,这与近一百年前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谈论女性和小说时所得出的结论相似,“想要写小说或诗歌,你每年必须有五百英镑的收入,以及一间带锁的房间。”有了这两重自由,女性才可能拥有“毫不妥协的行动自由”。
站在一个老女孩的角度,玛丽将自己与进入婚姻的朋友进行比较,她愈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逃离了什么。她不用再时刻保持自己的形象,当她状态糟糕的时候不需要假装良好,情绪崩溃的时候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也不必为另一半付出情绪劳动。她做家务是为了照顾自己,而不是为家庭提供无偿劳动,她所做的不会得到任何奖励、赞美或认可,但同时也不用背负任何期望和命令。
她不用为了他人的事业、他人的幸福、他人的自洽而努力,不再试图在“奴役”中获得快乐,而只需要为自己的成长负责,“不需要孩子或伴侣当我的镜子,我也依然知道我是谁。”

▲玛丽·科克书架上的 《易经》 图/受访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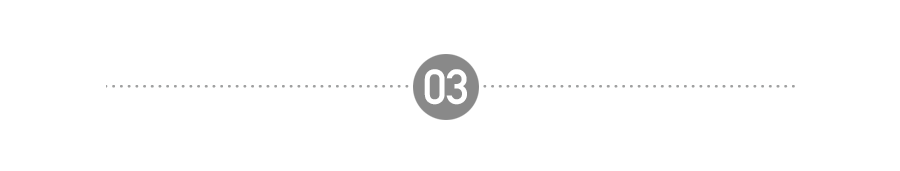
不再担心自己“只是个好人”
刚开始从狂热寻觅爱情的状态中退出的时候,玛丽一度怀疑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来自另一半的“监视”和需求换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关注和需要,当你没有一双注视着自己的眼睛时,你要如何去找寻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当你的生活不再围绕一个同居者时,你要通过什么来确认存在的意义?
对比20世纪的探险家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玛丽曾感到自卑,这位探险家抛下丈夫和孩子,游历欧洲和亚洲,成为第一个抵达拉萨的西方女性。这仿佛是在提醒玛丽,“我们的人生若是在个人问题上没有得到圆满,就必须要用一场宏伟的奇遇加以弥补。”
然而玛丽自认没有像探险家在所到之处插上旗帜一样,在某个领域留下标记,“我的独身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非凡的命运,没有给我带来令人惊叹的冒险,现在,将来,我都会过着平凡而普通的生活……”玛丽没有将独身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理解复杂的学问,攻读博士学位,也没有用来学习有助于事业的技术。她仅仅用那些时间记下鸟类的名字、学画梵文字母、学习编织、练习瑜伽的下犬式、阅读娱乐小说……后来她想通了,“无目的地学习,无目的地思考,并努力为此创造尽可能多的空间,这不正是我们作为人类唯一的余地、唯一真正的自由吗?”
玛丽意识到独自生活是需要学习甚至训练的,不必给自己施加压力,期待立刻从中获得什么,“这就像跑步,一开始觉得很难,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跑,浑身疼痛,但随着不断练习,你会逐渐适应,开始感到乐趣、享受它”。
出版《老女孩》之后,玛丽与一群曾遭受暴力的业余表演者共同创作了一部舞剧。目前,她正在写她的第三本书《转弯之后,就是我的家》(非正式译名),探讨“家”或“归属之地”的含义。“我渴望做一些事情,比如写书,但我并不把这些看作个人成功的标志或成就。我在乎的是在我想做的时候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论这件事能否获得成功。”
法国女歌手恩罗恩罗的一首歌《只是个好人》曾引起玛丽的焦虑,歌词写出对亲密关系和自我实现的渴望,玛丽担心她是否会如歌词里所说的“向面包师问好,为老奶奶开门”,然后在自己的葬礼上被朋友们评价“只是个好人”。
现在玛丽不这么想,她开始为那些不会有任何回报的事情付出,接受那些无法报答的帮助,在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之间建立“良性循环”,人际之间的弱联系在玛丽看来并不脆弱,“这些关系摒弃了占有欲,更公正,也更尊重他人。”
摆脱占有欲后,玛丽不再将对虚无的恐惧误认为是对被爱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