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柏 林 童 年(节 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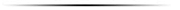
瓦尔特·本雅明 / 王涌 译
少年读物
从学校图书馆里我得到了最心爱的书,它们是分发给低年级学生的。班主任喊到我名字以后,那本我要的书就踏上了越过一张张课桌走向我的旅程:一个同学将它传给另一个,或者它会越过同学们的头顶被交到我手中。曾翻阅过它们的手在书页上也留下了印迹,装订书页并在上下两端突出的装订线也脏乎乎的。尤其是书脊显然忍受了许多粗鲁的使用,因此封面和封底无法对在一起了,书的切面歪斜着,形成了一层层小阶梯和平台。有些书页上还挂有细细的网线,宛如树枝间晚夏的游丝。在初学阅读的时候,我曾把自己编织其中。
书被放在一张过高的桌子上。阅读的时候,我堵上两只耳朵。这种无声的叙说我何尝未曾聆听过?当然不是听父亲说话。我冬天站在暖意浓浓的卧室窗边,外面的暴风雪有时会这样向我无声地叙说,虽然我根本不可能完全听懂这叙说的内容,因为新雪片太迅速而密密地盖住了旧雪片。我还未及和一团雪片好好亲近,就发现另一团已突然闯入其中,以致它不得不悄然退去。可是现在时机到了,我可以通过阅读那密密聚在一起的文字去寻回当初我在窗边无以听清的故事。我在其中遭际的那些遥远异邦,就像雪片一样亲昵地交互嬉戏。而且由于当雪花飘落时,远方不再驶向远处,而是进到了里面,所以巴比伦和巴格达,阿库①和阿拉斯加,特罗姆瑟②和特兰斯瓦尔③都坐落在我的心里。书中久置的气息缭绕在这些城池中,其中的流血和惊险是那样地让我心醉神迷,以致我对这些被翻破的书本永远忠心耿耿。
或许我还忠心于那些更破旧、已无法再找见的书籍?也就是那些我仅在梦中见过一次的美妙无比的书籍?这几本书叫什么名字?我除了它们已失踪许久和再也无法找见之外,便一无所知。而梦中,它们静躺在一个柜子里,醒来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柜子是我从未见过的。可是在梦中我们就像是老相识。这些书不是竖立着,而是平躺在柜子里一个气候多变的角落。书本里是雷雨交加。随意打开一本,我便会被带入一个封闭的世界,那里变化多端、迷糊幽暗的文字正在形成孕育着纷繁色彩的云朵。这些色彩翻腾着,变幻不定。最后,它们总是变成一种宛如被宰杀后动物内脏颜色的紫色。那些书的名字与这种不被重视的紫色一样不可名状和意味深长。我觉得,它们一本比一本离奇,一本比一本亲切。可是,就在得以拿到那本最好的之前我醒了,还没来得及触摸一下那几本旧旧的少年读物,哪怕是在梦中。

一则死讯
那时我大约五岁。一天晚上,当我已上床躺着的时候,父亲出现在我的房里,来和我道晚安。他显然不是情愿地告诉了我一位堂兄的死讯。这位堂兄年纪已经很大,与我也不怎么相干。父亲在思忖着整个事的来龙去脉,我对他的叙述有些心不在焉,然而对于那天晚上房间里的气氛却无以忘怀,似乎我当时就预感到某一天我还会与它发生关联。在我早已成年后,人们告诉了我那位堂兄死于梅毒。当时我父亲来到我房间是因为不想一人独处。可是,他找的是我的房间,而不是我。那天晚上,我的房间和我都不需要知已。

捉迷藏
我已经知道这间居室里的所有藏身之处,而且回到这些藏身之地就好像回到人们肯定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一所房子里那样。而现在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我屏住呼吸,被物的世界围得严严实实,这物的世界对我来说变得可怕地清晰,而且无以言状地与我靠得这么近。只有一个被施以绞刑的人才会如此这般地明白绳子和木头究竟意味着什么。躲在门帘后面,这个孩子自己也变成某种吹动着的、白腾腾的东西,变成了一个鬼魂;蹲着躲在餐桌下面,那张餐桌便使他成了神庙的一尊木制偶像,餐桌那有雕刻的桌腿便是支撑起神庙的四根梁柱;躲在一扇门后面,他自己便是门,并将门当作沉重的面具,以一个超凡巫师的姿态使所有不知内情地跨入门槛的人迷惑。他必须不惜一切手段避免被人看见。要是他被发现而做鬼脸的话,人们会跟他说:只需作敲钟样就行了,而且所作的样子必须一直保持下去。我在藏身之处明白了其中的奥妙。谁发现了我,谁就能将我看成是桌子下面一个神情凝固的神像,就能将我永远当作鬼魂织入门帘中,还能将我终生逐入沉重的门里。所以,只要搜寻者一找到我,我便会用大声叫喊来驱走为使我不被发现而如此这般让我隐身的恶魔——实际上,还未等到被发现时刻的降临,小孩就会发出这种自救的叫喊,以应对这一时刻的到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知疲倦地同这样的恶魔进行抗争的原因所在。在这样的抗争中,整个居室是我所用面具的武库。然而每年一次在神秘的地方,在屋中摆设那空空的眼窝以及张开不动的嘴里,会藏有礼物。这种让人着迷的体验会变成科学。作为父母房间的工程师,我对他们那阴沉沉的居室不再迷恋而去寻找复活节彩蛋。

爱| 爱情| 善意| 感情
孩子| 父母| 父亲| 女儿| 教育
命运| 位置| 快乐| 欲望| 妥协| 弱点
道路| 人生| 沉默| 真实| 觉醒| 尊严| 使命| 本质
智慧 | 年轻|自白| 友谊 | 大自然| 雄心 | 谦和 | 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