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城区洪殿街道黎二村是温州市著名的城中村,距温州的黄浦江——瓯江南岸不足800米,距市区最贵豪宅鹿城广场2.7公里。
黎二村几十幢破旧的居民楼在两个月之后会被夷为平地,一些极为破旧的房子被鉴定为C级危房,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尽快“清租”,而D级危房则被贴上了封条,不得住人。
黎二村的房价目前约为1.5万元/平方米,根据鹿城区采用的货币化安置方案,居民可获得2万元/平方米的补偿。这让拆迁工作几乎没有阻力。
如无意外,这批手握现金的拆迁户,会形成大量新增置业需求。之前,已有很多温州拆迁户走进售楼处。去年个别新开盘项目中,持拆迁补助的购房者占比一度高达50%,一些改善型楼盘中,拆迁户比例也达20%-30%。
等待拆迁的黎二村不是孤例,这背后,是温州市从去年启动的声势浩大的“大拆大整”专项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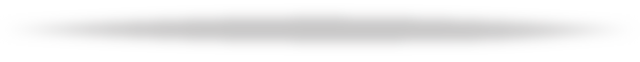
“大拆大整”包含城乡危旧房治理改造、“四无”生产经营单位集中整治、违法建筑拆除、城中村改造、流动人口管理、出租房整治、市区旧市场搬迁整治提升、双屿综合整治等八方面内容。
“大拆大整是个民生工程,但是影响到了房地产市场。”温州市房地产估价师与经纪人协会副会长陈德赚说。
为了推动拆迁力度,在货币化安置时,温州政府给出了明显高于房屋市场价的现金补偿。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当地一居民位于鹿城最核心地段的几套旧房被拆,共计约1000平方米,获得3600万元赔偿,补偿标准几乎等同于周边在售新房均价。
“如果选择实物安置,要四五年后拿到房子,政府一次性给出现金安置,等于是以5年后这一地区的房价进行收购,这很容易让人接受。”中梁地产瓯绍区域公司董事长冯植解释。
按照温州政府此前的指导政策,拆迁户如果一年内在市区范围内购买商品房或者有产权的安置房,最多还可获得10%的购房补助。
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温州市区房屋征收货币化安置达到3423户,货币化安置比例从2015年2.6%提升到2016年23.98%。
截至目前,瓯海区的货币化安置升至13%,同比提高8%,预计今年全区货币化安置比例将提到40%。而鹿城区今年的货币化安置比例目标是50%。
今年,市区计划完成24000户以上城中村改造任务,如果达到50%的货币化安置,至少会产生1万户手握丰厚现金的家庭。
该政策曾直接推动了一些楼盘的去化。位于温州市平阳县的滨江豪庭有1000套房源推向市场,2015到2016年只卖掉了30套。2016年11月,它成为温州市官方号召项目,如果在拿到拆迁款的6个月内购买滨江豪庭,可以获得政府10%的补贴。“一夜之间,去化就完成了。”知情人士说。
温州市委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推出的《2017年温州蓝皮书》指出,货币化安置对商品房交易的推动不可忽视。
截至2016年11月,龙湾区近3000户安置对象中超过1/3领取了10%的购房补贴,这一人群占据了龙湾区住房成交量的23.5%。
对政府来说,货币化安置的好处明显,按照鹿城区区委书记李无文的话,“腾出的土地可以及时上市拍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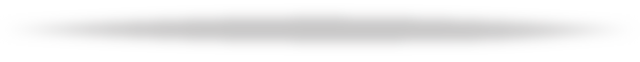
拆迁户成了开发商竞相争取的客户。
去年开盘的中梁首府壹号院,据统计有20%-30%的客户为拆迁安置购房;接近碧桂园的人士透露,碧桂园在温州的第一个项目,持拆迁补助购房的人占比达50%。
《温州蓝皮书》认为,城中村改造签约安置有购房需求的比例在60%-80%;短期内市区商品房价格几乎不会下降。
因此,去年温州楼市经历了有史以来成交量的最高峰。
据朗兆市场研究中心数据,2016年温州商品房供应套数54000套,同比上涨了45.79%;商品房成交套数64872套,同比上涨50.28%。改善需求爆增,市区成交住宅中,144平方米以上的占到65%。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温州楼市开始复苏,目前价格整体较为温和、健康。”冯植表示,即使在全国房地产空前火爆的2016年,温州的表现依然平稳。
冯植所在的中梁地产,是温州的龙头房企,曾号称温州每卖三套房就有一套是中梁的,对当地市场极为熟悉。“我们分析过客源,市场基本上靠本地自用为主。今年成交有可能超过去年,主要就是大拆大整带来的大量需求。”
一个不容忽略的现状是,多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温州楼市的实际库存去化周期已经降低到3-3.5个月,基本上处于无房可售的状态。
极低的库存让外来房企虎视眈眈。
4月24日,恒大以17亿元拿下了温州县级市瑞安的90亩商住地块,使瑞安的商住楼面价突破1万元/平方米。
6月29日,恒大和碧桂园在瑞安塘下镇塘口村的土拍会上正式对决,历经3小时106轮报价,双方将单价从起始的4100元抬升至8900元。
目前旭辉、融创、金茂等诸多品牌房企都有进军温州的意向,金茂就很有可能在瓯江口新区拿下大规模地块进行一级开发。
冯植表示,本土房企并不惧怕和外来大鳄的竞争,“但也担心,随着他们的进入,会刺激地价大幅提高。”
由于历史原因,近期以来的土地火热并未体现在房价上。“土地溢价率很高,但房价很难涨得起来,因为温州市民已经不愿买太贵的房子。”陈德赚分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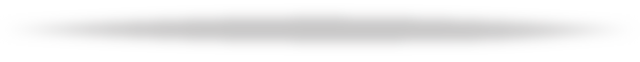
这个经历过房价第一、又一夕腰斩的城市,伤痛的记忆挥之不去,控风险的意识似乎也根深蒂固,无论是政府,还是买房人。
温州第一豪宅鹿城广场最高峰时单价近10万元,目前在售二手房单价不足5万元。
价格腰斩几乎是温州每个楼盘的“噩梦”。“原来温州人不是一层一层买,而是一幢一幢买。现在变得十分谨慎和理性,他们被伤得太深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炒房团已经基本绝迹。这一说法得到了所有受访人士的印证。
现在,温州人的储蓄存款出现持续攀升的势头。温州银监分局的数据显示,温州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
和房地产一样,温州的实体经济正在卸去过去的重担。温州银监分局统计,温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从2015年开始出现持续“双降”。
《温州白皮书》认为,通过一段时期消化,当前温州金融风险已现消退迹象,呈现后危机时期特征。
房地产抽干实体经济的现象,在温州是真实存在过的——这一度让房地产和实体经济都陷入过深渊。
2010年11月29日,温州师范学院操场作为住宅用地挂牌出让,拍卖价格从19.5亿元喊到37亿元,被置信地产拿下,成为当时全国总价地王,3.7万元/平方米的楼面价纪录,在温州至今未破。获胜者置信地产集合了108个温州企业主,被看作是实业家抱团炒房的典型案例。
时至今日,这个名为“置信原墅”的项目还有36套剩余房源,标价4.2万元/平方米。最低时,它的售价是3.5万元/平方米,比楼面价还低2000元,一位熟悉项目的人士告诉记者,这个项目亏了15亿元。
2010年6月,温州皮革龙头企业瑞新牵头37家民企组建财团,筹资20亿元,8月,以11亿元拍得瓯海区地王,楼面价超过2.6万元/平方米。这是它第一个房地产项目,也是最后一个。
2011年,瑞新君庭勉强入市,一期单价仅为2.2万元,即便如此依然滞销,公司先后被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追债。董事长徐士淮压力巨大,不久离开人世,成为了温州实业家败走房地产最悲凉的注脚。
“温州是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周德文说。
多年来,温州地方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难以摆脱。2014年一份《45个楼市限购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分析报告》指出,温州属于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的城市之一,依赖程度超过80%。在财政收入惨淡的2012年,温州甚至一次性推出 3220亩土地,彼时的温州市长陈金彪亲自出面当推销员。
记者综合温州统计局和当地民间研究机构的数据,2013年温州市土地出让收入450亿元,财政收入566亿元,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高达79.5%;而2016年土地收入348亿元,财政收入724亿元,占比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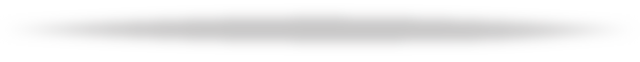
如今,经过4年多低位盘整,温州楼市终于成了一个看似正常的市场,但它背后依然暗流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