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载自全媒派
距美国纽约市100英里的东汉普顿长岛上,一片绿荫环抱的中心,便是罗斯中学(Ross School)的所在地。这所学校由Steven
Ross先生于1991年创立,由玻璃和石块建造而成。如今,来自长岛及世界各地的学生,已在这里寄宿并上课450多天了。在校园的后半部,高中部教学楼的前方,是一座立着胜利女神像的喷水池。
创校20余年,罗斯中学凭借自己独特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理念,成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典范。本期我们转载了全媒派(ID:quanmeipai)编译《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文章,带你到罗斯中学的校园和课堂中一探究竟,解锁这所私立中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独家奥秘。

打造媒介环境,重塑媒介感知
11月的某一天,穿着卡其色海军蓝校服的学生们蜂拥进教室,房间里霎时充斥着各种语言的吵闹声。大家在一张U型桌旁就座。而后,33岁的老师PaulGansky,穿着一件嵌有浅色条纹的灰色夹克走进了教室。
Gansky给孩子们展示了一张工厂图,图中是一排排装着机械手的黄色机器。
简单介绍了报告内容后,Gansky问同学们:“你们觉得组装电脑的工人工资多少才算合理呢?组装一台电脑又需要多久呢?”
大家众说纷纭。但是在Gansky揭晓了真实数字之后,孩子们都感到非常震惊。报告显示,这些工人的平均工资为250美元(约1676元)一个月,还要扣除18美元(约120元)的房费和面试报名费。孩子们迅速记下笔记:几百名工人挤在一间单人房中,低强度辐射和高温伤害,以及,可怕的自杀率。Gansky鼓励孩子们思考,为什么这种大工厂强制工人用有毒的香蕉油擦拭屏幕、清除指纹后才能将电脑包装并运往世界各地,“好像这台机器根本就不是人工组装的一样”。

这门“电子商务”选修课,就是罗斯中学媒体素养课程之一。该课程旨在教学生如何生产、消费不同类型的媒介,以及如何对一则报道提出质疑——即如何将一则报道拆分、变换,并找寻新闻报道者试图掩饰的漏洞。
对Gansky来说,
将媒介素养纳入文化产业教育,就是为了重塑孩子们在这个两极化世界中所丧失的媒介感知。
“你们正身处在一个为你们量身打造的媒介叙事环境中”。Gansky坦言,孩子们全都很活跃,通过媒介素养课程,他看到了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小家伙们开始去质疑,像探索他们的电子游戏一样去探索一则新闻报道。
发展历程一览
Steven Ross的妻子CourtneyRoss不在汉普顿时,常带女儿一起环游世界。她意识到,这样的机会可以帮助女儿在所接触到的事物和文化之间建立联系。1992年,Steven去世后,Courtney将3亿3000万美元砸进了罗斯学校的建设中。
为了规范学校的学术形式,Courtney调动自己的人脉网络,招贤纳士,在1995年聘请了诗人兼历史学家William Irwin Thompson及混沌理论家Ralph Abraham,共同设计了“
螺旋形”课程
,将各学科主题连结到一个叙述“人类意识演化”的故事中。学校早期只收女学生,没有固定的课时和学习时间的限制。
而媒介素养课程想法的落地,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学校在1996年聘请的纪录片制片人Marie Maci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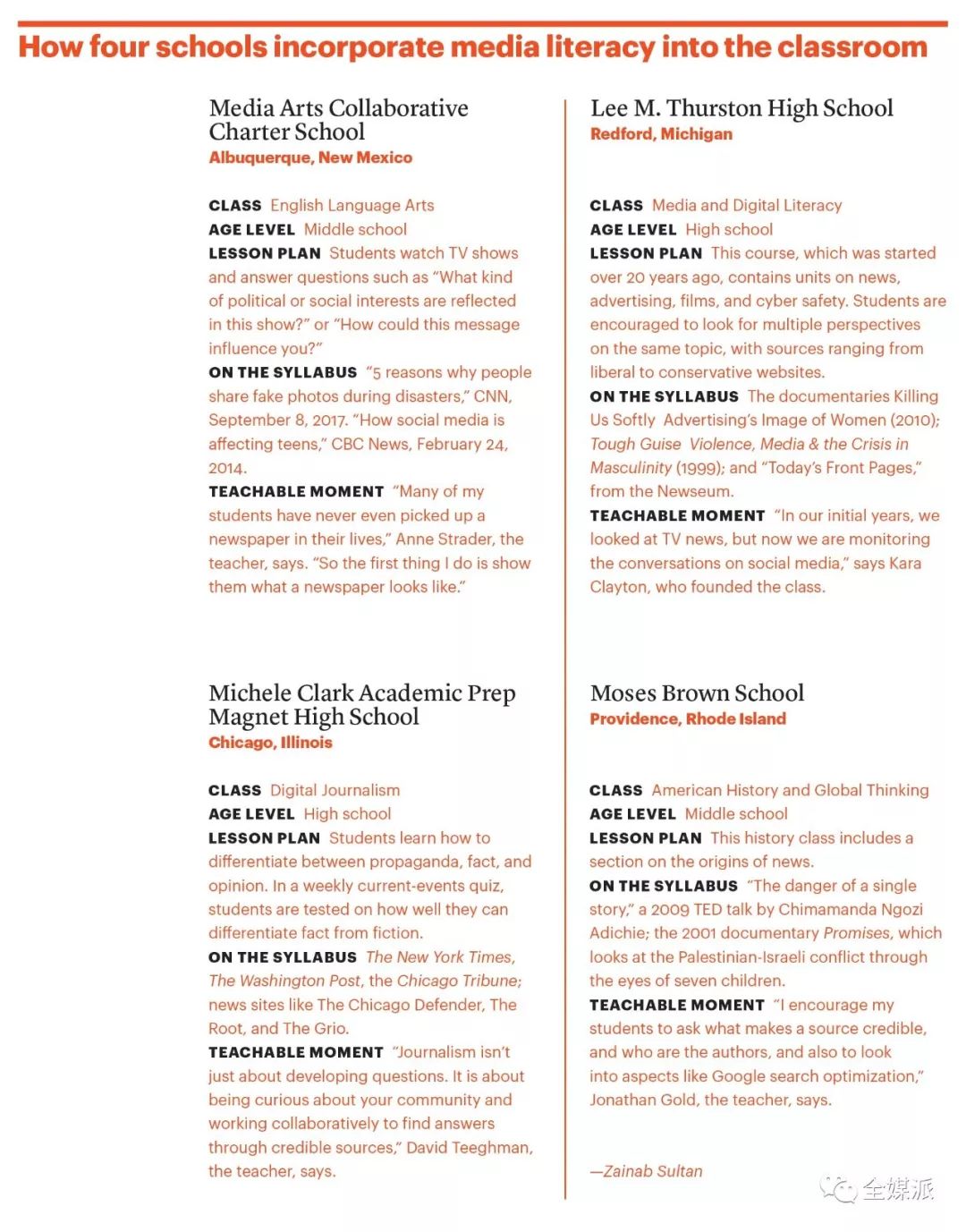
“我在罗斯学校的头几年,学校氛围极其活跃,大家会聚在一起讨论时事和各自领域的尖端问题”。Maciak回忆,有一天学生们跑进她剪片的摄影棚,好奇地问她在做什么。“大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不到一年,学校便叫我提出一套方案,把媒介研究纳入课程设置中”。
Maciak建议将媒介课程的核心定为“建构与解构”
——教学生们如何生产媒介
,并使用它创造改变。之后,Maciak列出了大纲,阐明了如何确保孩子们能够自由生产自己的故事,同时也能保持批判性思考。
Maciak将学生的媒介课程内容与他们在其他课程学到的知识整合到一起。比如Maciak曾制作过一部关于叙利亚难民的纪录片,于是他就为孩子们与一群居住在大马士革的伊拉克儿童建立了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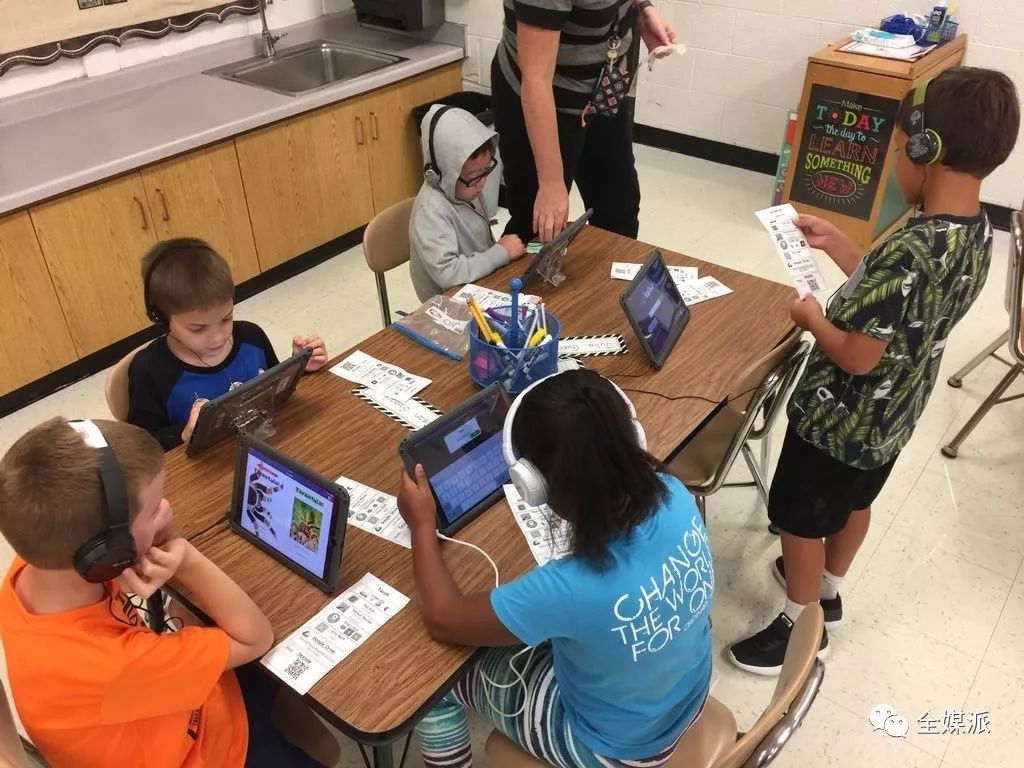
之后,
技术进步进一步推动了罗斯中学每节课程的发展
。相机变得小巧而价格亲民,这为制片提供了便利,但是剪片需要孩子们花很多时间,这与学校的课表并不契合。于是,制片课就成为了一门选修课或独立研究课。
“
现在在必修课上,我们把全部重心放在理解媒介是如何运作的
”。孩子们从关注《泰晤士报》和CNN等传统媒介,到如今开始关注《民主杂志》等期刊。
呼唤质疑精神和思考能力的回归
如今,我们普遍认为,在电脑和手机普及后出生的
“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
比其父母一代更善于处理和分析源源不断的信息。
然而这些被认为是“屏幕大师”的孩子们,在解读那些他们乐于分享的信息上,却仍是个新手。Instagram、Snapchat等社交媒体上的“迷因文化”使事态更加复杂。
2015年,斯坦福大学的历史教育小组发布了一项调查,衡量初中到大学的青年人对互联网信息可靠性的分析能力。
但是在任何一个阶段的任何一个案例中,学生所展现的分析能力之匮乏令人震惊。
研究结果表明,203名初中生中,有超过80%的人认为“原生广告”,甚至包括带有赞助内容的广告,都是合理的新闻报道。直到高中快结束,学生才开始逐渐意识到“事实可能是被建构的”。
Gansky称,美国学生判断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能力“通常是最差的”。他们很自信自己对是非对错的判断,常常不做基础的调查研究。“
他们通常相信自己的情感
”。

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的确有很多方式,但是最有效的方式,不是仅仅停留于将媒介素养作为一种识别假标题或是核实真相的技能,而是要作为一种敏感度加以培养、教导及实践。
许多学校认为,从长远角度看,媒介素养的培养是一件既耗时又费力的事,尤其对那些资源不足的乡村学校来说,负担媒介素养教学的基础设施费用更是困难。但罗斯学校的Hobbs认为,
有意义的媒介素养教育并非只能是贵族学校的专属
。
罗斯学校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课程,为学生提供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师生共同在课堂上剖析青少年的“迷因文化”,探讨他们获得信息渠道的来源及其原因,倾听新闻记者们的调查经验分享。
一旦孩子们开始学会对他们在互联网上接触的信息持怀疑态度,任何事物都可以变成可思考的问题
。“逼迫”孩子们质疑他们的所见所闻,已是媒介教育的大势所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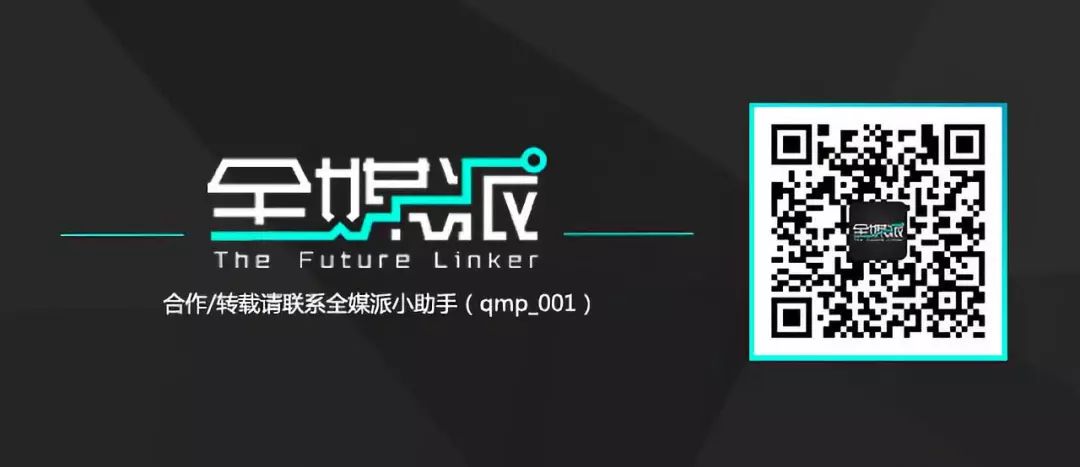
你能为我摘一颗星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