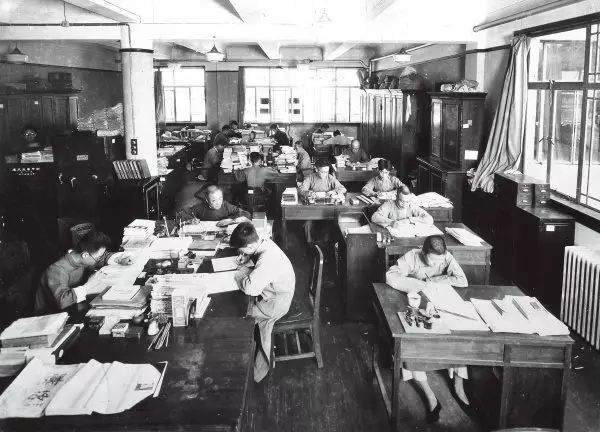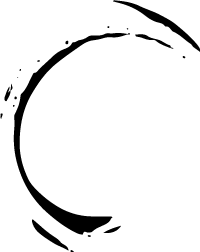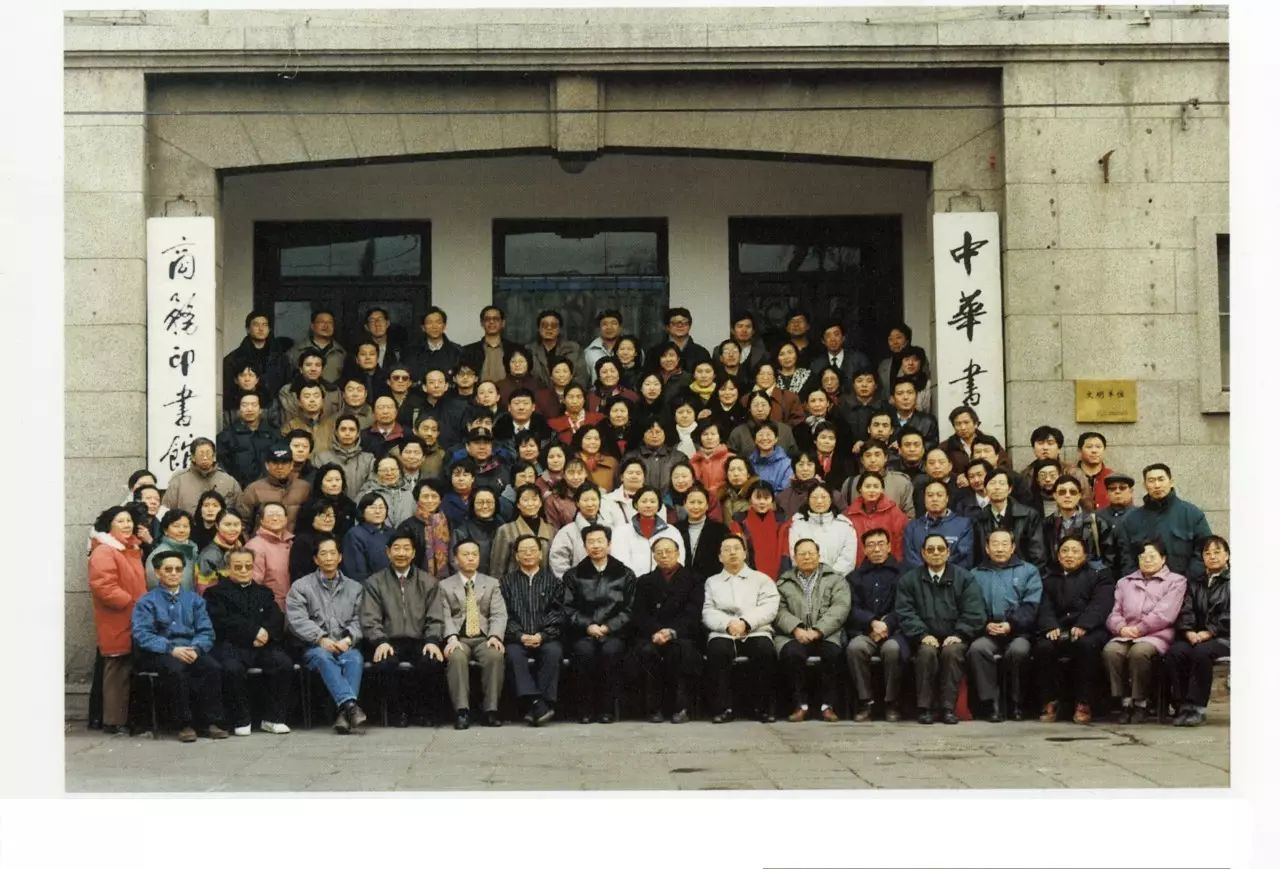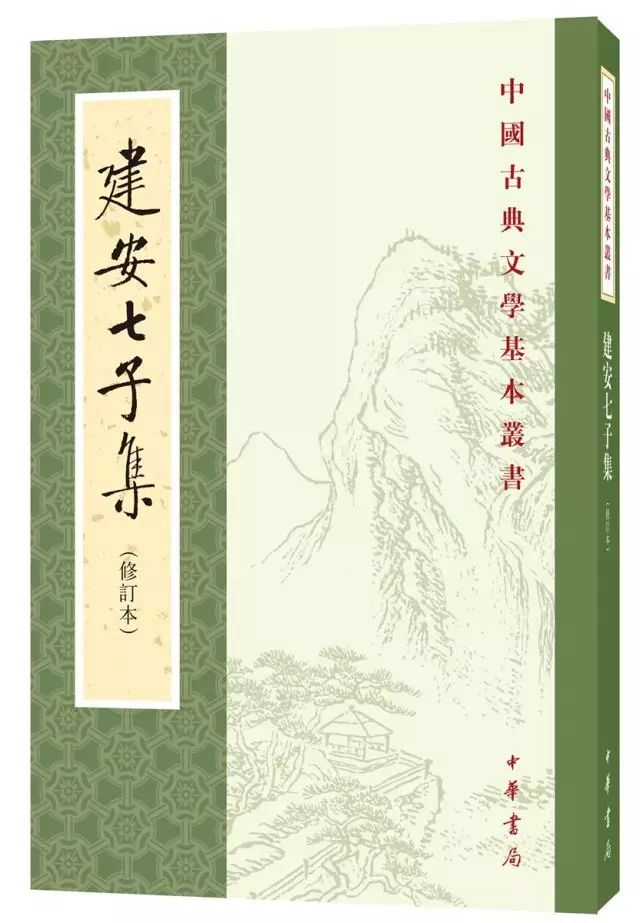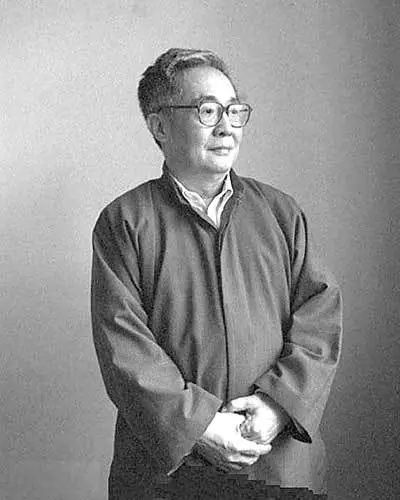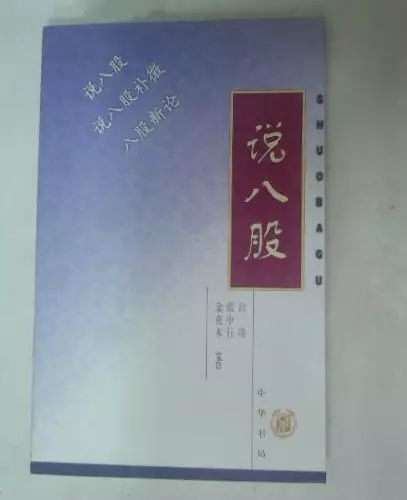专栏名称: 做書
| 记录出版者的努力和探索,让出版简单、有效率。 |
目录
相关文章推荐

|
为你读诗 · 《中国博物馆全书》,一口气“逛遍”1000间博物馆 · 16 小时前 |

|
为你读诗 · 新的一年,听新闻,让孩子看世界 · 昨天 |

|
为你读诗 · 《哪吒2》番外强势来袭,后劲比电影还大 · 昨天 |

|
为你读诗 · 蒙曼讲诗词:腹有诗书,如草之兰 · 2 天前 |

|
新郑发布 · 新郑·文苑 | 离家之后 便会更想家 · 2 天前 |
推荐文章

|
为你读诗 · 《中国博物馆全书》,一口气“逛遍”1000间博物馆 16 小时前 |

|
为你读诗 · 新的一年,听新闻,让孩子看世界 昨天 |

|
为你读诗 · 《哪吒2》番外强势来袭,后劲比电影还大 昨天 |

|
为你读诗 · 蒙曼讲诗词:腹有诗书,如草之兰 2 天前 |

|
新郑发布 · 新郑·文苑 | 离家之后 便会更想家 2 天前 |
|
|
19楼 · 注意!最近这些卖得很火的东西竟易致宝宝性早熟!你家可能也有,赶紧丢掉 8 年前 |

|
奥斯CAR · 如果交警都这样,就不会有人违章了! 8 年前 |

|
济宁7890后 · 这绿帽子带的,真是稳啊!没毛病 7 年前 |

|
午夜漫画站 · 色系漫画:幸福暴走 7 年前 |

|
玲珑 · 【520专场】一个人吃的是饲料,两个人吃的才叫饭 7 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