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家王春林
既问苍生,也问鬼神
——关于石一枫长篇小说《心灵外史》
文 | 王春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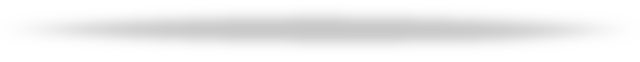
我们注意到,小说创作近几年来可谓风生水起的青年作家石一枫,曾经在关于《世上已无陈金芳》与《地球之眼》这两篇中篇小说的一个创作谈中明确表示,自己小说创作追求的根本目标乃是“不问鬼神问苍生”:“我恰好又在不看一肚子洋书就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环境里混过些年,于是概莫能免地啃过几套‘内部文库’、‘先锋译丛’之类的红宝书黑宝书。至于文学作品,连《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也不是没鼓起奥运精神挑战过,可惜看到一半儿,看出了我认识那些字儿而那些字儿不认识我的境界,只好怏怏作罢。等到腰围渐宽,对自个儿的要求放松了,再加上着实编了几年文学期刊又是一‘现实主义’杂志,在老同志的耳提面命和潜移默化之下,发现自己能够认同的审美标准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够不够‘可读’,读完之后有没有一点儿哪怕是小感动?感动之余能不能稍微耐人寻味地‘可想’?如果想来想去还想不明白,那就算一不留神写出过得去的东西了。而具体落实到个人操作上,则是通过塑造好一两个人物,再挖掘出这些人物与时代的勾连关系,来实现上面的效果。这种观念比较传统,甚至称得上陈腐,但也的确是我这几年的真实感受。而且要想实现那些哪怕中学课本里都讲过的‘文学原理’,恐怕也不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作者不停地琢磨人、琢磨事儿,琢磨社会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总之功夫在诗外,除了考虑‘怎么写’,还得考虑‘写什么’,更得考虑‘为什么写’。”“其他诸如情节走向腔调风格,个人觉得倒是末技。这年头大凡不那么认命的人,总会在‘别人让我怎么活’和‘我想怎么活’之间徘徊辗转,也会冷不丁地冒出点儿体验别人的人生,反观自己的人生的需求。写或者读那种‘不问鬼神问苍生’的小说,其动机多半在此。”①
在这段创作谈中,石一枫以充满幽默、诙谐色彩的话语所一力强调的,乃是在现代主义已然发生普遍影响的时代,坚持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理想的重要性。其所谓“不问鬼神问苍生”者,正是这种创作理想的形象表达。实际上,只要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熟悉的朋友,就都知道石一枫的“不问鬼神问苍生”这句话,是从李商隐《贾生》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诗句化用而来的。贾生者,汉代名臣贾谊也。李商隐诗作主要写汉文帝夜半时分召见贾谊,可惜的是,他们俩虽然交谈到三更半夜,贾谊却竟是白白地向前移席,因为皇帝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与天下百姓紧密相关的国计民生,而只不过是一些神神鬼鬼的事情。质言之,汉文帝之所以关心神鬼的问题,也不过是企图借助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贪求如何才能够长生不老。然而,假若我们超越李商隐的诗歌语境,将他的诗句与作家石一枫的小说创作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苍生”就可以被看作是普通民众的苦难生存现实,而“鬼神”者,则可以被理解为普通民众健康精神世界的构建问题。如果我们的上述理解能够成立,那么,你就会不无惊讶地发现,与《世上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这两篇中篇小说相比较,仅只是在时隔不久之后的长篇小说《心灵外史》(载《收获》杂志2017年第3期)中,石一枫就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某种自我突破。倘若说在前两篇中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石一枫的确是在“不问鬼神问苍生”的话,那么,到了他的《心灵外史》中,作家就确然是在真真切切地“既问苍生,也问鬼神”了。
实际上,只要对于这部或许是在向作家张承志的长篇小说《心灵史》致敬的《心灵外史》(之所以断定石一枫是在以《心灵外史》向张承志的《心灵史》致敬,根本原因在于,这两部长篇小说全都是与精神信仰紧密相关的作品)的叙事话语稍加留意,我们即可以一目了然地辨析出石一枫小说的特别味道来。是的,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我这里的具体所指,就是某种程度上独属于石一枫的一种文学比喻修辞。比如,“而来到西安之后,有一天我肚子疼得直打滚,校医开了包同样的药给我吃,几十条蛔虫就被浩浩荡荡地打下来了,如同在茅坑里下了一碗手擀面。”这是在写“我”打蛔虫。比如,“他说这话时,正在把一条剥好了的象拔蚌往嘴里塞去,但是因为蘸了过多的日本青芥末,便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喷嚏,看起来好像喷出了一股又长又滑的鼻涕。那条鼻涕就挂在他的嘴边,旋即又被吱溜一声吸了进去。”这是在写李无耻吃象拔蚌。再比如,“我便夺过了他本人的那一盒,拆开来一块一块地按碎,‘榨出了皮袍下面藏着的卵’,顺势又将那些蛋黄塞进了自己的嘴里,示威性地大嚼,嚼得直流黄汤儿,那模样好像正在兢兢业业地吃屎一样。”这是在写“我”如何大嚼大咽中秋月饼。够了,已经不需要再列举了。所举出的这些话语例证,已经足以说明石一枫的叙事话语特质了。
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石一枫的这些文学比喻都不仅非常地形象传神,而且也很明显地达到了某种叙事话语“陌生化”的效应。除了石一枫之外,我们的确未曾在其他作家那里读到过如此一种文学比喻。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能不承认,石一枫的这一类文学比喻有着令人作呕的“恶趣味”。将在茅坑里翻滚着的蛔虫,比作手擀面,将美味的象拔蚌,比作又长又滑的鼻涕,将吃美味的月饼,比作吃屎,无论其创造性如何,恐怕也都是令读者所难以接受的。人都说石一枫的文字中充溢着某种难以自抑的“痞子气”,这类看起来相当肮脏的文学比喻,应该就是这种痞子气的形象表现之一。
事实上,远离了这种“恶趣味”的文学比喻,石一枫也完全能够找得到其他同样恰如其分的语言修辞方式。更何况,据我所知,石一枫也是出身于一个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因此,尽管我非常明白石一枫的如此一种修辞方式显然具有亵渎与解构虚假神圣的特别艺术效果,但从内心里说却还是无法接受他的这种文学比喻。究其根本,这种令人作呕的文学比喻方式,所说明的,或许很可能是石一枫一种难以自控的恋污癖。然则,细细想来,此类“恶趣味”文学比喻的内涵恐怕又不止于此。倘若我们把石一枫的此类文学比喻与中国古代的禅宗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中恐怕便更深地隐含着石一枫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或者干脆说,就是一种世界观。
禅林语录载,临济宗为打破凡夫俗子之执情,并使其开悟,对审问“佛者是何物”者,一向都会以“干屎橛”来作答。盖屎橛原系擦拭不净之物,非不净则不用之。究其根本,临济宗乃是要借助于此种最接近吾人之物,以教斥其专远求佛而反不知清净一己心田秽污之情形,并用以打破学人之执著。很大程度上,我们也正可以在“佛者”“干屎橛”的意义层面上来进一步理解石一枫式污秽语的寓意内涵。
然而,正所谓瑕不掩瑜,只是作为个别片段出现的“恶趣味”文学比喻修辞,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心灵外史》真正的文学光芒。又或者,假若说“恶趣味”文学比喻的出现乃充分说明着石一枫内心里潜藏着的某种狠劲儿的话,那么,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凭借着这股发自内心的狠劲儿,石一枫才既可以尖锐犀利地洞穿社会现实的黑暗面,也能够异常敏感地意识到国人精神信仰层面上心灵深渊的存在。
具体来说,石一枫《心灵外史》中,作家对于国计民生表示强烈关注的“既问苍生”,集中体现在描写表现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想方设法探寻大姨妈曾经居住过的乡村世界那一部分。“我”之所以执意要去探寻这个地方,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在来看守所的路上,“我”出乎预料地遇到了不正常的大堵车:“然而刚一上路就碰到了堵车,一眼望去,收费站附近挤满了‘红岩’和‘斯太尔’……这种形态的交通堵塞通常发生在鄂尔多斯、大同、神木之类的城市,由此也可以推测本县是怎样兴旺繁荣起来的——无非是地底下挖出了什么宝贝。”其二,“我”在看守所从大姨妈口里得知,自己的那个村子早就没法住了。不仅大姨妈表示曾经得家园已经无法居住,而且那位警察对于身为记者的“我”的探访行为也一再地推三阻四:“他的口风更加让我生疑,觉得不去一趟简直说不过去了。”等“我”几经周折,终于战胜重重险阻抵达目的地之后,面对着差不多已经空无一人的村庄,“我”才真正搞明白为什么大姨妈有家不能归,为什么那位警察会对“我”的探访行为做千方百计的阻拦。
却原来,“我”的寻访地已经快称得上是哀鸿遍野了:“村里却一团寂静,几乎和海边鬼城有得一比,甚至更加让人心悸,因为这里偏偏是有人迹的——不是活人,却是死人。路边房子的大门两侧,有一多半挂着白对联,按照农村的习俗,这些人家无疑是正在办丧事或者刚办完丧事。”只有到这时候,“我这才明白了大姨妈为什么有家不回。一个地方要是每家每户都在死人,死到了写挽联的民间书法家都忙不过来的地步,那么,谁敢住在这里才怪。”至于死人的原因,却毫无疑问地与开矿有关。正如同石一枫已经明确揭示的,唯其因为在开矿的过程中,有什么化学元素从‘矿上’“润物细无声”地融进了水里,土壤里。所以,大姨妈他们方才永远地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却原来,地方政府为了一味地追求所谓发展主义的目标,为了追求所谓的GDP数据,不惜付出伤害村民生命以及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巨大代价。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经济的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乃是建立在无尽血泪的基础之上。我们寻常所谓“带血的GDP”云云,具体所指的,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种简直令人惨不忍睹的状况。借助于如此一种几乎称得上是哀鸿遍野的生存状况的真切书写,石一枫把自己尖锐犀利的社会批判锋芒首先对准了“带血的GDP”,对准了改革开放的所谓原罪。
依照常理,面对自己所亲眼目睹的这一切生存惨状,身为记者的“我”理应挥动手中的笔,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把这一切都如实地通过相关媒体向社会揭露出来。但实际的情况却是,除了想方设法从危险地带全身而退之外,除了更多地考虑大姨妈未来如何安置的问题之外,“我”其实一直保持着某种禁口不言,貌似什么都没有发现的状态。这就与此前打击“虫虫宝”传销事件中的那个“我”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一种对照。那个事件中,虽然“我”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找到并求出已经深陷传销泥淖的大姨妈,但从客观效果上说,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位记者,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卧底传销团伙,并最终取得了相关的一手资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假如‘虫虫宝’的人找到了摄像机并能正确操作它的话,就会发现我已经把打入他们内部之后的大部分所见所闻都拍摄了下来:晚上的例会、盛大的集会、宣讲、谈心、狂呼口号……我敢说,我搜集到了足以让同行们羡慕不已的一手素材,要是把它们剪辑成纪录片,足够获得新闻界的二流奖了。”不仅如此,到最后,当“我”在大姨妈的帮助下从传销团伙侥幸出逃之后,这一切冒险记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果然在警方打击传销团伙的行动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徒步走回县城之后,我立刻去公安局报了案,而后又给单位打电话。一个北京的记者被传销团伙绑架、拘禁,差点儿连命都送了,这本身就是相当劲爆的新闻。省内的执法系统迅速运转了起来,没过多久,捷报频传。”事实上,正是因为有“我”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警方才能够对传销团伙进行迅捷有力的打击。
两相比较,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自然也就是,同样一位“记者”,在性质同样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的表现,为什么前后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呢?要想彻底澄清这一问题,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那就是,就在“我”下决心要去寻访导致严重生态污染的矿区的时候,警察对“我”曾经发出过的警告:“‘恁俩咋一个比一个“死劲”,’警察被逼急了,迸了句河南话,随后说了个地址,却又补充一句:‘去时别说你是报社的,这也是为你好。’”警察本来应该是社会一切邪恶势力的对立面,但从他叮嘱“我”的话语中所隐约透露出的,却是面对某种超出了自我控制范围之外的邪恶事物的厌恶与无奈。唯其如此,他才会提醒身为记者的“我”千万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这种特定的社会身份很可能会给“我”带来别一种莫须有的灾难性后果。
依照常识,一般情况下,这个社会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竟然让记者与警察感到犯难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事情恐怕就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大姨妈居住地因开矿而导致的生态严重恶化,很显然正属于此种状况。说到底,唯其因为“带血的GDP”乃是与地方政府的发展理念紧密相关的政绩工程,所以它的存在方才会受到地方政府的特别保护。具体到石一枫的《心灵外史》,警察与身为记者的“我”,之所以会在打击传销团伙的事件中表现出色,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在于,这一打击行为更多地乃是地方政府意志的真切体现。相反地,到了开矿事件中,眼睁睁地看着矿物的开采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已经致使很多人无端死亡,但警察与“我”却偏偏就是无所作为,关键原因显然在于,这一开矿行为的行为主体乃是地方政府。现行体制下,无论什么事情,一旦政府下定决心,其他社会力量即使再不同意实际上也都无济于事。在现实社会已经跌打滚爬多年,已经熟知社会运行规则的“我”,之所以面对触目惊心的惨状已然禁口不言,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也因此,仅仅只是写出“带血的GDP”还算不上石一枫思考认识的深刻,只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写出身为记者的知识分子“我”面对如此一种惨状的被迫噤声,以至于敢怒不敢言,方才算得上石一枫在“既问苍生”方面抵达了某种更其深刻的思想境界。
“既问苍生”,固然是《心灵外史》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层面,但“也问鬼神”,对国人精神信仰层面上心灵深渊的存在做真切的深层透视,却更可以被视为石一枫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开拓。这一点,集中通过大姨妈这一被刻画得神灵活现的女性形象而凸显出来。
具体来说,在这部虽然篇幅相对短小但叙事时间跨度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长篇小说中,大姨妈精神信仰方面的疾患,乃集中通过四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而体现出来。
首当其冲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文革”期间本来情同手足的大姨妈对于母亲的告密出卖。这个故事,一直到了小说的后半段,才由与“我”的感情关系素来紧张的母亲转述给“我”。但在展开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加以澄清的,却是母亲与大姨妈之间并无血缘纽结的真实关系。大姨妈是厨娘的女儿,打小就和“我”母亲结下了很深的情谊。由于双方母亲先后离世的缘故,她们两位只能无可奈何地相依为命。但就是这样两位无可奈何地被迫如同涸辙之鱼一般相依为命的女孩子之间的亲密情感关系,居然也因为大姨妈的告密行为而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问题的关键,出在一些被刻意埋藏的字儿纸上:“家里的细软字画早已荡然无存,而母亲之所以藏下几叠字儿纸,无非是要‘留个念想’。”但即使是如此私密的一件事情,到最后竟然也被组织给知道了。亏得有大姨妈气喘吁吁地从她所工作的饭馆赶回来,主动替母亲承担了埋藏字儿纸的罪责,否则,母亲就将面临更严厉的惩处。即使如此,“随之降临在母亲头上的就是内部批评、公开批评、大过处分、留校察看……而这还是没被‘抓着现行’,因此获得从轻发落的结果。”在那个非正常的政治高压时代,已然有罪名在身的母亲,为了寻条活路,只好被发配到三线去接受思想改造。只有到了火车站送别的时候,大姨妈方才充满悔意地承认:“母亲私藏手稿的事情,是从她那儿传出去的,并且不是无意泄露,是主动检举。”
那么,大姨妈为什么要以告密的方式出卖情同手足的母亲呢?到后来,大姨妈方才坦承,自己的动机不过是出于对革命的相信:“只不过大姨妈事到临头内疚了。后悔了,革命意志没那么坚定了。”就这样,“大姨妈史无前例地出卖了母亲,却又一如既往地豁出命来保护了母亲。”对于大姨妈的告密出卖,母亲的态度,是既理解却又不相信。从人性的角度,母亲理解大姨妈的告密行为:“‘多简单啊,那年头人人都这样。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的多了。你姥爷就是被跟他一起赏菊花吃螃蟹的朋友举报的。他被定了性以后,我也必须表态跟他划清界限,否则就上不了大学。既然人人这样,也就没什么不能理解的了。’母亲说,‘我不原谅那个世道,但也没有怨过那个世道里的任何一个人。’”但从个人关系的角度,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母亲都不肯相信大姨妈的揭发动机乃是因为她相信革命。缘于对于大姨妈的一贯了解,“我”坚决认定大姨妈的相信是真诚的:“‘革命。’我顿了顿又说,‘她说她相信革命,这话是真的。’”但母亲对“我”的认定不以为然:“我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太不可捉摸了。她说她相信,你相信她相信,这完全就是‘子非鱼’嘛。信又怎么样,不信又怎么样,结果还不是一样,我能做的只是不恨她——而你同样也可以不相信我。
”叙述者“我”之所以坚信大姨妈的告密出卖乃是因为她对于革命的相信,其原因主要建立在对她的深入了解上:“在决定揭发母亲的那一刻,大姨妈相信革命是善的,正义的,伟大的。她还相信自己正在像那个年代的其他人一样革命、而革命必须有所牺牲。虽然她很快就含糊了,后悔了,但她的心里确乎涌现过一个天真纯洁的、光整的世界,思之令人落泪。”然而,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问题是,那个时候的大姨妈为什么会真诚地相信革命。要知道,作为一个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女性,大姨妈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革命为何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姨妈的相信革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时代思潮裹挟而去的一种结果。一个人对一个自己根本就不理解的事物的确信,说到底,只能被看作是一种盲信,一种无知的信。
唯其因为大姨妈的相信只是一种建立在无知前提下的盲信,所以才会呈现出“一种相信”很快就会被“另一种相信”取代的多变特征。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时间节点,亦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大姨妈对于气功的相信了。这个时候,也正是“我”因为家庭变故的原因,对于大姨妈的最早结识。由于父母聚集南京闹离婚的缘故,年幼的“我”只好被母亲委托给了实际上并无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姨妈来照顾。幼年时的“我”身体特别虚弱,不仅十岁了还尿床,而且“我还是那么黄,那么瘦,像根火柴棍一样,麻杆上顶着颗如斗大头。”一方面因为身体虚弱,另一方面也因为反应慢,那时在学校里,“我”曾经被同学们称为“傻球”。为了早日彻底改变“我”发育、成长不良的状况,心急如焚的大姨妈真正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地采取了各种手段。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就是要借助于气功大师的超能量有效改变“我”的不良状况。用大姨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刚才做的事情,正是运用师父传授的功法,从大自然里把好能量汇聚起来,再传到你的身上,把坏能量逼出去。这样一来,你的身板儿就会壮实起来了,脑袋也会变得比现在聪明,以后你就能考上大学,当上干部,学者,改革家……”究其根本,大姨妈之所以会着迷于气功,具体原因除了改变“我”的身体与智商状况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解决自己因输卵管疾患而长期不孕的问题。
具体来说,这一个时间节点的相关描写中,有以下三点不容忽视。其一,包括很多高级领导干部在内的社会公众已经全部陷入迷狂状态中的真切场景描写:“毫无疑问,在这种气场下,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被牢牢地摄住了,定住了,控制住了。而你又能想象上千个灵魂集体性地、以高度一致的频率共振,是怎样一个场面吗?整个儿礼堂仿佛被一团能量所充斥,它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百转千回滋滋冒烟儿地往人们肉里钻着。”非常明显,最后那一句“百转千回滋滋冒烟儿地往人们肉里钻着”又是典型不过的石一枫式话语。除了这些叙事话语之外,无知懵懂的叙述者“我”,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气功大师鼻子肉瘤上的一撮毛给揪了下来的如此一种具有突出反讽意味的故事情节设定,也散发着明显不过的石一枫气息。
其二,是大姨妈的事后反省。只不过当“我”得以了解到这一情形的时候,已经是在数年后的返京列车上了。在此处,石一枫很巧妙地穿插使用了信件叙事的方式。大姨妈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真切不过地表达了某种自我矛盾的惶惑心理:“杨麦,我有个念头,也只能对你一个人讲。你说师父这人究竟是善还是恶,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呢?以前没敢想过这事儿,而现在,事情和你相关,我就不能不想了。他如果像他自己说得那样大慈大悲,那么怎么可能记你一个小孩的仇?但我又托人问过师父的弟子,他们一口咬定,得罪过师父的人一定会遭报应,会出门被车撞死,会喝口凉水都把自己呛死。他们还说,我必须持续不断地参加带功报告会,而且还得发动你和你爸你妈也来,这样才能替你免灾,否则就等着收尸吧。但再一想,这不是打击报复吗?不是威胁恐吓吗?不求着他就不能得到安生,这样的做法,和我们厂的厂长,和我们县里欺行霸市的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对于一个厉害的恶人,我们只有怕,但却也不会信。我不愿这么想,但我还是忍不住这么想:我信师父是不是信错了?”一位思想能力匮乏的普通女性,竟然对自己曾经的精神信仰做出如此一种富有深度的强烈怀疑,究其根本原因,端在于对于“我”发自内心深处的关切。正因为严重牵连到了“我”的生命安危,所以大姨妈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过程之后,方才能够明确意识到那位气功大师言语的自我矛盾之处。自我矛盾一旦形成,其对气功热以及大姨妈精神信仰本身的一种突出解构作用,自然也就无可置疑了。
其三,无论如何不容忽略的一点,是这一部分关于那位拦车告状老太太的描写:“她头缠白布,身披标语,标语上的字样正是昨天所见过的,无非‘伸冤’‘做主’之类。”石一枫尽管只是顺带一笔,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太,之所以会执意不管不顾地拦车告状,肯定有着天大的冤屈。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的那些领导干部们,宁可拿出大把的时间来去捧一位气功大师的招摇撞骗,却根本就无视民间疾苦的存在。也因此,虽然只是作家的顺带一笔,但却强烈地呼应了石一枫“既问苍生”的深刻思想题旨。
【梗概】心灵外史/石一枫
少年杨麦父母离异,家人将他托付了给一个被称作“大姨妈”的女人。在代为照料杨麦的同时,“大姨妈”也向他展开了一个离奇古怪的世界:气功、传销、家庭教会……深陷于渴望相信什么但却无可相信的困境之中,“大姨妈”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得异于常人,也越来越无法适应令她饱受创痛的现实世界,最终走向了自我放逐。而杨麦在长大成人之后虽然选择了主流的功利主义生活方式,但却无法真正解决埋藏在深处的心理危机,并且得上了焦虑症。两人分开多年以后,当杨麦正为内外交困的生活而焦头烂额时,突然得知了“大姨妈”的下落。感念着“大姨妈”留给自己童年时代的温暖记忆,杨麦决定去寻找“大姨妈”。他想要报答“大姨妈”,也希望能将“大姨妈”从盲信状态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从而完成对自己的精神治愈。然而事与愿违,等待他的不仅是一段荒唐的冒险经历、一系列社会怪现状,更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现居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2005年起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原创作品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等,译作有《猜火车》等。2017年第3期《收获》刊载石一枫长篇《心灵外史》。
2017-3《收获》
2017-2《收获》
2017-1《收获》
2016全年8本《收获》,特惠
2017《收获》长篇专号(春卷)
《收获》微信公号
微信号 : harvest1957
地址:上海巨鹿路67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