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敦西北部尤斯顿火车站外面,一个寒冷秋天的早晨,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站在室外的楼梯顶上,环顾四周的警察,并极力掩饰自己的行为,以便不被人关注。这比听起来更难,不仅仅是因为他超过190厘米的身高,还因为罗伯茨正从口袋里取出塑料包装的包裹,然后撕开它,滑出里面看起来像个大棉签的细长管子。再次检查发现没人注意到他后,他沿着楼梯扶手拖着大棉签跑下楼梯,然后再将细管揣进口袋,最后慢慢离开。
走过一条街道后,罗伯茨偏离了繁忙的尤斯顿路,沿着街道前往自己位于伦敦大学学院的实验室走去。他没有做任何邪恶的事情,可是因为到处都是闭路电视,伦敦也正处于防范恐怖袭击的高度警惕下,他担心惹出不必要的麻烦。直到到达圣乔治花园的中间那片绿树环绕的绿色空间,罗伯茨才全身放松下来。
罗伯茨正在做的事情已经被他及其支持者做过几百次了,他们的目标是重拾40多年前被抛弃的研究实践。他们采集环境样本,希望能找到充满细菌的最肮脏之地,以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今天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抗生素耐药性。所谓的抗生素耐药性是指,细菌抵御我们用来杀死它们的化合物的能力。自从抗生素在20世纪40年代被发现以来,几乎所有抗生素杀死细菌的有效性都在削弱。每年,全世界至少有70万人死于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细菌感染。如果我们不能减缓耐药性蔓延或找到新药物,到2050年,这个数字很可能会激增到1000万人。常规手术和轻伤都可能会重新危及人类的生命。

然而,为了避免这场灾难而做出必要的改变似乎渐渐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畴。我们继续大量使用抗生素,甚至将大量抗生素喂给农场饲养的动物。要想阻止细菌耐药性可能需要10年时间研发,并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而制药公司对此似乎缺乏研发意愿。
这就是来自英国中部43岁的微生物学家罗伯茨为何要加入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的原因。回到他的实验室,他掏出许多走路时收集的试管,并给它们贴上标签,包括鞋子、浴室门把手、树、长凳以及楼梯扶手等。他伸手去拿出大堆的培养皿,每个盘子里都盛着清澈的黄色培养基。他打开盘子,然后将收集到的样本放入其中,并且封闭然后标记它们,最后放在旁边孵育。
罗伯茨说:“自然界的微生物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化学成分,我们对此还没有充分调查过,而且我们不必前往海洋底部或其他极端环境中就可找到它们。”罗伯茨要求人们在细菌可能繁殖的地方给他发送样本,越不卫生的地方越好。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所有的抗生素都来自自然资源。这就是1928年抗生素时代开始时的场景,弗莱明爵士据说保持其伦敦实验室的窗户开着,几周后发现霉菌斑点,里面分泌的化学物质可以杀死菌葡萄球菌。那种化学物质变成了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随后氯霉素也在委内瑞拉的堆肥中被发现,金霉素则是在密苏里大学干草试验田中的细菌排泄物中发现的。
这些都是抗生素时代的基础药物,使感染的历史威胁从死刑变成了“小麻烦”。它们杀死致病细菌的能力并非偶然产生的,最早的抗生素是从化学武器中提炼出来的。在这些化学武器中,细菌在与其他微生物争夺生存空间和养分的过程中不断进化。制造这些武器的生物似乎在潮湿和肮脏的地方更易茁壮成长。
这些早期抗生素非常成功,利润如此丰厚,以至于制造商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更多的抗生素。以科研为基础的全球性医药保健公司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曾在1951年年度报告中,要求股东们舀一茶匙泥土,稍显潮湿但不太湿润,不要大块石头,然后寄到公司总部。Eli
Lilly公司曾与基督教和传教士联盟成员达成协议:前往发展中国家的部长们需要携带试管。辉瑞公司招募了探险家、飞行员以及外国记者,以向他们发送土壤样品。

这些搜索发现的抗生素今天依然至关重要,包括在菲律宾发现的红霉素、在婆罗洲丛林中发现的万古霉素、从圣经中诺亚方舟的安息之地——阿勒山山麓发现的达托霉素等。但是,从这些土壤中识别和提炼出有用的化合物异常缓慢。微生物学家塞尔曼·威克斯曼(Selman
Waksman)从10000多个样本中发现链霉素,辉瑞在13万个样本中找到土霉素(早期的四环素)。
土壤中盛产微生物,小小茶匙中可以包含数以百万计的微生物,但只有小部分细菌可能会被证明产生有用的抗生素化合物。而在那个子集中,只有极小的部分能在实验室中成长,远离能够促使它们进化的复杂自然环境。研究人员原以为他们正在翱翔在全新的治疗和利润领域,但却发现自己困在发射架上,一遍遍地发现相同的抗生素化合物。土霉素的开发商表示,在1951年之前找到它时,他们重新发现链霉素“至少100次”。
到20世纪60年代末,药物公司放弃了在土壤中寻找抗生素的做法,转而在实验室里人工合成化合物。这并非是巧合,而是因为找到新药的速度大幅下降。从1940年到1970年间,有12种不同种类的抗生素通过临床试验进入美国市场。可是自1970年以来,只有少数药物被发现。这意味着自那时以来,几乎所有的新抗生素被发现都是现有细菌发生突变所致。
由于没有新的药物来抑制细菌的扩散,致病细菌也随之崛起。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突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它可以催生出只需要数天就能让人死亡的急性肺炎。本世纪初,VRE的传播造成严重的医院感染,它对万古霉素产生抗药性。NDM病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有很强的抗性,它在2000年左右感染了印度和世界各地大量旅客。让万古霉素束手无策的MCR于2015年在中国确认,此后传播到世界30多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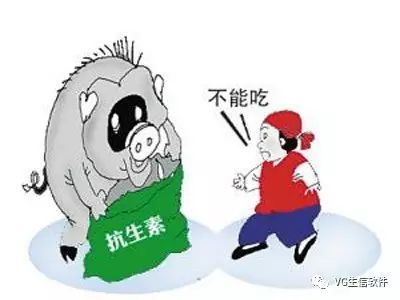
到去年为止,多种药物耐药性细菌的上升趋势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并在联合国大会上举行了罕见的特别首脑会议。此次会议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致力于打击滥用抗生素行为,并支持寻找新药的研究。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耐药性细菌是对人类健康的根本性和长期性威胁。
罗伯茨正在实验室里翻阅厚厚的活页夹,看看他收集的样本是从哪里来的。其中大部分都不是他自己收集的,而是由他创建的网络提供的,通过众包活动和在Facebook上重现20世纪50年代药品公司的实践,旨在从更广的地理范围收集样品。罗伯茨于2002年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十多年来始终致力于研究细菌获得抗生素耐药性的主要途径,即通过DNA交换环节来回传递基因。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两位研究人员描述了这种传染病的抗性,志贺氏杆菌对未接受过治疗的药物产生了耐药性。从那以后,微生物噩梦就开始了。可传递的耐药性使细菌防御抗生素的突变不仅仅通过遗传传播,即通过母细胞传给子细胞,而且也能通过交换质粒(DNA的小循环)在不相关的细菌中传播。质粒可以同时运输多个基因,因此它们允许抵抗多种药物的抗性积累起来,最终帮助细菌赢得胜利。
罗伯茨对这种现象很着迷。但是经过多年的学习,他决定转移注意力。他说:“我开始认为,我们可以永远找到新的抗性基因,因为他们总是在进化。可是为什么要寻找新的基因而不寻找新的药物呢?”他决定从几十年前药物化学开始的地方为起点进行研究。2015年2月份,罗伯茨发起名为“Swab
and
Send”的活动。只需要5英镑,参与者就可以得到样品试管、信封,并解释罗伯茨想要他们寻找什么:细菌可能竞争营养和繁殖空间的环境。他要求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越不卫生的地方越好。
在第一次抗生素搜索中,罗伯茨没有要求他的样本收集员们专注于土壤。相反,他希望他们在前人可能忽略的地方进行搜查。他说:“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微生物丰富的环境。每个地方都是一个生态位,细菌会在那里独立进化和适应。这些地方可能演变成生物大战的地方,而海洋环境、泥泞的环境或受污染的池塘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战场,很可能到处都有不同到的化学物质。”
“Swab
and
Send”运动激起人们的积极性:在2个月内,罗伯茨收到了超过1000英镑以及数百份样品。小额支票继续以邮寄的方式到达,小学邀请罗伯茨去做演讲时,他让孩子们将棉签带回家。他带了样品试管去参加聚会和编辑部。他甚至对国会大厦的桌子进行了采样。罗伯茨读道“曼彻斯特足球场第三层的卫生间”、“被遗忘在冰箱里发霉的莴苣”等。

我们已经坐在他的实验室里了,罗伯茨正在打开培养皿,细菌已经在一夜之间孵出来了,他将它们转移到96个培养板上。他在重复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们的化学过程,在实验室里研究细菌,看看它们能做什么。
第一步是把棉签放在培养基中,并且让它孵化。第二步是把所有生长在凝胶上的细菌分开,一个棉签可能会包含许多种细菌,需要把它们分离到新的培养板上,让它们不互相干扰地繁殖。在第三步中,罗伯茨将每个样本放入含有其他微生物的培养基中,看它们是否会互相竞争。他正在寻找一个“抑制区”,即围绕着细菌的透明圈,预示着它产生一种能杀死细菌的化合物。清除这种障碍的细菌会面临更高的挑战:大肠杆菌对15种不同的药物产生耐药性。如果细菌在这种挑战中幸存下来,其产生的化合物被认为值得进一步审查。
罗伯茨使用20世纪40年代不存在的分析工具,来寻找幸存者是否真的属于新事物。自从发起“Swab
and
Send”运动以来,罗伯茨和他的研究生们在开始了一系列的培养过程,煞费苦心地收集了数千个细菌样本。其中,数以百计的细菌会分泌出至少能杀死一种试验细菌的分泌化合物,少数甚至可杀死潜在的真菌,因为抗真菌药物的供应比抗生素更加短缺。迄今为止,罗伯茨已经发现了18种非常有前途的细菌,它们可杀死多重耐药性的大肠杆菌。
根据细菌进化的速度判断,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这令罗伯茨感到沮丧。3年前,他的女儿刚刚6岁。那时,她正在乡下玩,并在腿上挠出划痕。此后,划痕变成脓疱,清洗后开始蔓延到其全身皮肤上。医生尝试了三种不同的抗生素,但都没有效果。来到伦敦大学学院医院后12个小时,她接受了手术。虽然女儿已经康复,但她的胫骨上有一处凹陷处,那时被切除感染伤口时留下的。但对罗伯茨来说,这事件让我们了解到抗生素耐药性的不可预测性。
罗伯茨说:“如果卫生保健系统无法治愈她的感染,她可能会失去腿。在没有抗生素的支持下,你所拥有的医疗保健系统会崩溃吗?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罗伯茨的研究进展缓慢,同时也恰恰说明了寻找新抗生素的艰巨性。

AstraZeneca公司负责临床抗生素开发的前高管、致力于研发抗真菌药物的公司F2G首席医疗官约翰·莱克斯(John
Rex)说:“最难的事情不是找到能杀死细菌的东西,蒸汽、火、漂白剂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最大的挑战是找到杀死细菌的东西,而且它不会伤害服用它们的人。你在谈论的是可以进入你的口腔、肠道、血液的化学物质,它不能发生任何变化,但却能消除感染,杀死细菌,同时对你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