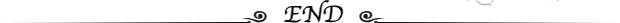大卫,阿佩里斯画康巴斯白,1814
[法]让-吕克·南希 & [意]费德里科·费拉里 /文
○●○●
lightwhite /
译
拜德雅·卡戎文丛主编
泼先生执行编辑
亚历山大让伟大的画家阿佩里斯来画他的宠姬康巴斯白,阿佩里斯是亚历山大的宫廷画师,并且是唯一一个被允许为他画肖像的人。根据普林尼(Pliny)的说法,亚历山大想要康巴斯白赤身裸体,以“欣赏她的美”(ob admirationem formae)。阿佩里斯在工作的时候爱上了她。国王注意到了,并把他的宠姬献给了画家。这个场景被人画了许多次,但大卫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呈现了它。和其他作品一样,在一个分组场景的位置上,大卫以一个宽广的尺度来安排场景,这样,三个人物就可以被清楚地看到。两个男人,一个站在另一个身后,都朝向了女人,女人和他们隔着一定的距离。她的裸体暴露在他们面前,并且出于羞涩,虽然这样的羞涩没有什么胆怯,她做出了一个保留的暧昧姿态。但对那些熟知故事的人而言,她的尴尬或她的撒娇既可以在讨好主人的同时掩饰自己的欺骗,也可以在激起情人欲望的同时向他确保自己掌控着游戏。所以,康巴斯白的裸体,作为美的真理被暴露出来,是欲望之纠葛的关键和所在:亚历山大的欲望和阿佩里斯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和挫败。亚历山大渴望图像——他渴望支配,渴望对这个已被占有的身体的至高的居有——虽然这个身体已从他那里被偷走。阿佩里斯渴望身体——他同样已经占有了身体,即便只是用眼睛来把捉——但他只能拥有图像(以及执行图像的时间)。
沿着康巴斯白的羞涩的姿态,画家所小心翼翼地选择的装饰告诉了我们一切有关裸体之表面不一的东西。这样的装饰只体现为一张床,白色的床单被黑色的帷帐衬托。它不只是装饰,不只是呈现的一个框架,它也是画家的床(仿佛一个人要相信阿佩里斯就睡在他的画室里……事实上当国王不在那里的时候,他必定这么做)。羞涩本身是含糊的,因为如果康巴斯白看似做出了一个用头发遮掩自己的暧昧的姿态,那么,她就什么也没遮住,既没有遮住乳房,也没有遮住肚子。尤其是肚子,相比于她身体的其他部位,肚子是向画家的凝视敞开最多的。这肚子被床抬起,和两个男人的肚子处于同一高度:两个男人按其目光的轴线被排成一列,画面也沿着这条目光的轴线展开。
但这只是刚刚开始。和在画布上画出了康巴斯白半身像的许多前人不同,大卫给我们的只是一幅草图的起始的线条,从大腿一直到尚未画出的腹部。画家的影子落在这些模糊的线条上,既隐藏了它们,又突显了它们。在别的地方,画布是空的。(我们知道大卫没有完成这幅画:他那时已经完成了阿佩里斯面前的画吗?……)(画布)背景的颜色在身体的某些部位重复。空白的画布如同一个裸女的绘画,虽然它是裸体的一种表达而不是一种再现,但它把三重价值赋予了裸体:外露的价值,身体被延展,被拉紧,被呈奉于画笔;可操作和可锻造的价值,这是指画家想要给予他自己的身体会来到画布上;间隔的价值,只要画布充当了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的一面屏幕。(屏幕或注意力的转移:一切被设置起来,就好像有两条男人目光的轴线,让他们产生了斜视:第一条是对女人的凝视的轴线,第二条是对女人肖像的凝视的轴线。另外,画布被呈现为一个舞台;一条成对的黑色帷幕在上方升起。)
这不是全部。在这里,裸体扮演了一个甚至更受限制的角色。初看上去,亚历山大的赤裸的身体强加了自身,高贵的君王服饰的松散的褶皱和将军的头盔突显了它。主人将自己赤裸地展现出来,面对着他赤裸的宠姬:这样的展示宣告了他的欲望,这是占有的暗示,并突显了他们的对称,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对抗。亚历山大的身体,作为男性版本的优雅的、雕塑一般的形式,没有把任何东西让予康巴斯白的身体。在这个点上,观者的凝视发现自身被绘画的两端所吸引:被引向一个性别或另一个性别。历史(或传说?在此,这些并不重要)认为亚历山大是双性的。我们知道,裸像对大卫而言是如何地重要,因为他甚至为它写了一个手稿;这幅画反过来允许一种用双性人或同性恋的观念进行的分析。亚历山大的手触摸画家肩膀的细节也允许这样的分析。但一个人只需分析绘画:裸体是明显地成对的,不管是以异性恋的还是以同性恋的形式。但这不是内在于一般的裸体吗?存在着孤立的裸体吗?所有的裸体不都面对着它自身或另一个裸体吗?裸体不首先是一种“面对”吗?虽然它从不拥有一种“面对面”(vis-à-vis),因为裸像并不观看。它被看,也看着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画布是空白的,光秃的:那是绘画在面对自身——如同一种被延展开来的巨大的欲望。画布具有一个勃起:看看离我们最近的画框高处的菲勒斯顶点。与之对应的是邻近的床的布置,上方有一个向外逐渐展开的顶柱。
裸体不是一个存在。它甚至不是一种性质。它总是一种关系,总是多个同时的关系:关乎他人,关乎自身,关乎一个图像,关乎一个图像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