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介绍了自然文学作家约翰·缪尔、伊莎贝拉·伯德和约翰·巴勒斯的生活和作品,探讨了他们对自然、自由和生活态度的追求,以及他们对自然文学发展的贡献。文章通过描述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引发读者对自然和生活的思考。
文章介绍了约翰·缪尔、伊莎贝拉·伯德和约翰·巴勒斯三位自然文学作家的生平经历、作品内容和思想,包括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态度。
文章通过介绍三位作家的生活和作品,探讨了自然与自由的主题,包括人们对自然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如何在自然中找到自我和生活的意义。
文章强调了这些自然文学作家对自然文学发展的贡献,包括他们的作品对自然环境的描述、对自然美学的探索,以及对自然文学普及和推广的作用。
在这个时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仿佛了了。如果是为了恢复能量,在家躺平,不是比去户外旅行更高效吗?为何还有许多人喜欢去大自然,去荒野呢?
与梭罗齐名的自然文学作家约翰·缪尔曾言:
“原本只是出去散一会儿步,最后却决定在外面等到日落,因为我发现往外走,其实也是往内心去”。
这个夏日,群山在呼唤,而我必将前往!
中信出版近期推出了“
如花在野”系列的自然文学三部曲
,希望与大家能一起走入荒野,寻回真我。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让我们一起
与约翰·缪尔共度山间夏日
,无论是那些未曾涉足的远方山川,还是那些已经消失在记忆中的童年沉迷在山野的趣事,都将被重新点燃,激发我们探索自然的渴望和勇气。
让我们与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
女性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
,跨上马背,奔向落基山脉,行于荒野,也沉醉于荒野。
让我们与
博物学家、散文家约翰·巴勒斯在山间
、在田野,去看毛茸茸的花栗鼠、狐狸、野兔和小浣熊的趣味生活。
自然文学作家约翰·缪尔在1888年7月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只有独自一人,不带行李,默默地走下去,才能真正走进荒野的深处。其他一切旅行都不过是灰尘、旅馆、行李和闲聊。”
人对自然的憧憬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能本质上,是那份
长在自然里的自由
吧,不必必须“有用”,只要
舒展地活着
即可。
不被人看到,也轰轰烈烈地盛开,不被人赞美,也依然是碧天云卷。
1838年,约翰·缪尔出生于苏格兰,1849年,缪尔随家人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威斯康星州波蒂奇附近的一个农场生活,随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读,直到1863年。

离开大学后,缪尔从事机械发明,但在1867年,当一场工业事故几乎让他失去一只眼睛时,他放弃了这项“社畜”般的事业,全身心的开始了
自然之旅
。
他
离开社会,选择到“荒野”度过余生。
后来的他,成了
博物学家、作家和冰川学家
,也是继梭罗之后重要的自然文学作家,被称为
“山之王国的约翰”“美国荒野的守护神”和“美国国家公园之父”。
1903 年,他陪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美国西部的约塞米蒂进行了数天荒野之旅。
罗斯福称 :“在世上所有人中,约翰·缪尔是最值得与之一起去约塞米蒂的人。”
受缪尔影响,罗斯福在任期内签署建立了
5个国家公园、18 个国家纪念保护区、数十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及上百处国家森林。
约塞米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里有无数人向往的内华达山脉,默塞德河与图奥勒米河蜿蜒其中,瀑布、溪流、花田、森林组成了美妙的山中盛夏。如今,约塞米蒂美国国家公园,也是全球徒步爱好者必打卡的美景胜地之一。

时间回到1869 年,31岁的约翰·缪尔也曾与我们一样拥有夏日到山间度过的美好愿望:
“而我想趁这时候到山区看看,奈何囊中羞涩,不知该如何维持温饱。漫游者们总是在为生计发愁,我也正为粮食问题困扰不已,甚至想试着学习野生动物的谋生手段,四处收集种子和浆果之类的吃食,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不带金钱也不带行囊,快活地漫步、攀登。”
这时,他收到了养羊人德莱尼的请求,说需要缪尔同牧羊人一起去内华达山脉牧羊,同行的牧羊人会负责所有放牧工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欣赏风景,考察植物、岩石、溪流等。
接下这份差事的缪尔,看着2050只羊,“忍不住担心自己会把它们带上一条不归路”。

他将所有故事记录到了
《夏日走过山间》
这本书中。
作为一名博物学家,他还在书中记录了
大量植物相关的发现
,如白花仙灯百合、耧斗菜、白百合、羽扇豆和熊果的浆果等。细细品味之下,这种对植物的青睐,与中国自《诗经》《楚辞》而起的
“草木情怀”
或许是很好的一种对照。

关于自然,缪尔有两句知名的名言:
“群山在呼唤,我必将前往。”
“成千上万疲惫不堪、神经紧张、过度文明的人开始发现,上山就是回家,这种野性是必要的。”
他将自己的
荒野之旅化作了诗意的表达
,这种浪漫也将驱使着我们走入荒野。
从1869年6月3日的盛夏到9月22日的凉秋,
100多篇生动的自然日记
收录在《夏日走过山间》,尽显山间夏日的美好。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我渴望疾劲的风
急欲找一个爱山的人说说话
“我渴望疾劲的风、重叠的山丘、巨大的松林、夜间野兽的吼叫、诗意般的自由,以及无与伦比的快乐的山旅生活。”
说出这句话的女人,是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探险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首位女性成员”伊莎贝拉·伯德
。
在女性以“完美主妇”为理想的时代,在1873年,她却选择像男性一样
跨上马背
,挑战“北美脊梁”落基山脉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朗斯峰。
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她
行于荒野,也沉醉于荒野。

1831年,伊莎贝拉·伯德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牧师,父母都非常支持她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她非常喜欢和父亲一起学习骑马,逃离那个时时刻刻被要求做“淑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文明社会的规训。
换言之,
她像男性一样的跨骑在马背上,就是一生逃离到荒野的开始。
维多利亚时代压抑的生活规范,使她神经衰弱,身体每况愈下。23岁时,一位医生建议她去长途旅行以疗愈疾病,从此她开启了无数次冒险之旅,足迹遍布北美、亚洲和北非等地。
英国BBC拍摄的纪录片《开拓者:落基山公路之旅》中曾谈道:“实际上,在
伊莎贝拉·伯德
的一生中,她步行和旅行的距离相当于绕地球三圈。”
1873
年秋天,她来到了北美落基山地区。
当时,她停留得最久的科罗拉多,还是不属于美国的未开发地区,当地的法律还在制订中,铁路也还在修建中,这块土地上居住的是生活简陋的拓荒者,他们才刚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得这块土地。

伊莎贝拉·伯德在落基山体验到的极致之地,也就是神圣的埃斯蒂斯公园,如今已是个观光客随时可以方便进出的游览区,当时却是美丽绝伦、与世隔绝的处女地。
她迫不及待想对世人描述这片土地。
她说:
“无论如何,我都要抵达那片深蓝的地方,甚至站到那有闪亮白雪的朗斯峰之上。”
而那座山峰的海拔超过4000米。
她将此次落基山脉之旅的经历都记录在了
《我渴望疾劲的风》
一书中,全书由伊莎贝拉·伯德写给挚爱妹妹的
17封信组成
,这种
书信体的叙述方式
既亲切又富有感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
对旅行艰辛的幽默吐槽、对河流与山川美景的由衷赞叹、对山中饥寒交迫生活的真实记录,以及对荒野冒险的深情回眸,都随着轻松愉悦的书信一一展开。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在路上,不仅有诗意,还有痛苦。
一方面,是山间的美景,令人惊叹。
“我刚刚不期然地进入了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不过它的每一处都超乎我的梦想。”
另一方面,还有一连串的关于旅程艰辛的“吐槽”。
“到这里为止,路途十分孤寂,除了右边的巨山阻拦外,到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我们像极了在海中航行,只是少了一方罗盘罢了。……几只秃鹫在上空盘旋,旋即又降下。动物的尸骨处处可见。”
当然,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她遇到的那些生活在野性世界的自由人。

离开落基山脉,一切成为了过去。
70岁时,她最后一次踏上旅程,在摩洛哥完成了长达1000英里的骑程。
尽管她马不停蹄的一生充满穷困与危险,她却于74岁时在爱丁堡家中的床上安详辞世。
伊莎贝拉·伯德的一生,无疑是对“
女性力量与自由”精神
的最佳诠释。她用自己的行动,有力地打破了社会对女性的固有偏见,同时在旅途中展现出了女性独有的坚韧与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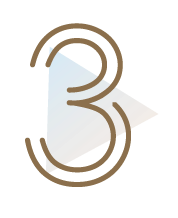
与毛茸茸的动物共度山间冬日
约翰·巴勒斯
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杰出的
自然文学作家
,他被称为“一个带着双筒望远镜的诗人”、“走向大自然的向导”。
约翰·巴勒斯,于183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他的一生与梭罗极为相似,都是
沉浸于自然的怀抱。
他当过教师,做过农场主,还在华盛顿特区的财政部做过9年的职员。多年后,他搬到了纽约州哈德逊河谷的一个农场,而后辗转各处生活,不变的是他的笔端从此没有离开过对自然的关注。

由于他对鸟类倾注了许多心血,著作有《夜莺》《鸟与诗人》《蝗虫与野蜜》等等,他也被称为
“鸟之王国的约翰”
,而我们上文提到过的约翰·缪尔则被称为
“山之王国的约翰”。
在
《雪夜,狐狸毛茸茸》
一书中,约翰·巴勒斯记录了他在山间生活时,
与动物之间发生的趣事
,文字读来十分治愈,兼具
博物知识与文学诗意。
他的文字,让我们看到可爱的动物们的生活,也看到自己。
它们忙忙碌碌的在田野奔波,而我们也在大城市中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