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一提起父亲,我心中便涌动一种复杂的情愫,唤起一种酸甜苦辣的记忆。
在我眼中,父亲那双浑浊的眼睛,犹如蓄满沧桑的老井;而他那暴跳的青筋,又像导火索一样,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我心中常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假如有一天父亲突然撒手而去了,该怎样为他作悼词才算公允?!
打我记事起,父亲便是生产队长。每天清晨,当我还沉浸在睡梦中的时候,父亲便拿起铁皮卷成的话筒高喊:“出工啦!”有时,我躺在床上,听见他在给男女老幼分派不同的活计,偶尔也听见他暴跳如雷地骂娘,说这个“偷懒”,那个“混工分”。
我当时害怕得很,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何那样急躁,他是那种“大跃进”年代培养起来的农村基层干部,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奉为行动指南,恨不得每个人都像他那样出满勤,出满力。

后来我才发现,对每个人都要求很高,对任何事情都要求尽善尽美,这是我们父子共同的禀性,急躁情绪,好心好意地得罪许多人。
母亲娘家号称“李家大塆”,其实由于不断拆迁,只不过三五户人家,于是便和我们“赵家大塆”合并,组成一个生产队。母亲有一个远房堂叔叫李马林,中年丧妻,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作伴,在旧社会沾染了一些坏毛病。

父亲当了队长之后,李马林总是百般讨好,常约父亲到他那间草屋里对饮。父亲看他没有多少家庭牵累,断不至于将公家的东西往家里拿,便委托他为仓库保管员,掌管集体财产和粮仓的“印斗”。
一种木盒状,底下凿有如筛子一样的网眼,石灰粉落下去,粮堆上便印有一个“公”字。
那年月,生产队也“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乡民们肚里的粮食越来越少,而野菜,胡萝卜却越来越多。不到半月,许多家的“口粮”(按人口定指标的粮食)便告罄,然后东家借一升,外村借一斗,互相接济。我们一家八口,一日三餐,父亲是不管的,生计全靠母亲一人操持。
因此,母亲常抱怨父亲把命都交给集体了,每天起早睡晚,累得半死不活,做梦都在安排生产,只从家里往外拿,不见他从“公家”往家里拿一根棍棒,菜园子更是不闻不问。我们家六个小孩,呈“梯队”状态,正是长身体的“半崽”,吃起饭来,如风卷残云,狼吞虎咽。每到半月,母亲便得厚着脸皮,拿着升子和盆子,找那些没有小孩拖累的家庭“周济”粮食。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躺在床上忍受着饿肚咕咕咕的叫唤,像煎烙饼一样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难以入眠。突然,我听到我家窗户门被拍响了两下,有人在轻唤父亲的名字。很快就听见父亲趿着鞋,“拍拍拍”地去开门。
“嘿!我给你们家搞了两袋粮食”。我听出这是保管员李马林鬼鬼祟祟的声音。
“你怎么能这样?全村人都在挨饿,我这一队之长能吃独食?快给我背回去!”父亲感到事情的突然,显得有些慌乱。
“唉!你们一家八口,成了全村最大的缺粮户,你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留下吧!我走了!”
没等父亲开口,李马林已消逝在夜色里。父亲不敢声张,怕闹得左邻右舍都知道反而说不清,于是便将粮食移到了屋里,想等天亮再说。

第二天,李马林“恶人先告状”,上告大队,说父亲“私分粮食”,“贪赃枉法,该当何罪?”于是,父亲被革职反省,退回粮食,全大队批判,李马林接替了父亲的位置。
自从父亲下台之后,许多看着脚尖走路的势利小人,便在父亲背后指指戳戳,冷嘲热讽,甚至咬牙切齿。也有人客观公正地评价父亲:“虽说脾气不好,但呕心沥血地为了集体,大公无私,心肠却是大大的好!”从此,父亲不再是一只令人敬畏的老虎,而变成了一只困兽。龙困沙滩,虎落平阳,即便有威风也无处施展,不得不屏声敛息,老实做人。
父亲开始学会隐忍。原先高高大大的身躯倒下来可以压死人,这时变得只剩下空架子,一个高门大嗓,声若洪钟的人,变得少言寡语。一夜之间,父亲苍老了许多。
父亲当队长时,对李马林常常是大呼小叫,如有不满,便如同训孙子一般,当他们的位置颠倒过来之后,李马林便对父亲报复性地百般刁难。
那时,每到“双抢”季节(即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生产队时兴集体做饭。用一个大蒸笼将全队男女老幼的饭碗装进去,每一只碗都装有米和水,蒸熟之后,各家各户领回自己的饭碗,不用各家开火,为的是节省时间。

有一天,正值江南的“梅雨”季节,瓢泼大雨下得人们睁不开眼,天地之间,雾气沉沉。父亲从秧田里回来,褴褛的衣衫在风雨中飘动,浑身上下湿成一片,冻得嘴唇发乌,身子瑟瑟发抖。于是,他在开饭时,本能地从蒸饭的棚子上扯下一小块塑料布,下午下地时围在身上,用来遮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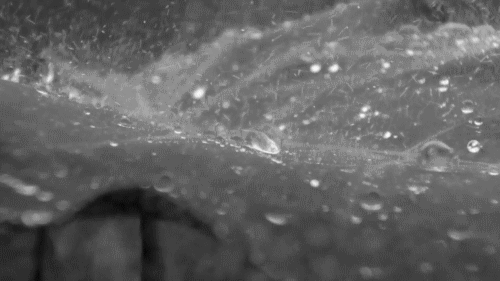
不料,这件事被李马林知道了。他当着众人的面,小题大做,不点名地挖苦父亲。父亲像被人当众剥光了衣服一样,受到了极大的羞辱,感到无地自容的痛楚。很多人都担心这头暴烈的“虎”会被激怒,可是他终于咬着牙忍下了。对于一个有着“爆竹”脾气的人来说,这种隐忍,如同把心嚼烂,又如同打落牙齿,连同血水往肚子里咽。
父亲是一个宁肯苦死自己,也不肯吐出一个“苦”字来的人。他心里苦极了,在我们面前却依然显示出高高大大,宁折不弯的强悍形象。
 我为父亲拍摄的照片
我为父亲拍摄的照片
母亲深深地理解父亲的苦衷,便向我们诉说父亲历经的磨难,以唤起我们的理解与同情。父亲小时候给地主家当佣人,听的是没完没了的使唤,吃的是残粥剩饭,受尽了地主婆的欺侮。
解放后,刚刚成家便相继死了父亲和母亲,留下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三岁。他既要哺养家小,又要承担起“长兄长嫂当爹娘”的使命。
他常常穿着草鞋,沿着羊肠小道,起早摸黑,赶到往北几十里开外的山上,挑着一百五十多斤重的柴禾回来,第二天又赶早,往南负重行进三十余里,到县城卖掉,换回几块钱,为家小、弟弟们扯回一件衣料,或者挑一担胡萝卜回来,供全家充饥。

父亲的两个弟弟渐渐长大了,他送他们参军,激励他们在部队里努力进步,入了党。我们家门前“光荣军属”的牌匾一挂就是好几年,给破烂不堪的家增色不少。在此期间,父亲又在家乡为两个弟弟的婚姻大事跑烂了几双布鞋。

那时,我已经十多岁了,已是一个中学生,每次叔叔的亲家需要走动,父亲便派遣我去。我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七十年代末期,时兴选举,父亲又一次当上了生产队长。那时,我已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父亲依然像以往那样严肃认真,那样让人难以接受,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有一次,全队精壮劳力从稻田里往禾场上挑稻子,我也侧身其间。父亲看见一批人懒懒散散,便冲着我发火:你还是什么团小组长?其实,我心里清楚,父亲在指东骂西,无非是敦促大伙儿鼓足干劲,大干快干,但我心中还是觉得有种莫名其妙的委屈。
他重新当了队长之后,依然是一副急性子,一副火爆脾气。有一回,生产队养鸭子,我被推举为掌管“千军万马”的“鸭倌”,师傅是从我姐姐的婆家请来的亲戚。

一天傍晚,我们正在一片“嘎嘎”声中给鸭子喂饲料,生产队抢收稻子的队伍正从我们身旁经过,父亲看见别人耍滑头,偷懒,又亮开嗓子骂开了。洪亮的声音直往我和师傅的耳朵里灌,师傅显得有些紧张,我的身心也一阵紧缩。我为父亲在姐姐的亲戚面前,不顾自己形象大发雷霆而感到脸红,可是我又没法劝阻他。因为他毕竟是出于公心啊!难道战场上的将军以正军风而甩帽子、骂娘,还应当受到指责吗?

大学毕业后,我坚定地走上了西藏高原,成为“西天最后一片净土”的主人。临行前,父亲对我说:“听说去西藏的大学生,一去就是八年?”当时我也搞不清,一想到去一个完全陌生的荒僻地方,征途漫漫,岁月悠长,不仅不能尽到一个长子的孝心,而且连见父母一面都很难,我的鼻子一酸,情不自禁地泫然泪流。
儿行千里,岂止是母担忧啊!父亲似乎更明白事理,更具有深沉的爱,他安慰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再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相信高原的风沙会把你锻炼成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意志力坚强的汉子。”父亲的幽默,使我的心平衡了许多。
进藏头一年,我没有回去过年,父亲在吃年饭时,进进出出,坐卧不安,他久久地眺望西南方向,然后坐在门前的石碾上自言自语:“台湾同胞都回来探亲了,我那儿子却没有回来。”说着说着,老泪纵横,潸然泪下……

这些年,父亲已不再当那劳神费心、吃亏不讨好的队长,而守着自家的责任田辛勤耕耘。每次听我说:“应该离开土地去经商,直接进入商品流通渠道,与钱打交道才能致富”就十分反感,大光其火,大骂:“农民不种地,谁提供商品粮食给你们吃?”
父亲近年来越老脾气越坏,酒瘾也大增,饮酒经常量也没准。每次一边呷着酒,一边慢悠悠地往嘴里送油炸花生、油炸黄豆之类,几颗稀疏的大牙咬得嘣嘣作响,一副怡然自得的沉醉状态。酒过半斤之后,便开始云里雾里,晕晕乎乎起来,自得其乐的同时,免不了意气如虹,产生夸大的自信,显示出英雄气概,说些吹牛皮的大话,闹出许多笑话,让人啼笑皆非。
有一次,父亲喝了几两“烧酒”之后,去卖粮食,验质的人随口说了句:“乡亲们,要把好粮食卖给国家,湿了不行,杂质多也不行!”其实那人只不过是泛泛而谈,酒后的父亲却感到是别人对自己的不信任,于是,喷着酒气,涨红着脸发火:“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家有好几口吃国家粮,交了优质商品粮,我家也有人吃得上,我凭什么不交好粮,狗眼看人低!”

还有一次,也是在饮酒之后,别人在说共产党员的坏话,父亲挺身而出,说:“我们家有三个党员,可以成立一个支部,我最容不得别人说党的坏话。”
当别人夸自己的孩子时,父亲也不甘落后:“我那儿子虽说在西藏,偏远了些,可他来来去去都是坐大型飞机,你们谁坐过?”在我看来本是很寒酸的事情,经父亲一说,仿佛是一件荣宗耀祖值得炫耀的事,让我心中涌起酸甜苦辣的复杂情味。
这几年,父亲不论是到我姐姐家走动,还是翘首期盼我的归去,如果没有酒便满脸的不高兴。没有菜他不计较,没有酒便觉得扫兴。
前年,我那留在家里的三岁的儿子,每次开饭,都主动抱来酒瓶,饭后拿来香烟,父亲每次给我写信,都赞不绝口,说:“他在替你尽孝道哩!”因此,父亲特别喜欢我那儿子的乖巧。每次外婆接他去玩几天,父亲便想念得不行,天快黑了,他不顾人家的再三挽留,顶风冒雨,也要将孙子架在脖子上,深一脚浅一脚地顶回来。我知道,父亲在孙子身上,也寄托了老人家对远在边陲的儿子深切的爱啊!

父亲日见疲惫和衰老,但人老心不老,人格并不见萎缩,仍然恪守“人穷志不穷”的古训,迎接任何挑战;仍然时常在昏黄的灯下,凭着那双老花眼镜,给我写来家里的致富信息,写来鼓励与痛切的思念。他常常让我想起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位老人,你尽可以消灭他就是打不垮他;常让我想起一位朋友的诗句:
沉重的犁
沉重的风雨
终于为你写下沉重的诗句
尽管站起来的时候
腿禁不住阵阵战栗
……
并不甘心就这样
任衰老匆忙地合上生命的日历
迎着早春的太阳
你缓缓地充满深情地走向你所熟悉的嫩绿
忽然,你抬起头,高高地抬起头
迸发出一声长长的呼叫
一如铁笼中的虎啸
回旋着带血的信念和期冀
▌补记:父亲在中风瘫痪五年半后,于2008年10月18日凌晨三点,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享年73岁。我回到武汉,在报社工作了14年,他一直以我为骄傲。我是一边啜泣,一边念完追悼词的。全场肃立,甚是悲切。离我当年发表的这篇文章过了整整17年又5个月。
原题为《挥不去的记忆》,原载《主人》杂志,发表于1991年5月。
▼

作者简介丨赵代君
武汉晚报传媒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编委、监事
武汉晚报新闻110部主任,高级编辑
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
总制作丨张洵 朗读者丨林芳俏
文章配图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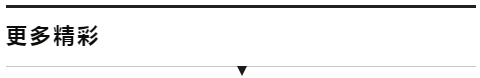
☞ 陵园踏青不阴森!可这位壮男扫完墓浑身抽搐翻白眼!以为“鬼上身”
☞ 国家发大红包!在武汉这70平方公里,直接海淘,比原产国还便宜!还有各种福利等你发掘……
☞ 武汉孕妇一顿能吃6碗饭!宝宝出生十来斤!医生却很捉急……
☞ 一点点奶茶店又出事了?!小情侣发帖怒斥:喝完上吐下泻一夜未眠!吃货们又吵翻天了……
商业洽谈 | 13467514651(杜鹃)















